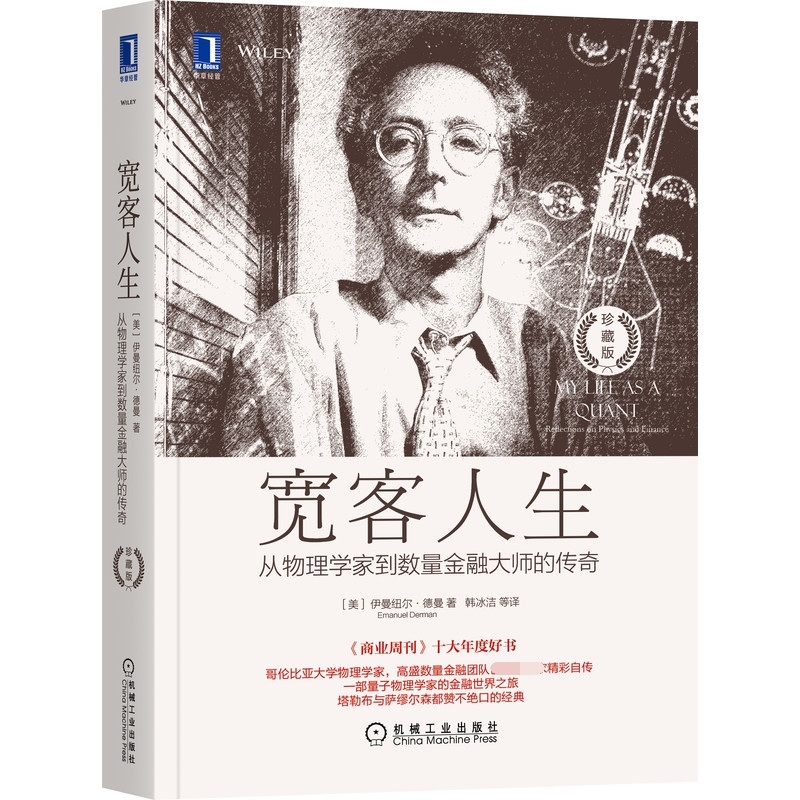
出版社: 机械工业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1.40
折扣购买: 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珍藏版)
ISBN: 9787111698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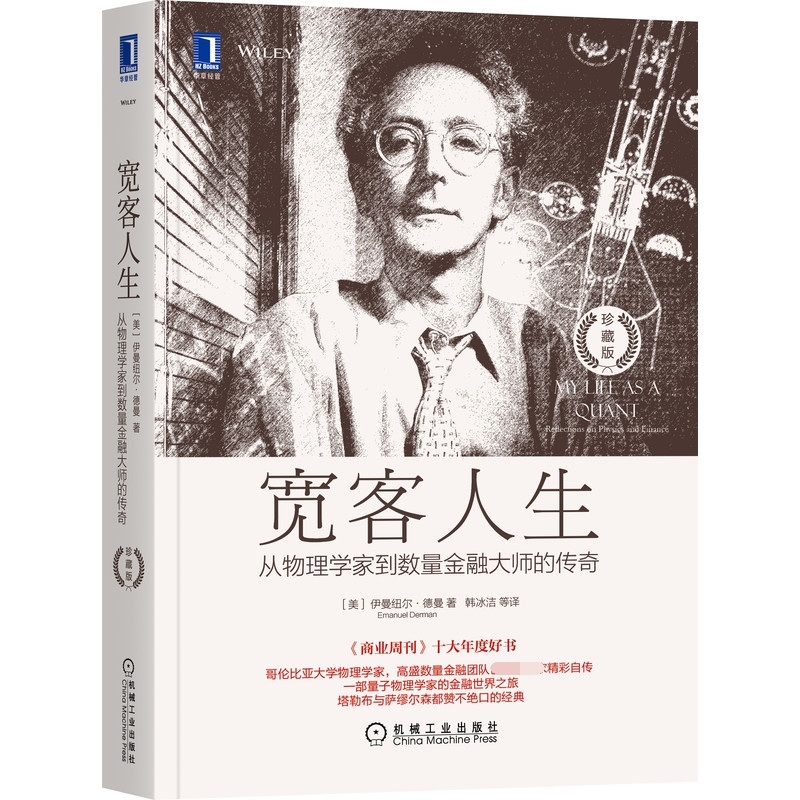
我把纽约想象得很美好 。然而,当我在1966年秋 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到达那里 的时候,纽约城看上去既肮 脏又凌乱,毫无现代感可言 ,令人失望。当时我在倒时 差,疲惫不堪,从肯尼迪机 场坐上闷热的出租车去上曼 哈顿区,旅途让我情绪低落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设的 研究生公寓——“国际公寓” (I.House),位于远离纽 约上西区的地方,公寓里塞 满了塑料家具,跟我在南非 时他们寄给我的宣传册中的 样子大相径庭。走廊的墙壁 被粉刷成白绿相间的颜色, 让人很不舒服,加上后门入 口处的保安,都让人有种身 处监狱的感觉。花了几个月 时间,我才对这些让人难受 的东西熟视无睹。我们都把 这个地方称为“国际公寓”, 看来确实很适合外国学生居 住。 走下飞机的几个小时后 ,我陷入了一种非常强烈的 孤独感中。这种感觉与突然 的距离感和时间感有关,我 曾经几度离开家门,但没有 一次离家这么远,也从来没 有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 情况。在一连几个星期,甚 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喉 咙里好像有个肿块,随时都 可能把我压垮似的。这种强 烈的感觉很长时间才过去, 可当它消失后,我又怀念起 那种让我意识到自身存在的 悲伤和渴望而带来的痛感。 很多年后,当我读到罗伯特 ·穆齐尔(Robert Musil)写 的《青年特尔勒斯》 (Young Torless)时,就 意识到了那位年轻的主人公 穿透人心却又令人捧腹的苦 恼。当初那种孤独感并未完 全消失,从那时起,无论何 时我独自到达一座新城市时 ,都会唤起我对那段痛苦时 光的回忆,即使这种感觉只 是片刻。 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 我在国际公寓几乎没有跟任 何人讲过话。那时还没有开 学,公寓里基本空无一人, 寂静无声。出于惯有的谨慎 ,我提前三个星期来到学校 ,强迫自己安顿下来,熟悉 环境,等待我的物理学博士 课程开始。然而,我感到跟 以前认识的所有人都隔绝开 了。今天似乎不能想象在世 界任何一个地方而与外界失 去联系的现象,但我从开普 敦到纽约的第一年确实是这 样的。那时,在一层楼里住 着50人的国际公寓中几乎没 有电话,只有在过道一个隔 音效果极差的电话亭里装有 一部分机。当时,打给南非 的电话费非常贵,而且必须 向接线员提前预订。我从来 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取而 代之的是,我每周都会给家 里人和朋友们写几封信。最 后,感谢“上帝”,我在研究 生院第一学期的课程总算开 始了。 一定要在物理学界成功 ,这种盲目但强烈的愿望激 励我离开开普敦,一次简单 而又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哥 伦比亚大学。4年前,我16 岁的时候进入开普敦大学读 书。我们接受的是英国式教 育:你必须选择你的主攻方 向——科学、艺术、医学或 是商业,然后才能开始学习 。我选择的是自然科学。在 我大学的第一年,我选了四 门分别要上一年的课程:物 理学、理论数学、应用数学 和化学。大学里并没有可供 选择的辅修课程,老师选择 讲什么,你就要学什么,然 后在每年年底的期末考试中 得到相应学分。到了大学四 年级,我决定选一门应用数 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双学位课 程。可愚蠢的是,学校从我 大学二年级开始就规定只能 选择理论物理学了,这使我 缺少实验技能。这样过早地 确定专业,在美国任何一所 好大学里都是不能容忍的。 1965年年末,我突然意 识到我很多有志向的同学计 划申请出国读研究生。碰巧 ,我因为讨厌痤疮而意外踏 上美国之旅。说来凑巧,10 年前我那心理医生的姐姐帮 助我的皮肤科医生的侄子克 服了“注意力缺乏症”,这位 皮肤科医生出于感激,鼓励 我申请去国外读物理学。我 接受他建议的时候还没有完 全弄懂我将踏上的是怎样的 一条路,就着手申请英国和 美国的奖学金了。开普敦大 学物理系对出国读书所带来 的益处持有偏见,但我并没 有被他们劝住。 如果不是痤疮,可能我 仍留在南非。所以从那时开 始,我就相信我的人生旅程 、分别的老朋友和结识的新 朋友、我的婚姻和我的孩子 们,都是一次偶然的痤疮的 结果。 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