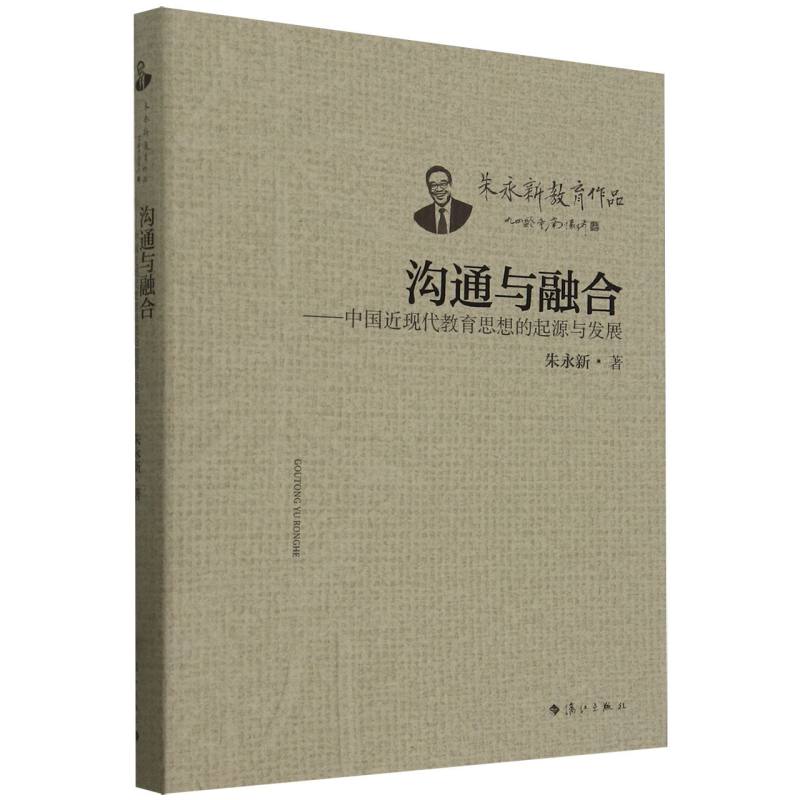
出版社: 漓江
原售价: 69.80
折扣价: 41.18
折扣购买: 沟通与融合——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ISBN: 9787540794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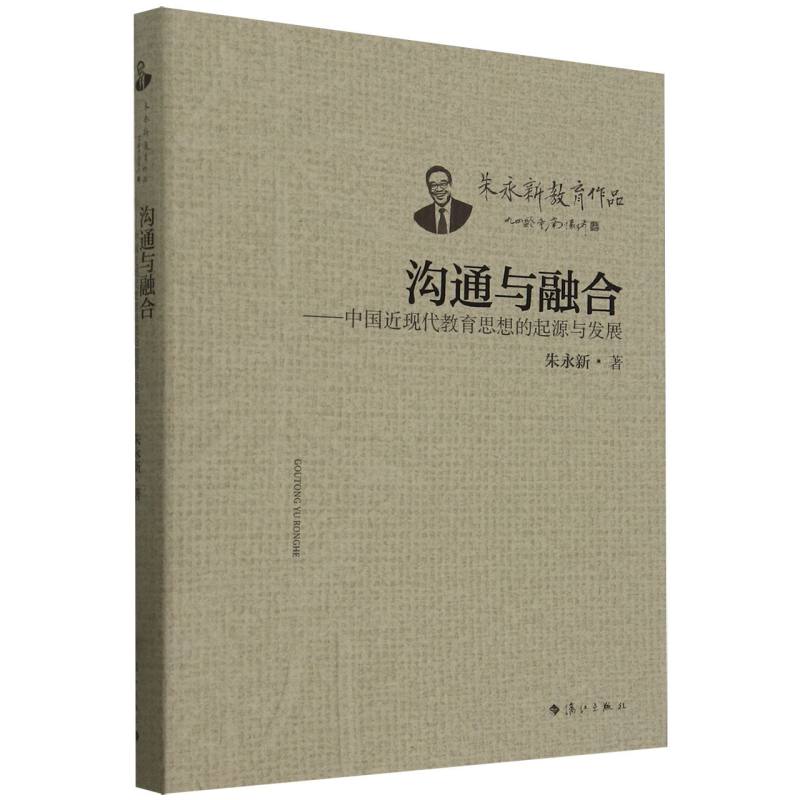
朱永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等,著作被译为英、法、日、韩、俄、蒙、阿拉伯语等28种文字。主编有“当代日本教育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等30余种图书。先后多次主持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国教育十大风云人物”、“中国教育60年60人”、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等,先后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全球教育单项奖“一丹教育发展奖”等奖项。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教育学经历了从创立、发展到粗具规模的三个时期,中西教育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以会通和融合,中华教育思想呈现出新的面貌。在一百余年的时间内,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仅完成了由古代教育思想到近代教育学的过渡,也实现了由近代教育学到现代教育学的转变。 一、西学东渐与近代教育学的诞生 西方教育学的传入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在明末万历年间(1573—1620年),传教士利玛窦率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为手段,求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利。紧随其后的西方传教士大多也如法炮制,在为传教服务的宗旨下,翻译介绍了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与传统的封建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方教育信息。如西方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撰写的《童幼教育》(1620),论述了西方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这部著作很可能是最早输入我国的教育类读物。再如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西学凡》(1623)和《职方外纪》(1623),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文、理、医、法、教等专业的课 程纲要、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考试等。这一时期西方教育学的传入,由于数量极少、内容零星,未形成多大影响。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世纪时,由于外国传教士介入了清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雍正皇帝把传教士全部赶出境外,西学东渐的历史出现了暂时的中断。当中西教育交流再度开通时,已是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再度来华,并更加重视教育活动。如新教的教会学校所拥有的学生至 1890年达16836人,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更达25000人。与此同时,描述与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于1873年出版了《德国学校论略》。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在该书前言中评论说:普鲁士最近的军事胜利应归功于其士兵所受的教育,它鼓励他们为理想和原则而战。该书强调义务教育及在全国各地开办大量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重要性。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西学考略》(1883)也是一部有影响的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著作。他于1880—1882年受中国政府委派出访西方七国,收集这些国家的教育资料,此书便是他调查研究的成果。此外,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花之安的《泰西学校论略》(又名《西国学校》)、林乐知(Y. J. Allen)的《文学兴国策》等,也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1882 年在圣约翰书院主持院务的颜永京翻译了《肄业要览》,署大英史本守著,这其实是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著《教育论》中的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最早译本,也是中国最早的汉译教育理论著作。 中国真正开始大规模引进或传入西方教育学说和思想,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而且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的。1898年8月2日,清光绪帝发布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样,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人员就作为政策确定下来,一时间留学日本的人员激增,1906 年留日生已达 13000 人左右。留学日本的学生在引进国外教育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西方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学说和著作,如夸美纽斯、卢梭、洛克、斯宾塞、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赫尔巴特等人的传记、学说和著作,大多从日本传入中国。根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年到1911年,中国共译日本教育类著作76种,为历史最高峰。另据杭州大学周谷平的统计,这一时期(从1901年《教育世界》连载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教育学》到 1915 年新文化运动)中国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几乎均为日译本或据日文本编译而成。 我国最早通过日本引进西方教育学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去日本留学的人员翻译或编译有关教育学著作,以及日籍教员来华讲授教育学课程,把他们所用的教材翻译或编译过来等途径进行的。因此,以日本为媒介来引进西方教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的重要特点之一。以日本为媒介虽有快捷便利之优点,但亦有信息失真之弊。如当时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产生于德国,传入日本后再传入中国,几经转译、删改,难免大为走样。以奥地利林笃奈尔原著、日本汤原元一译补、中国陈清震重译的《教育学》为例,林笃奈尔是根据赫尔巴特的体系阐述的教育理论,他去世后又托付德国扶廖利爱博士增订,日本汤原元一因原书多征引欧洲材料,则“多以中暨日事易之”,而中国陈清震在留日期间又把汤本中的“日事以中事易之”。这样,传入中国的其实已是经过日本诠释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了。 这一时期西方教育学传入的另一特点,是以编译讲义和教科书为主,从上述征引的著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作为讲义或教科书印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师范学校开设教育学课程的需要,或以强国富民、重视教育为目的,引进的功利性目的比较明显。相形之下,还没有完全、真正地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更没有自觉认识到教育学可以用来指导实践、预测未来教育发展的理论功能。引进西方教育学的这种缺陷,已成为中国教育科学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而长期存在,是值得重视的先天不足现象。 但不管怎样,这些编译或翻译自日本的有关教育学著作,以及少部分参考日本著作而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毕竟把域外的科学教育学的种子播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中国学者编著的教育学书籍,尽管其体系、结构、内容等均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毕竟已开始了结合中国国情来编著教育学的尝试。如张子和的《大教育学》,其参考的原本是日本学者松本、松浦二氏的讲义,但在该书《自叙》中,他明确说“欲讨论修饰以适合中国教育界之理想实际”。 这样,近代中国的教育理论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质。第一,它仍保留着古代教育思想的形式。大多近代学者基本沿袭着古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即主要是经验式的描述或思辨式的宏论,很少有实验性的研究与实证性的调查;阐述教育问题的概念也大多是古代的范畴,如人性、人才、劝学等,很少涉及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方法等;在社会危机面前,他们的主要精力在匡时救世的社会宣传,教育的见解大多与其政治、社会等思想浑然一体,是社会变革舆论的组成部分。第二,它已初步涉及近代教育学的某些内容。近代学者如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多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们或者间接接触或者直接翻译介绍西方教育学的著作,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古代教育思想与近代教育理论的交融与汇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把西方教育制度与自己的大同理想糅合在一起,并未显出拼凑勉强之状。不仅在讨论的内容上,近代教育理论已突破了过去的概念和范型;在思维方式和视角上,近代教育理论也超越了古代的模式,带有近代教育学的若干特点。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产生之时,中国的近代教育学已具雏形。而中国近代学者以及留日学生、日本教习,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过渡到近代教育学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本书中,作者从国际国内、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角来总结中国近现代的教育经验,剖析教育发展史,并以史为鉴,用过往的经验来开拓现代教育事业。是一本对读者具有较强启迪作用的教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