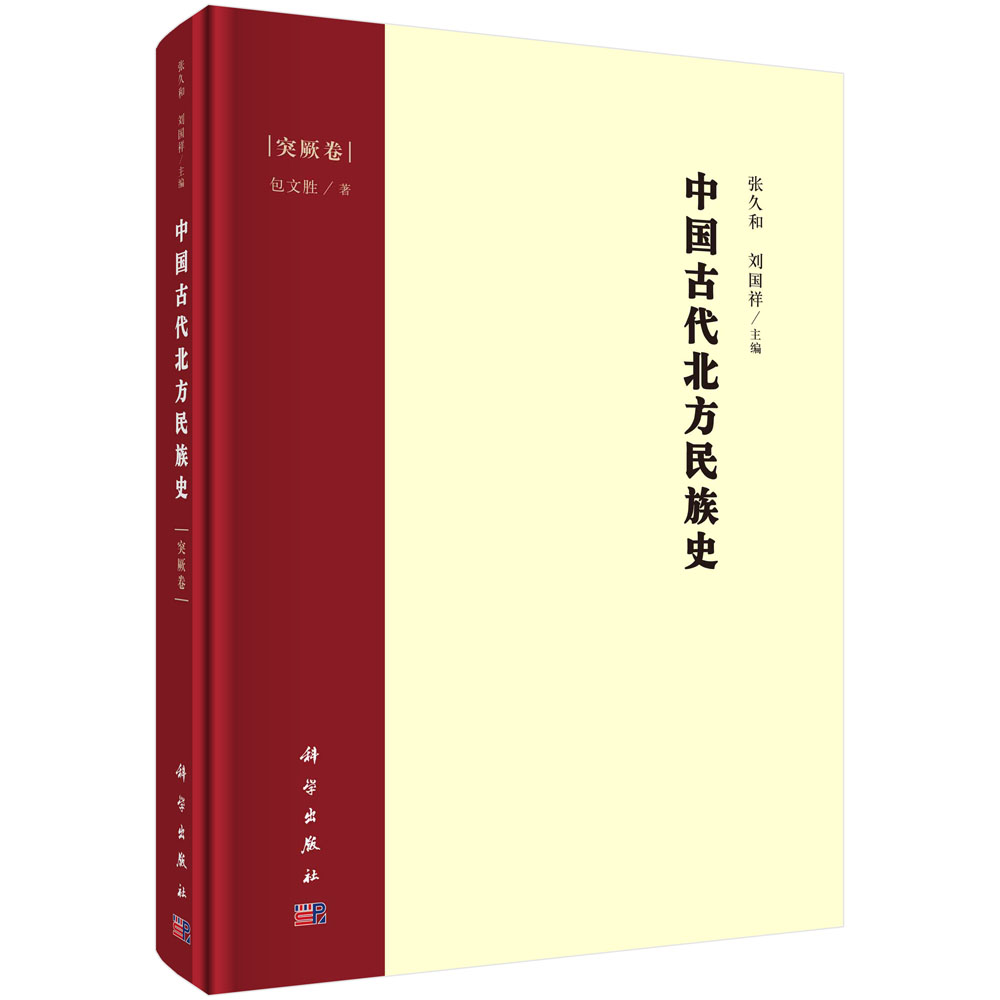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101.20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突厥卷
ISBN: 9787030690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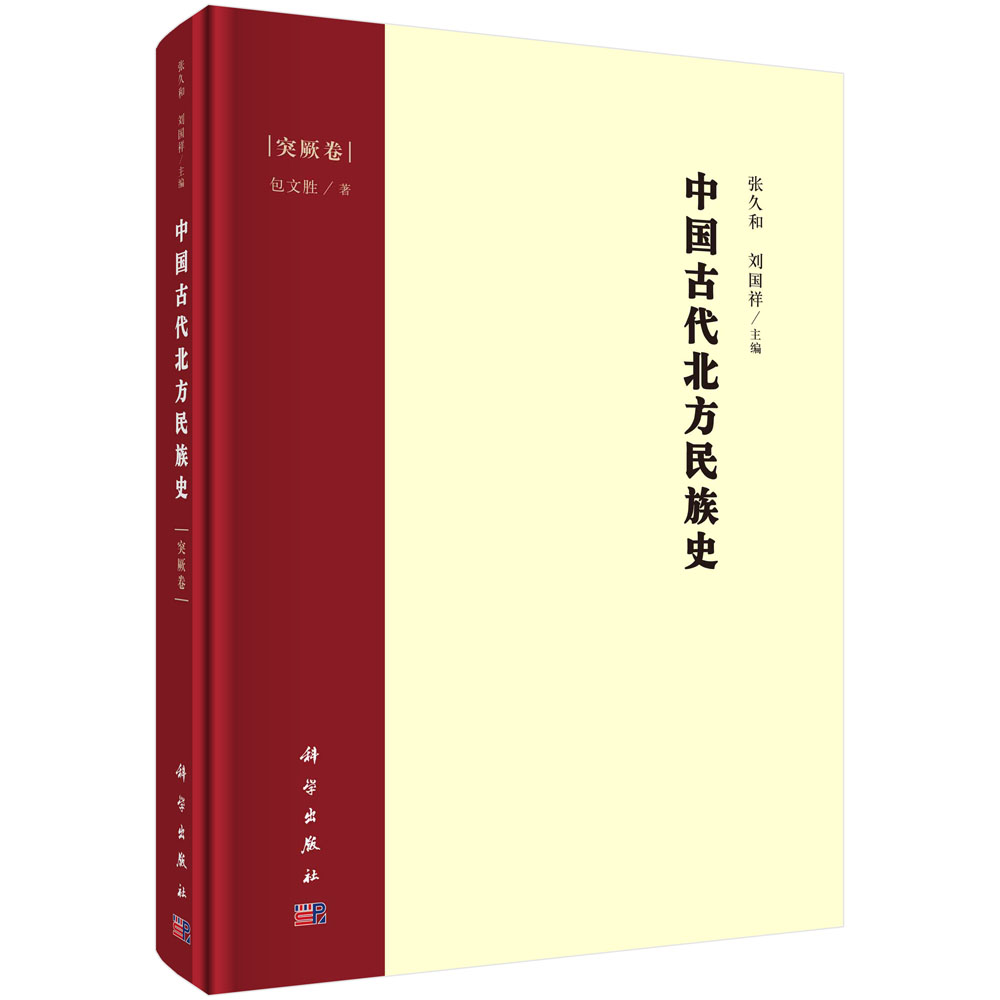
第一章 突厥的资料和研究状况
突厥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突厥史则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一带,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开始向外延伸扩张,建立政权,鼎盛时期曾掌控亚欧草原及周边地区。突厥政权从8世纪中叶开始衰落,统治地域被其他政权或部族不断占领,部众散落,渐渐淡出史册。研究突厥史的资料,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丰富,非汉文史料也不少。国内外学界研究突厥史的时间较长,且研究内容广泛,所获成果颇丰。
第一节 突厥的资料
有关突厥的汉文史料记载,相对其他文字文献而言较为丰富。“突厥”之名在汉文史册始见于542年。从此,与突厥有关的历史被当时或后世史家著录,其名不绝于史。在廿四史中,《周书》最早立《突厥传》,之后,《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相继设有专传。在其他类别的史籍中,《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等史书也立有“突厥”专目,集中记载其史事。除了这些专传和专目之外,还有许多与突厥有关的内容散见于各类汉籍史书及碑志、文书等当中。
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初就开始搜集有关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至今可谓成果颇丰。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从“正史”中摘录了西突厥、“西域诸国”及相关人物的列传,从僧人行纪中搜集了有关西突厥的记载,又从《册府元龟》中摘录了有关西突厥的零散记载,并把这些材料汇集成书,于1903年出版。我国学者冯承钧把沙畹的这部著作译为汉文,并以《西突厥史料》为名,商务印书馆于1932年出版,中华书局分别于1958年和2004年再版。冯承钧的译本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对沙畹搜集的汉文史料进行了校勘,还以附注的形式提及疑误、纠正错误等,提升了沙畹书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岑仲勉对沙畹书中所搜集的汉文史料进行补缺及考证,以《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为名,中华书局于1958年出版、2004年再版,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沙畹书的内容。刘茂才(Liu Mau-tsai)的《东突厥史料》一书,体例与沙畹书相似,其内容包括汉文史书中有关东突厥的专传和专目,以及相关部落的记载和散见史料等,于1958年出版 、1993年再版。在各部辑录史料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中华书局于1958年出版、2004年再版。此书中搜集的汉文史料更全,为学界青睐,其内容包括散见史料编年辑考、突厥本传校注及突厥人物的列传碑志校注等。岑仲勉对所搜集的每条史料的年代、字句以及史料所记人名、部名、地名和相关史事等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校勘和辨析。可以认为,岑仲勉的这部著作奠定了学界研究突厥史的史料学基石,成为涉及该领域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当然,从岑仲勉书出版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其间新发现的突厥史料数目可观,又发现了传统史籍的新版本,古籍整理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也不断运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分析、研究等,因此,有必要对其著作进行补充和修订。吴玉贵的《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一书,正是出于这一要求编纂而成。这部著作几乎将有关突厥第二汗国的汉文史料搜集一空,并在体例上改变了以往的专传、专目与散见史料分开辑录的方法,而是把专传和专目内容拆开,与散见史料一起进行编年辑考。该部著作对每条史料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校订,提出很多新观点,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另一部搜集突厥史料的著作是薛宗正的《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这部著作将正史除外,以《册府元龟》为主,又以《唐会要》《通典》《全唐文》《文苑英华》《文馆词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为辅,全面搜集了有关突厥的史料。这部著作的上编是史料系年,就是把每条史料按编年辑考;下编为文献集萃,把汉文史料所记有关突厥的内容分门别类的辑录,又搜集了非汉文如粟特文、突厥卢尼文、古藏文、古希腊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资料。纵观前人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与突厥有关的汉文史料的挖掘已经很深入,校勘考订工作也做得非常详细。
突厥卢尼文碑铭是研究突厥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突厥卢尼文是突厥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字,学界因该文字的外形与古代北欧诸民族使用的卢尼文(Runic)相似而命名之。突厥卢尼文碑铭是突厥人用自己的文字刻写自己的历史,所以史料价值很高。19世纪末期,突厥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和拉德洛夫(W. Radloff)成功破译了突厥卢尼文,从而拓展了研究突厥历史的史料范围。与突厥历史有关的内容相对保存完整的突厥卢尼文碑有《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等,以及最近新发现的《克尔克斯敖包碑》。
《暾欲谷碑》于1897年发现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Ulaγan baγatur)东南约60千米的巴音朝克图(Bayan .oγtu)之地,有大小两块石碑,记录着突厥汗国功勋大臣暾欲谷一生的伟业。大石碑高243厘米,四面刻字,共35行;小石碑高217厘米,四面刻字,共27行。《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于1889年发现于蒙古国后杭爱省(Aru qa.γai aimaγ)哈拉和林苏木(Qara qorin somu)赫硕柴德木(kü.iye .aidam)之地的鄂尔浑河东岸,记载了阙特勤和毗伽可汗兄弟二人一生的功绩。两碑并立,间隔约1千米,皆为唐朝工匠雕刻,盘龙碑额和龟趺底座,碑高375厘米(《毗伽可汗碑》稍高些),宽122—132厘米(碑的上部窄,下部宽),厚44—46厘米。两碑的西面刻汉文,而南、东、北三面刻卢尼文,两碑的三个棱角、龟趺以及西面的部分处也刻有卢尼文。《翁金碑》于1891年发现于蒙古国前杭爱省(.bür qa.γai aimaγ)翁金河(O.γin γool)之旁,距《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赫硕柴德木南约160千米,发现时已断裂为几块。此碑内容是阿史那骨咄禄时期突厥汗国复兴的历史。不过,碑主是谁并不清楚,从碑文内容来看,其主人可能是骨咄禄之弟咄悉匐。该碑东面和南面刻写着卢尼文,共12行字;南面上方又有较短的7行字,记载着立碑和刻文者情况;碑前所立杀人石上又有1行字,记录了杀人石主人之名。《阙利啜碑》于1912年发现于蒙古国中央省(T.b aimaγ)德力格尔汗苏木(Delger qan somu)叶克赫硕图(Yeke kü.iyetü)之地,其内容记载了阙利啜一生的功绩。此碑高190厘米,宽65厘米,厚20厘米,东、西、南三面刻卢尼文,共28行;还有横着写的1行字,内容为刻文者的状况,但未写其名。关于此碑主人阙利啜身世不是很清楚。从碑文所记内容来看,他生活于骨咄禄和默啜可汗时期,参加了很多建立汗国和向外征服的战争,应该是骨咄禄族人。《克尔克斯敖包碑》于2016年5月由蒙古国特 伊德尔杭爱(Т. Идэрхангай)和策 巴图图拉嘎(Ц. Бaттулга)在蒙古国巴彦洪格尔省(Bayan ho.γur aimaγ)博查干苏木(Bo.ihan somu)西北45—50千米的拜达尔河(Baidar γool)西北岸发现。此碑为残碑,属于某碑的断裂部分,南、北、西三面刻卢尼文,共8行。此碑内容属于突厥第二汗国建立时期的历史,碑主为毗伽啜莫贺达干,应属于骨咄禄家族人,但确切身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以上介绍的碑铭,国内外很多学者均有释读研究,并出版其相关研究著作,如Ramstedt G. J. 、Gerard Clauson、René Giraud、С. Г. 克利亚什托尔内(Klyashtorny)、Malov С. Е. 、Hüseyin Namik Orkun、Talat Tekin、Л. Болд、M. Шинэх 、Mehmet .lmez、Erhan Ayd.n、小野川秀美、森安孝夫、韩儒林、岑仲勉、耿世民、芮传明等。
除突厥民族以外,回鹘、黠戛斯等也有以卢尼文刻写的碑铭。与回鹘有关的碑铭有《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苏吉碑》等。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70余座墓碑则多与黠戛斯有关。此外,年代和内容不太清楚,且内容相对简单的小型题记刻文也不在少数。在蒙古国境内发现了百余处石崖或器物上刻写的突厥卢尼文。最近,在蒙古国苏赫巴特尔省(Sükebaγatur aimaγ)董瑾席勒(Dü.gin .irege)之地新发现了大型的带有突厥卢尼文墓碑的祭祀遗址,但刻文内容相对简单,重复刻写了两三句话。中亚草原地带也发现了几十处突厥卢尼文石崖刻文,内容较为简单。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河洞壁、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查干敖包(.aγan obuγa)等地也发现了突厥卢尼文刻文。这些突厥卢尼文资料,也有多寡不同的与突厥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
有关突厥史的粟特文史料不多,但很珍贵。粟特文是居于河中地区(即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人使用的文字。突厥人曾借用粟特文。目前发现的以粟特文记载突厥历史的碑刻有《布古特碑》和《小洪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