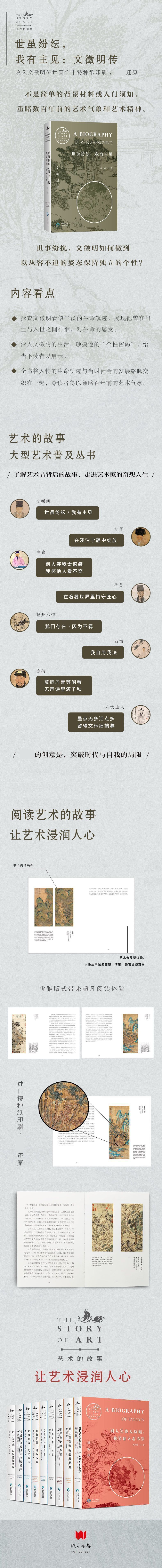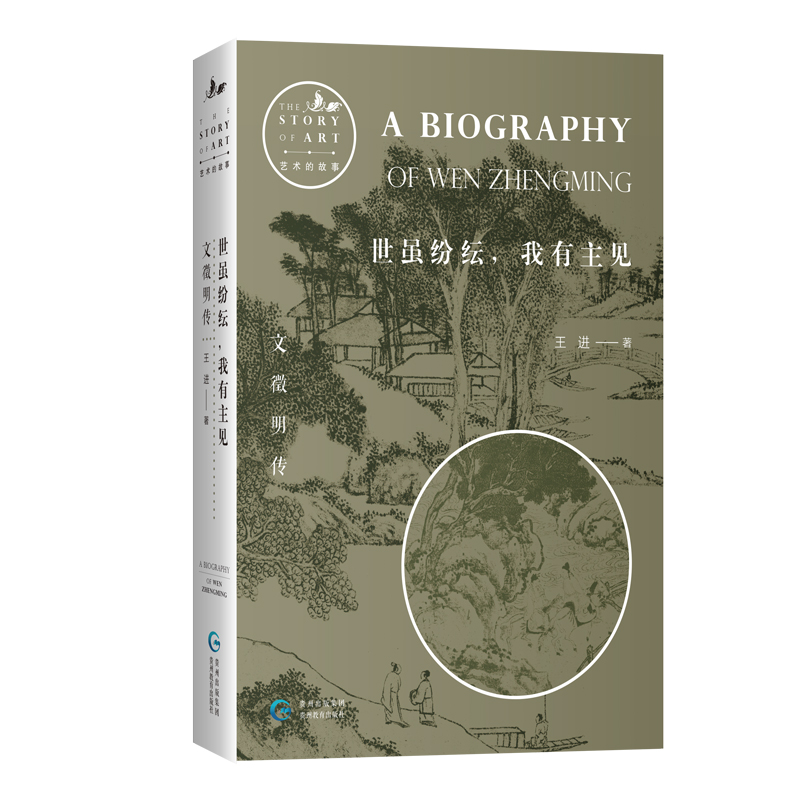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教育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16
折扣购买: 世虽纷纭,我有主见:文徵明传
ISBN: 9787545612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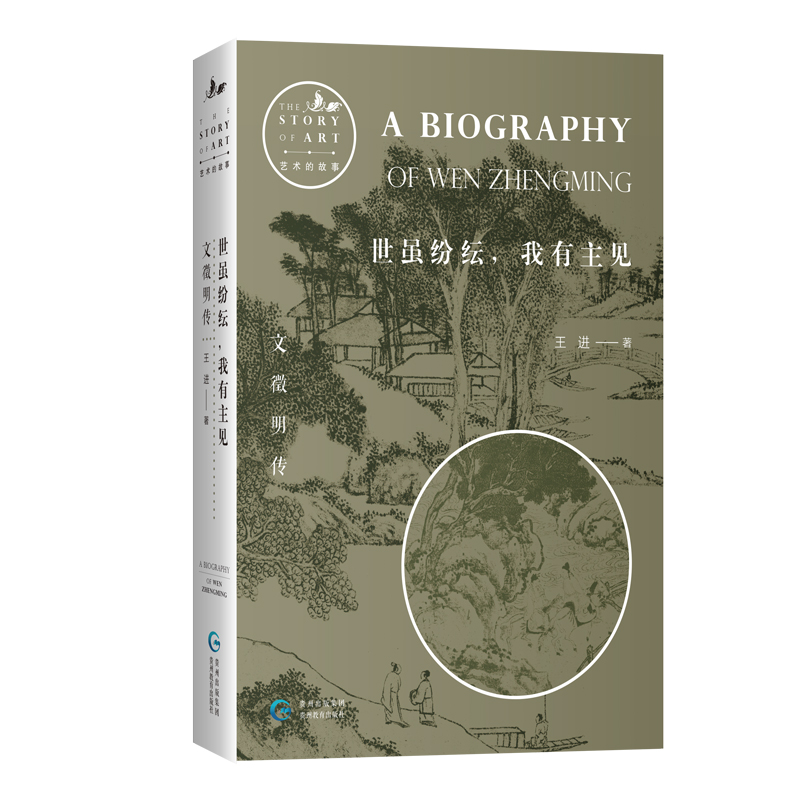
王进 资深媒体人。以明代文学为研究方向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东方早报》、《中国证券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编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等传媒奖项。
序章 丹青寄梦 文徵明逝世时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他一生的浓缩象征: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二月,正是自然界乃至整个明王朝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时候。江南苏州,文徵明正襟危坐在书房的小椅上,瞑目逝去,仿佛沉浸在书画构思之中,又仿佛创作之余的小憩。面前是整齐摊开的纸笔,翰墨飘香——他死都死得很儒雅,而且得享九十岁的高龄。后世用“翛然若蜕”“翛然若仙”来表达对一代大师离世之从容和圆满的羡慕。这一天,同他的三位好友,与他并列“吴中四才子”的唐寅、祝允明、徐祯卿的死,已经相隔了数十年。由于他的大名、他的高寿,在时人的眼中,他已是“活神仙”般的一流人物,大批拜读了他的诗文,赏鉴了他的书画的门生、文人或者权势贵胄们,都纷纷慨叹没有和这位“前代大师”生活于同一时代,却不知大师就在他们中间——“海内习文先生名久,几以为异代人”。 文徵明这一安于平淡和归隐的姿态,大约可以贯穿他的一生。这是一个没有传奇与戏剧色彩的人物。他的九十年人间畅游的经历,除了刚刚出生时有点儿古怪(史载文徵明连着数年不大会说话和走路)以外,在其余的漫长岁月里,他“相对自由”地读书、赏景、习画、练字、考科举而屡不中、被推荐入朝而迅即逃回以及最后在艺术和自然世界中轻松弃世而去。说他自由,是因为他既没有官场的羁绊和束缚,也没有“立德立言”的著述精神和不舍追求,他在自己的爱好和趣味中度过一生,这是幸运的——比之于唐寅在悲苦中死去,祝枝山在不认不服中逝世,徐祯卿在艰难跋涉的三十二岁英年之时不舍地离开。 古人每每叹息:“绚烂之极反归于平淡。”我们会觉得,其余诸人一生的紧张和繁华,即使如唐寅那样播传于众口地春花绚烂、才子风流、火树银花、流星绽放,最终都不敌文徵明的平静和淡泊。文徵明的魅力在于他无论是作为自然个体还是作为艺术家,迷人之处恰好就在于这份从容不迫。他的画作,也正是带着这份精纯的艺术气韵,在中国画史上,同沈周、唐寅、仇英一起,共创了吴门画派,被后人合称为“明四家”。故而文徵明的一生,既是暗藏着政治之梦的隐士的一生,更是不折不扣恬淡艺术家的一生。相比之下,“吴中四子”中的其他人就未必有这份艺术的纯粹。所以,文徵明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之间游刃有余,并在数个领域都创造了时代的奇迹,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史地位。这一点,同沈周、唐寅、祝允明、徐祯卿等只在某个或某几个艺术领域中达到精纯和大师地位是不同的,这倒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兼通多种艺术派别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巨人颇为相似。 这本画传,正是希望探入文徵明这种平淡生活的水面,触摸他深埋于水下的艺术人生和艺术精神。虽然这有些像花港观鱼,有些像极目远眺,有些像趴在山顶的俯视,远远近近的、模模糊糊的,但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本书更多地了解他许多画作的由来,许多创造精神的发端。 文徵明本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于是改字为徵仲,改名为徵明。由于文家先祖曾在衡山县居住良久,所以以“衡山居士”为号。他思想宽容、敏锐,性情却沉稳执着,有时甚至近于固执。他不喜欢修整容貌仪表,不喜欢接近女伎,而重容仪喜女伎则是当时社会的标志性风气,从达官贵人到市井小民,莫不如此。他力摒流俗,甚至有“平生不二色”的名头,在以温柔佳丽地著称的江南,且置身一群放纵礼法的年轻才子中,这是一件难得和不可想象之事。“小事不小”,从他的诗文、思想与“色”之一字的矛盾上,可以看出他大致所趋同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而同样“不好色”的礼法之士、卫道之夫,同文徵明这样的外忠厚、内自由的时代人物,还是不一样的。他生性豁达,但朋友间如有小过错,却又断然不放过,经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来;朋友间谁有一技之长,他也从不吝赞美之词。所以,文徵明始终不失赤子之心,是真性情之人。 但是,后世史论家都执着地认为,文徵明的忠厚性格以及由这种性格所决定的平静生活的抉择,并不能掩盖他对个性和自由的向往。文徵明固然少年老成,始终将儒者的风范乃至老来长者的儒雅展露给乡人,甚至被尊为地方道德标准的“楷模” (史书曰:“晚岁,德尊行成,海宇钦慕。”)。由于人生道路的蹭蹬不平,也由于思想、性格的与世不合,文徵明和他周围的一大批人常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但是,他的个性不改,他的朋友,祝、唐、徐三人,均是狂傲不羁之人,他们以强烈的个性精神与社会势力对抗,追求自由生活,蔑视社会规范,因此用常人眼光来看,不免有些畸形和变态。三人的作品多次表达了这种安于癫狂和尖锐的姿态。祝允明有《祝子罪知录》,唐寅有“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之宣言,文徵明虽然表现得温和与内敛得多,但他日日与此等人为伍,一同高谈阔论、抵掌叹息,大家相近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可想而知。只是文徵明没有更多地表现在行动和外表之上,而是表现在艺术创作之中罢了。 所以,文徵明虽然没有唐寅的诗酒风流、大喜大悲,没有祝允明的张扬尖锐、愤世嫉俗,没有徐祯卿的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而且除了九次科举考试、一次短暂出仕之外,终其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过苏州方圆,但他也深藏年轻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时露中年后日趋强烈的家国之忧。他的壮年时期,恰逢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宦官专政,奸臣当道,国家外表强大而内实处风雨飘摇之中。尤其在思想领域,新旧之争,仿佛老树对抗新枝,仿佛方生方死之间的明暗交替和誓不两立,其惊心动魄,非笔墨所能尽述。然而,文徵明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在艺术世界的平静栖 居。没有从政,也没有启蒙之志。老实说,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如果文徵明出仕,也未必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许多比他更具政治天赋的人,如父执辈的庄昶、吴宽、杨一清、王鏊,以及其父文林、叔父文森等,都选择了隐居、辞官等诸般挂冠而去的无奈举动。文徵明外平淡而内自由的性情和艺术天赋,实在最适合艺术创作。他的一生虽然几乎都是在山水优游、诗酒酬唱、书画鉴赏中度过,但平淡之中有自然的精彩,有艺术上艰难的突破,有作为儒者对理想和道德的坚守,有作为个体对生命的苦痛感受,也有在出入之间迷惘的徘徊。我们看他一生的点滴痕迹,看他的诗文甚至词的创作,看他的洋溢着山林野趣的画作,也许能对画家的痛苦与他最终转向艺术有更深体会。 说穿了,这种被迫转型,是身兼艺术家和儒者双重身份的文徵明对“个体趣味”还是“大众责任”的选择。他选择了前者,因为他身处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富有张力的明中叶。 明代历史是一段极其有趣和复杂的历史,读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读者可以从那小段历史描述窥见大明以至整个中华民族风云之一斑。看似没有大唐的辉煌、大宋的悲壮、大元的怪异,但明王朝留在普通大众记忆中平平无奇的历史表层下的,是酝酿、冲击和澎湃着从精神到物质的千年之沉淀,以及蓄势剧变的潜流。思想领域的风云激荡,世界局势的暗藏转折,中国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分子的反省和压抑,社会风气的世俗和人性化......就在文徵明跨过的明代成化至嘉靖的九十年风云里,历史 其实正孕育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到来,其间风云无数,有史上最有名的大太监刘瑾的乱政,有明代最大的藩王叛乱——宁王朱宸濠造反,有荒诞皇帝明武宗的游戏天下和神秘暴亡,有明代臣子和皇帝冲突最大的行动——“大礼议”事件......而与“吴中四子”同时及稍后,思想界更是风云激荡,有思想巨人王yangming,有“左派”新锐王艮,有狂人徐渭,有李卓吾,有“公安三袁”......可是,我不敢说,文徵明曾经和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辈们一起,在时代的呼唤中,像海燕一样渴望着和实际地投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去。他在出世入世之间摇摆了许久,最终还是用逍遥的姿态来解构了面前沉重的现实。当然,这样说,不是意味着他像柳永那样“奉旨填词”、漂泊花酒,或像唐寅那样绝望地意识到与政治无缘后,索性进入了民间的世俗世界。文徵明是不折不扣的儒者,他出身世家,一生忧国忧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他只是最终像无数他的老师、前辈一样,抱着政治之心而选择了致仕和远离。无论如何,文徵明在画、文、书三个天地中积九十年之力创造的艺术高峰,始终是本文最有兴味的焦点。而读解他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经历,也是读解这位画家,读解与我们横亘数百年历史长河的古书古画的必要手段之一。 笔者希望,文徵明的画传不是简单地为文徵明之画提供背景材料和入门须知,而在于为重睹数百年前的艺术气象和艺术精神,打通冥冥中存在却无法尽情揭橥而出的生机勃勃之脉象。优秀的画家史传也许不是画家毕生活动的影子和笔录,然而可以成为对洋溢画作之中的艺术和历史气象的描述和填充,成为画家人格和画作精神的具体附丽之物,画家的人格与个性凝结成了画家的创作,而它们又共同在画家九十年不断变化的人生历程中寻到端倪。 史载明代国画大师们绝大多数活动在江南,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在当时,江南是全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心,城市经济发达,物质财富带动了人们对文化的狂热追求,也为文化上的推陈出新创造了衣食无忧的基本生活条件(虽然文徵明、唐伯虎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压力,甚至苦恼和危机)和推崇艺术享受的风气。在此情势下,吴中创作风云激荡、艺术派系林立,文徵明和他那些政治上不顺利、思想上不安定的伙伴们,把创造力和创作精神悉数放到了艺术的篮子里。于是,一批继往开来的艺术探索者和革新家,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继承关系、美学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但最终都凭着各自的聪明才智与刻苦勤奋,在同一个时间跨度里,艰难地开创出各自的艺术新风,没有强求画风统一,也始终没有将个性磨平。 正是无数画家殊途同归的可贵,造就了明代中叶艺术的繁荣。其中之最著名者,便有文徵明。 笔者希望,文徵明的画传不是简单地为文徵明之画提供背景材料和入门须知,而在于为重睹数百年前的艺术气象和艺术精神,打通冥冥中存在却无法尽情揭橥而出的生机勃勃之脉象。 优秀的画家史传也许不是画家毕生活动的影子和笔录,然而可 以成为对洋溢画作之中的艺术和历史气象的描述和填充,成为 画家人格和画作精神的具体附丽之物,画家的人格与个性凝结 成了画家的创作,而它们又共同在画家九十年不断变化的人生 历程中寻到端倪。——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