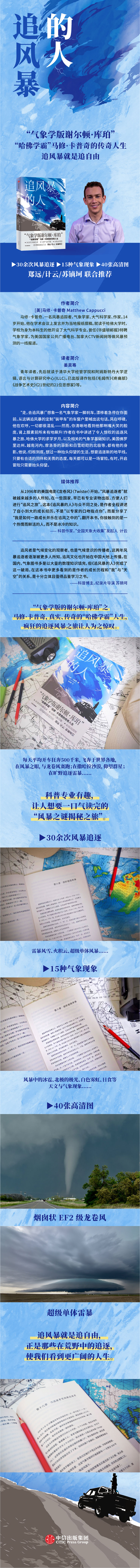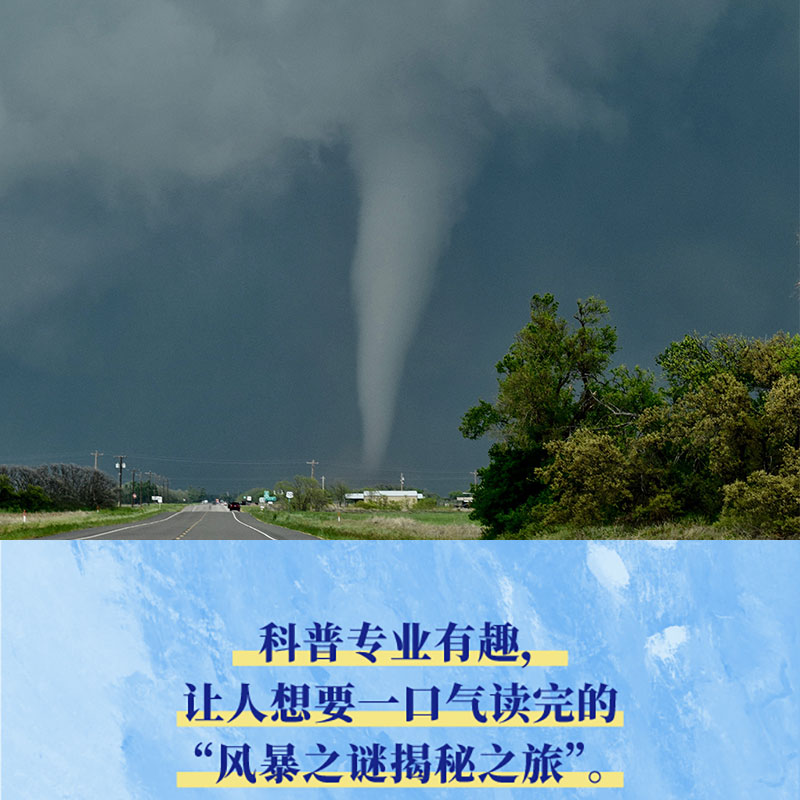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80
折扣价: 45.40
折扣购买: 追风暴的人
ISBN: 9787521756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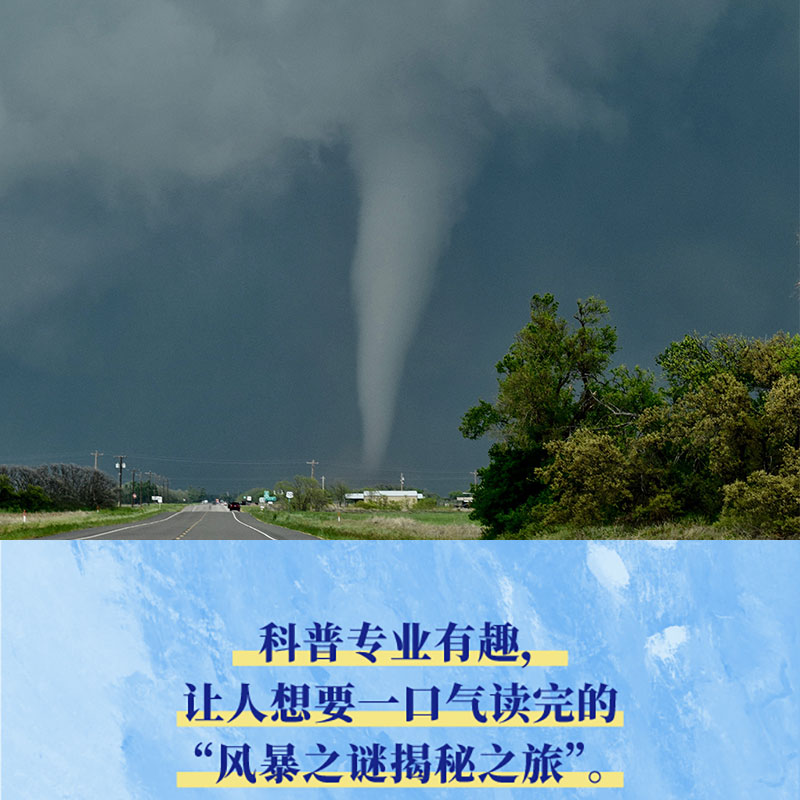
[美]马修·卡普奇,一名风暴追踪者,气象学家、大气科学家、作家。14岁开始,他在学术会议上发言并为当地报纸撰稿。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学校为身为本科生的他开设了大气科学专业。曾任《华盛顿邮报》特聘气象学家,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加拿大CTV新闻网等做风暴预测的一线报道。
文摘:当追逐者变成被追逐者 2020年5月22日像追风季的其他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了——在一晚36美元,而且绝对闹鬼的堪萨斯州汽车旅馆里。那是清晨4点8分,闹钟开始闹腾,真是可恶。窗帘在凉爽清新的风中沙沙作响。睡了整整3个小时后,我并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这是马不停蹄追风要付出的小小代价。12个小时前,我还在架挡风力催动的冰雹,躲避漏斗云,看着毛糙的绿云从头顶扫过。在目不能视物的暴雨中开了2个小时后,我在凌晨1点抵达道奇城(Dodge City),这里曾经是通往西部边境的熙攘门户。我在遇到的第一家亮着霓虹灯的经济型旅店住了下来。房间的窗户是破的,烟雾报警器被垃圾袋遮住。 现在我平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检索数据。我上下扫视地浏览着。这是气象学版的打地鼠游戏——太契合2020年了。争取好成绩是一场逆风战斗。 《华盛顿邮报》从3月新冠疫情暴发后就关闭了办公楼,我从那以后都在远程工作。尽管难免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有机会摆脱工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我可以上午干活,下午追逐风暴了。 尽管夜里的雷暴给空气降了温,但那是5月,只要几个小时,潮热就会卷土重来,让大气再次变成火药桶。我知道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会出现风暴,我届时必须在场。唯一的问题是具体位置。 尽管环境条件有利于风暴骤发,但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引子去触发大气中压抑着的火气。最稳妥的办法是循着一条残余外流边界,那里是沉寂下去的雷暴排出的温和凉爽空气,蜿蜒指向南边的俄克拉何马州与得克萨斯州边境。 但在动身南下之前,我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我匆匆敲出来两篇文章,头上罩着一股烟味的羊毛毯,录制当天的华盛顿特区电台天气预报。等到三张照片慢吞吞地上传完毕后,我不禁欢呼了起来。显然,昨晚停电之后,酒店的倒霉Wi-Fi没有重置。 上午10点,我已然精力充沛,车加好了油,驶上283号高速公路,开往区区350英里之外的俄克拉何马州阿德莫尔(Ardmore)。我在人口70万的堪萨斯州恩格尔伍德(Englewood)停车,又写了一篇文章。天空染上了鲜亮的蓝色,东方地平线上遥远的云彩是前一晚风暴的残迹,强风里携带着大量水汽。 当我穿越俄克拉何马边界,向东南开进时,狂风吹得我自己焊接在挡风玻璃上风的防雹罩哗啦作响。前些年的两场不亚于《圣经》中雹灾的冰雹让我明白,在追风季的高潮,保住挡风玻璃是很有价值的。空气从金属罩两侧流过,发出风扇一样的嗡鸣,而我在听着自动气象雷达用机器人一样的语调播报上午11点的气象观测结果。“伍德沃德,81华氏度,南风,风速17,最高可达31,”低沉的声音伴着静电声传来“俄克拉何马市,气温84华氏度。” 我强迫症似的扫视着天空,距离目的地还有三个半小时车程。中午快到了。大气中还没有出现对流(垂直热量输送)的早期征兆。一片白云都看不到。 我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瞥了天空一眼,让大气明白我已经发现了它的诡计,而且我不会上当。无形的顶盖逆温——地表上空1至2英里处的暖空气层,起到阻止气块上升的效果——笼罩在头顶。它就好比给一锅沸水顶上加了个盖子,压抑着下方积累的热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等到顶盖破裂,大气就会喷薄而出。那就是风暴爆发的时刻。 下午3点前后,我来到了俄克拉何马城以南100英里处的阿德莫尔附近。我深入“怪人乔”[美国前动物园老板,2019年因虐待动物罪入狱。曾出镜纪录片《美国最危险的宠物》。](Joe Exotic)的地盘。我只要沿着州际公路往下开20英里,就到了这位电视节目明星的已闭馆动物园。 我掏出手机时乐了一下,急切地等待着下午的数据传入。正当我焦虑地审视数据时,我的表情凝重了起来。我之前在追的外流边界就在我头顶正上方,这意味着如果顶盖能够破裂的话,风暴最后就会在我的位置形成。但西边的气温略高,意味着顶盖会先在那里破裂。风暴追逐者通常想要赶上一天里的第一场风暴,因为在周围的风暴形成并加入竞争之前,先发风暴可以畅行无阻。 我已经开了五个半小时的车,再开两小时又何妨?我不情愿地叹了口气,将GPS目标地点设定为得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Wichita Falls)。我翻过起伏的山丘,沿途地貌点缀着橡树和灌木,偶尔还有养牛场。我路上遇到一辆被扔在田里的半挂车,车上喷着“二手皮卡”和“爱耶稣”字样,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我2018年追逐风暴时就见过它。树木总算开始消失了。随着我靠近欢迎司机来到威奇托福尔斯的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立体交叉道,地貌开阔了起来。 我路过了小卡尔餐厅。自从我2017年在这里吃了一个鸡肉三明治,它每隔两周就会给我发一条短信。我停在一家冰激凌店外面,车窗留了一条缝,然后跳下了座椅。天空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头顶飘着几朵中等高度的云彩。好戏还没开始呢。我伸了个懒腰,开了8个钟头的车,身体还处于麻痹状态。这一趟最好能值回来,我心里想。 我在布劳姆冰激凌店悠闲地点了一杯冰激凌,等不及蹭店里的空调了。我坐下来,一边做着白日梦,一边享受柠檬蓝莓味冰激凌。过了一会,我抬起了头。窗外的天空看起来比15分钟前更加清澈,雾蒙蒙的感觉不见了。 突然放晴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振奋,但我认出这是风暴的先兆。我知道这意味着顶盖刚刚破裂了,空气自由上升,与原本束缚在地表附近的湿气或污染物混合了起来。是时候出发了。 我跑到屋外,爬到自己的车顶上,迫切想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普通人眼里,天气看上去好极了。但我发现西边有四五片棉球一样的小积云,它们正扶摇直上。其中一片会发展成我想要的风暴。云越来越高,受到随高度变化的风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云就会扭曲,传递旋转,让风暴开始自旋。云的方向也会受到影响。 我快速扫视了一下,发现这一群云彩在我西北偏西方向约20英里外;我决定往北走几英里。仅仅过了10分钟,西边的天际就暗了下来。有一片腾云在上升过程中迅速膨胀,把太阳都遮住了。这片云下方开始落雨,雷达上有一片微弱的菜豆状蓝块。雨还不大,甚至连闪电都没有产生,但它在转了。 我越过雷德河(Red River)进入俄克拉何马西南部,向凯厄瓦赌场(Kiowa Casino)招了招手,然后停在了格兰德菲尔德(Grandfield)西郊的一片地上。风暴正向东北移动,但我赌它会右旋转弯。我赌对了。除了不时有零星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这里就没有声音了。严重雷暴警告已经生效,我看到远方有弧形闪电划过泛黄的天空,从越发鲜明的风暴核心击向大地。雨幕模糊了北望的视野,但我不在乎。我想看的是上升气流,那里没有雨。 上升气流是风暴的一部分,这里的暖湿空气内旋上升。在旋转的超级单体雷暴中,上升气流就像理发店门口的灯柱一样自旋,最危险的严重天气会在这里形成,包括龙卷风。既然空气呼啸上升,那么雨就下不起来,往往会留下一个晴朗的云核。我知道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现象。我稳坐钓鱼台,是时候坐待观察了。 在超级单体雷暴的云砧之下,蓝天依然在朝南散播。一群好奇的奶牛加入了我,它们在与土路平行的铁丝网栅栏旁。我猜我们是在哞哞农场[Moo Moo Meadows,《马里奥赛车》里的一张地图。]吧,我扑哧一笑。我目睹着风暴上升气流的成长过程,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来自南方的气流像触手一样伸进了旋转中的气柱。雨和雹全都留在右边,远离上升气流。这是个好迹象。 风暴在向我逼近,于是我决定向东转移7英里。天没有下雨,而且在我越过风暴边缘时,雷达显示我上方没有降水。但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一两颗孤零零的冰雹随机砸中地面,其中一部分有半美元硬币大小。我由此得知,风暴的旋转力度肯定加强了。冰雹从旋转上升气流的核心被甩了出去。 与此同时,风暴的结构正在演化成某种优美的、预示性的东西。上升气流的核心下方垂着一面云墙,表明一个更集中的旋转区域正在朝着地面下降。远处能看到扬起的烟尘,表明来自风暴侧后方,被雨水降温后的下沉气流正涌向地面,四散开来。有时,这个过程会收紧旋转中的风暴。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开始尖叫震动,报告无线紧急预警:龙卷风警报发布了。我丝毫不意外。 同时,在方圆300英里的范围内,雷达图空荡荡的。我悄悄庆贺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但我的庆祝转瞬即逝。一道地动山摇的闪电击中了1英里外的旷野,把我拉回现实。又闪过一道,然后又是一道。我看出来了,密集的闪电是风暴上升气流转化为龙卷风的一个迹象。 又到了向东转移的时刻。这意味着要穿过主要由夯实黏土建造的路网。这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轻松通行,但随着雨滴开始落下,铁锈色的黏土已经变成了湿漉漉的“水泥”。我意识到我必须赶紧上大路,否则就有被困住的风险。 我的卡车在3英寸深的烂泥塘中艰难前行,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方向盘几乎都打不了。车子每过一个坑都会前后摇晃,车厢剧烈摆动,收音机和车载设备纷纷掉了下来。回到大路以后,我马上疾驰向南。我很清楚,风暴很快就会追上我。 两年前的经验告诉我,追风时绝不能落在风暴后面。重新追到风暴前头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钻心(core-punching)。钻心往往是徒劳无功,而且一定要经历密集的冰雹、极端的暴雨和破坏性的大风。 每过1分钟, 风暴都在演化成某种骇人之物。我距离中尺度气旋(风暴中旋转的部分)只有不到3英里,却看不见它。我正在向东南行驶,心里知道暂时牺牲视线是值得的,为的是之后获得更好的观察位置。当我绕着即将进入得克萨斯州的风暴边缘行驶时,距离拦截位置有2英里。在我向南折返,要跨过雷德河时,道路转向右侧。就是在那时,我惊掉了下巴。 超级单体已经变成了一艘母舰,一个宽达2英里,距离地表仅800英尺的巨大气旋,无数云在搅动翻腾。它就像叠成一厚摞的煎饼,黑暗、粗犷、不祥、异世界般的旋转气柱,体积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大,飘浮,旋转,不停放电。在左边,中尺度气旋的南缘像剃刀一样锋利,外面是宜人的春日午后,里面是令人避之不及的风暴,泾渭分明。右边则是中尺度气旋与半透明帷幕般的暴雨冰雹之间的模糊界线。 风暴如此强劲,我确信我西边2英里处正在落下垒球大小的冰块。我把车开下匝道,看到第一条路便右转。两旁的行道树遮住了视野。我暗骂了一句,但注意到前方有一个随意堆放的20英尺大小的土堆。我停下车,拿起相机,爬上了蚁丘似的土包。站在土包上,我有一种攀上山巅的感觉。我之前强迫症似的预测天气,现在终于有了回报。我正在目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壮观的风暴结构。 中尺度气旋硕大无朋,涤荡大地,从它下面出现了一个活跃不定的漏斗云,后经确认是龙卷风。警铃大作。可怕场面的结尾是平静到诡异的杂音。在我不知道的情形下,相当于七八个城市街区外的地方正下着直径6英寸大的冰雹,挑战着得克萨斯州的最高纪录。巨型冰雹在地上砸出了坑,甚至穿透屋顶,落入民宅。 我可不想让自己的车报废掉。在最后关头,我注意到远方有几朵翻腾的云,于是立即向南逃窜。我开始是向东跟着初始风暴走,途中停车拍了一两张照片,然后我决定把宝押在新出现的云会演变成风暴上。赌南侧的单体风暴通常会比较好,因为它们能够最畅通无阻地接收暖湿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个决定,虽然要是早15分钟做出就更好了。 我向东疾驰,在向南奔逃之前时速已经达到了75英里。我扫了一眼车载雷达显示屏,发现又有雷暴在爆发式孕育了。风暴高度刚达到50 000英尺,电台就播放了龙卷风警报。 “已确定龙卷风位于贝尔维(Bellevue)附近。”空洞的合成音效一个字一个字蹦了出来。我还是太靠北了,距离有10英里。我已经错过了它。不过,凡是有一个龙卷风的地方,往往不会只有一个,我祈祷风暴产生龙卷风的过程尚未结束。我下了高速,再次继续往南。 我每次闯入单体雷暴时,都会经历一个“暂停”时刻的洗刷。这一刻通常是在阳光消失,我打开前大灯后的几秒钟,在雨滴马上要落下,但还没有落下,风刚刚停滞的时刻。我关掉收音机,绑紧安全带,放下扶手。我们又来了,我心里想,现在没有回头路了。 冲击接着就来了,这次跟洗车似的。强度最大的风暴往往有着最陡峭的降水梯度。雨不会由小到大。要么在大雨里,要么在大雨外。我就在雨里。 雨刷器疯狂地来回扫着,我瞥了一眼GPS地图和导航雷达图。“嗯……”我嘟囔道,“这次厉害了。” 风暴运动速度并不快,但方向是往东;我是从北面来的,正好跟它成一个直角。这意味着我正正好好,硬生生闯进了风暴的穹窿,也就是环流东面的无降水区。我本来会穿过下着冰雹的风暴核心,赶在风暴从我的位置经过之前,逃到气旋运动路径的南侧。 我考虑了各个选项。我可以放弃追风,等着它从我身边经过,也就是“穿针”。这意味着我要从气旋钩状回波的“针眼”里穿出去。 一、“气象学版的谢尔顿·库珀”之马修·卡普奇,真实、传奇的“哈佛学霸”人生,疯狂的追逐风暴之旅让人为之惊叹。每天几乎平均开车狂奔500千米,在世界各地飞奔,在风暴之眼,与龙卷风赛跑;在撒哈拉沙漠,仰望群星;在旷野追逐雷暴…… 这是一场与追风暴的人共同追逐梦想之旅,一场了解气象知识的精彩知识旅程,认识自然也是重新认识自我。他带我们追逐风暴,龙卷风、飓风眼、暴风雪和星空,在北极,你可以看到雾气凝聚成的白色雾虹;在撒哈拉沙漠,你会看到雪,仰头的一瞬间可以看到5400颗星辰;在佛罗里达野火引发雷暴,你看到整个天空变成紫色。 二、在狂飙的追风暴之旅中,进行风暴知识的科普,见识形形色色的风暴。 大气是真正的教育家,自然万象瞬息万变,而不是教材中的几串公式。雷暴风雪,只有在雷雪正下方的人才能听见它的轰鸣;火积云引发雷暴与野火,充满电荷的天空噼啪作响;第一个单体风暴的侧线上已经出现了第二个风暴。所谓侧线,就是尾随雷暴形成的一串发育阶段各异的云,而身处风暴之中,既意味着完美也意味着危险即将来临…… 三、科普专业有趣,让人一打开就想一口气读完的“风暴之谜揭秘之旅”,全书收录40张风暴相关高清美图,展现惊人的震撼与美感。 “设想你在用茶匙搅动咖啡。你知道旋涡中心那个凹陷吧?凹陷(流体缺口)越深,流体肯定就转得越快。飓风同理。但是什么在阻止凹陷被填入呢?飓风眼壁处于旋转平衡状态,意思是力达成了完全的静态平衡,以至于外物“填入”稳态下的风暴几乎是不可能的。”从风暴之眼,到北极的极光与白色雾虹,再到智利高山之上的绝美日食,作者也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转瞬即逝的震撼之美。 四、不要害怕做人群中的“异类”,正如马修所说“我的人生路径是反传统的,而且坦诚地讲,是怪异的。它将我引上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踏足的道路,但我喜欢独一无二。”正是那些在荒野独自的疯狂追逐,使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人生。 即使是在哈佛大学,他也会自我怀疑“我的同学有的都结婚了,有的去了华尔街,而我最亲近的伴侣是一盆仙人掌,还浇水浇多了……,我来哈佛大学学习大气气象学,是来浪费青春吗?”但是,经历过一次次追风之旅,开着被冰雹砸地到处是坑的小皮卡,冒着被雷电,风暴,高压电流等击中的风险,住着一晚上几十美元的汽车旅馆,在无数次的冒险中,他始终坚持着对风暴的追逐。他也终于明白,自己想过的是抬头仰望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