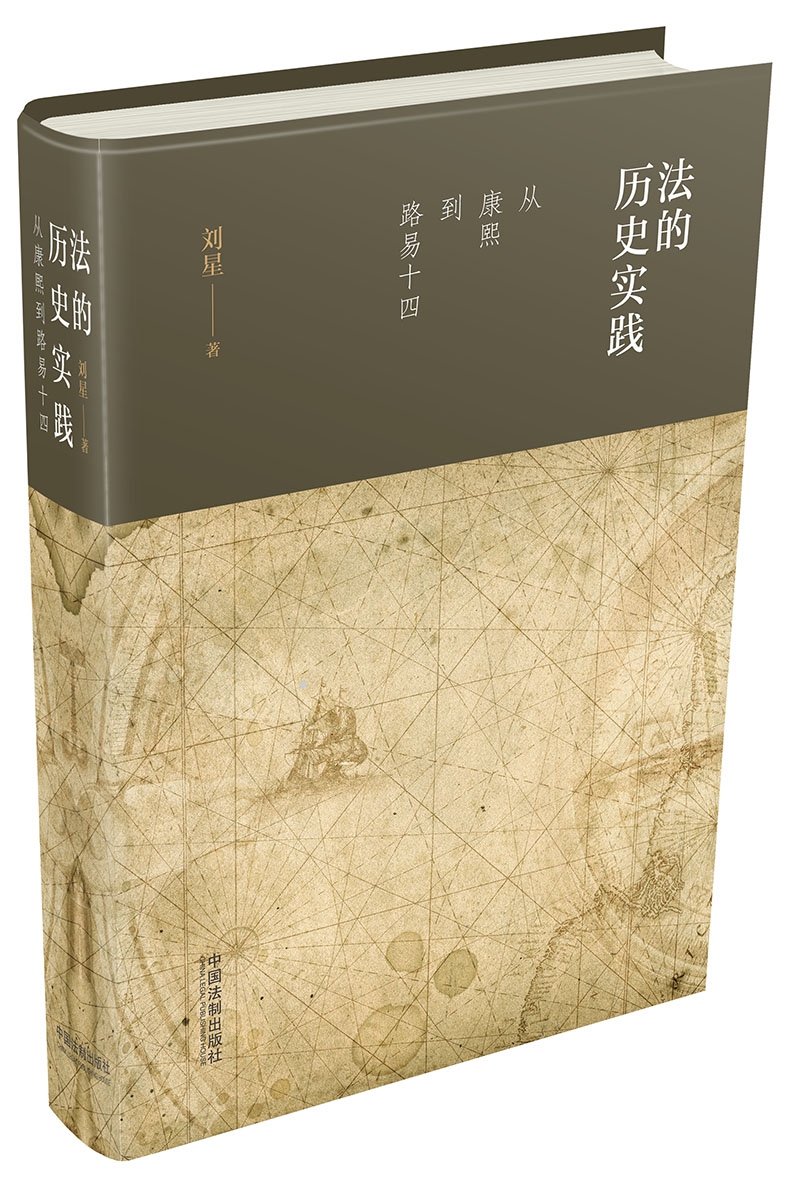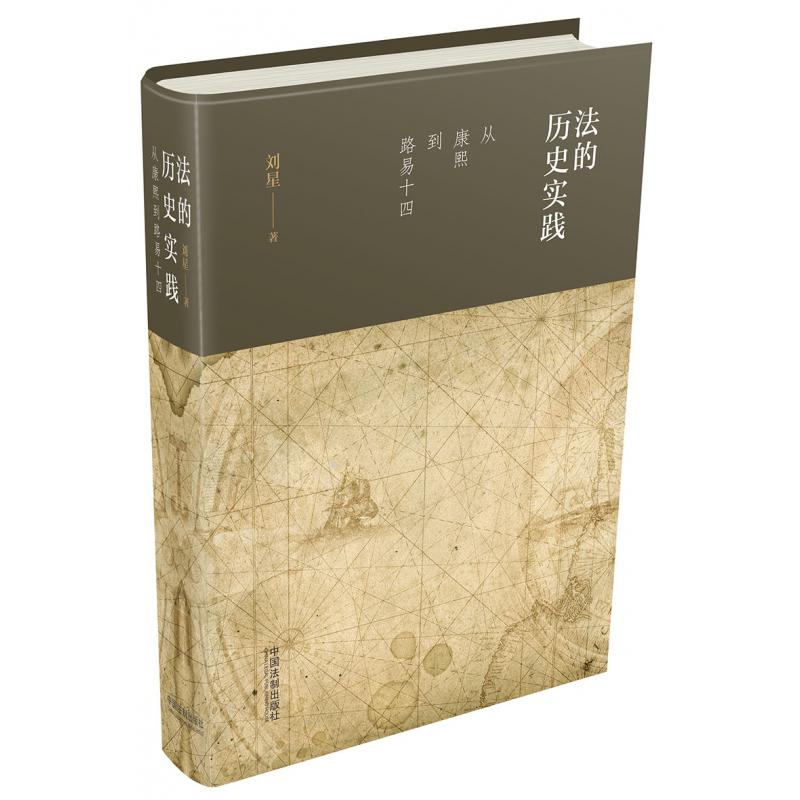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法制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7.00
折扣购买: 法的历史实践(从康熙到路易十四)(精)
ISBN: 9787509396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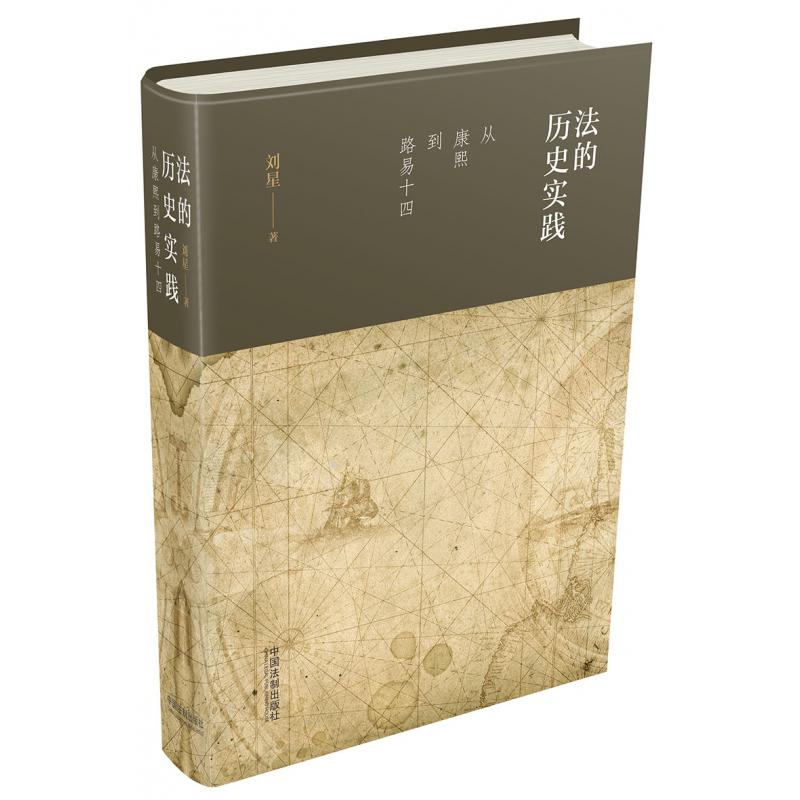
刘星 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出版《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等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 (一) 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连体一词的含义,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 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曾提到: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的,更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 自然,想象西方并不意味着仅仅树立西方的优势。“优势”的话语策略,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谋定展开的,因此,有时可能是相反的。作为对比,以及进而论证说明,我们可以注意稍早时期另外一位耶稣会士——利玛窦(M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 (一) 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连体一词的含义,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 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曾提到: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的,更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 自然,想象西方并不意味着仅仅树立西方的优势。“优势”的话语策略,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谋定展开的,因此,有时可能是相反的。作为对比,以及进而论证说明,我们可以注意稍早时期另外一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w Ricci)——对中国的恰与西方优势对冲的想象叙述。 就总体情况说,利玛窦在中国是相当顺利的,生活三十余年,终于定居京城北京,进入宫廷,博得皇帝垂青,取得合法传教地位,并且享有特殊待遇。于是,在自己的札记中,他赞扬性地描述过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说,就法定皇位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亲属而言,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亲属的另一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审讯和判决”。利玛窦同时提到,在中国“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家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此外,他还宣称: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 ……attew Ricci)——对中国的恰与西方优势对冲的想象叙述。 就总体情况说,利玛窦在中国是相当顺利的,生活三十余年,终于定居京城北京,进入宫廷,博得皇帝垂青,取得合法传教地位,并且享有特殊待遇。于是,在自己的札记中,他赞扬性地描述过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说,就法定皇位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亲属而言,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亲属的另一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审讯和判决”。利玛窦同时提到,在中国“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家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此外,他还宣称: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 …… ◎消除误解、树立文化自信:近现代以来,中西之间是双向交流,并非人们一直认为的中国单方面地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作者有别于一般中西比较和历史比较,提出了新的思路。 ◎以“个案研究”为手段:从康熙、利玛窦等中西具体人物对法律的使用、翻译和交流实例展开,将法律放在社会环境、政治目的、历史事件等具体语境中讲述,更易于理解。 ◎贴近“日常话语”和“文化”:置身文化背景和日常生活,以社会学、历史学视角分析法律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生动具体,可读性强。 ◎曾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兼备,本次由作者亲自修订,更新了文献版本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