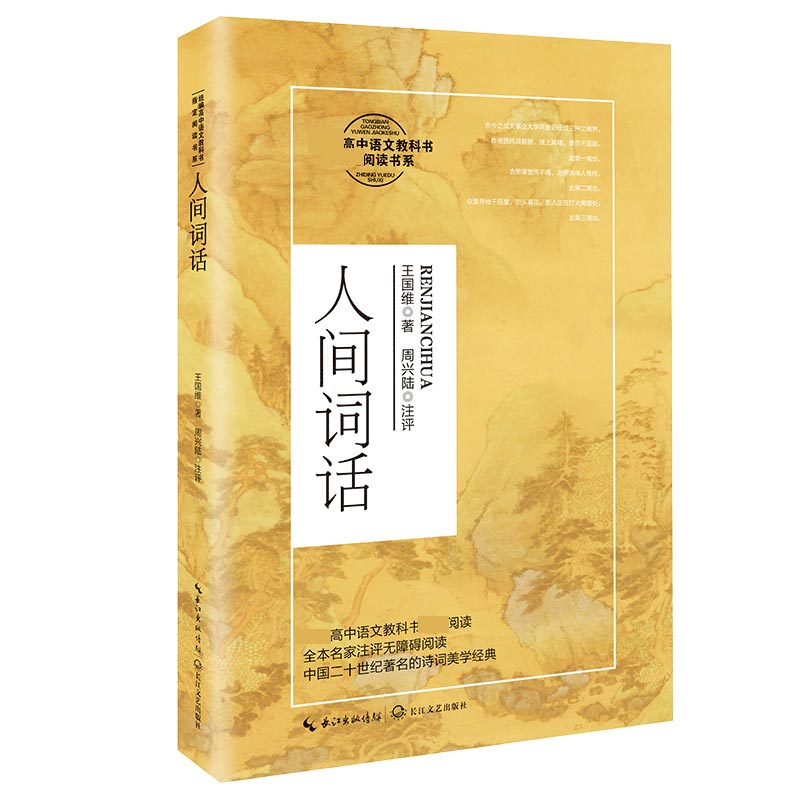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2.60
折扣购买: 人间词话(高中语文教科书阅读书系)
ISBN: 9787570215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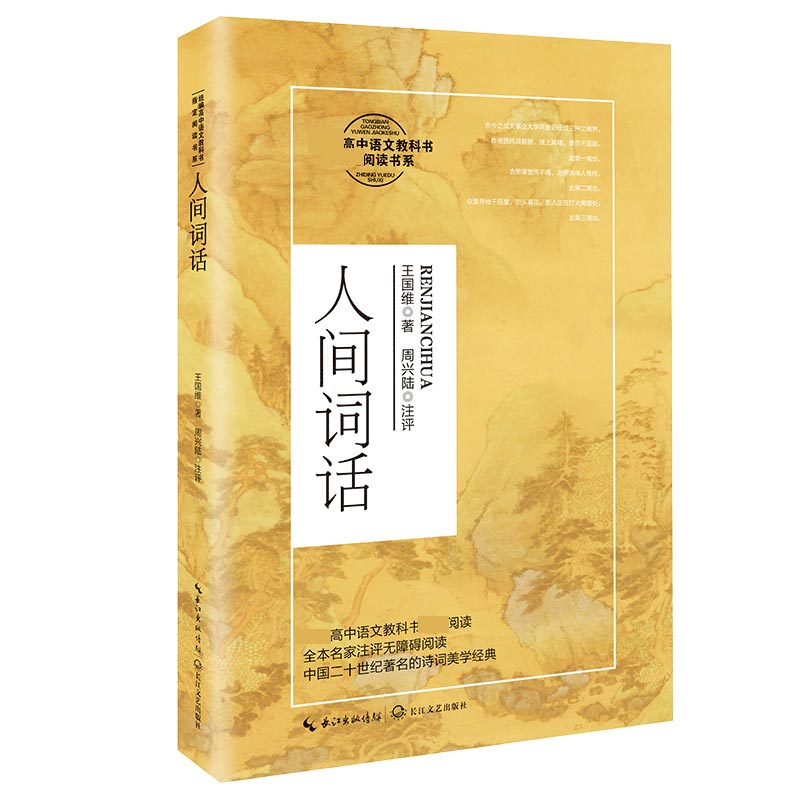
王国维(1877—1927),中国近现代学者,浙江嘉兴海宁人。他生逢变革年代,为学术和谋生,两考乡试,三赴日本,辗转京沪。一生著述62种,在戏曲、诗词、哲学、美学、史学、金石、考古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人间词话》导读 周兴陆 一、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王国维忧生忧世的人生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永观等。1877年12月3日(农历十月廿九)出生在浙江海宁。父廼誉,清诸生,习书画,能仿杭州钱杜(字叔美)之作。得之于家庭的熏陶,王国维对书画有一定的鉴赏力。父王廼誉尝游幕溧阳。值太平军乱,乃弃幕就商。王氏家境清贫,一年所入,仅足给衣食。但童年的生活在后来的诗歌里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昔游》)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心生喜悦。拿出小时积攒的压岁钱,从杭州购得前四史,开启了读书生涯。然不喜《十三经注疏》,也不专事帖括,读书唯究经史大义。弱冠肄业于杭州敷文书院,两应乡举而不售。他并非早慧。早年的《杂诗》里就把自己比喻为生长七年仍不成株的豫章树,结果被交付于拙工之手,削斫得面目全非。 1898年初,22岁的王国维离开家乡到上海《时务报》馆作书记员,做一些校对报纸、抄录信笺的事,薪水低,工作枯燥,然自此“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不久后的一天,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的上虞罗振玉去报馆找汪康年,不值,恰看到王国维《咏史》,颇为欣赏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二句,于是引入东文学社,从此与罗振玉结下了终身之缘。第二年留学日本物理学校,但仅数月因脚气病归国。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当时正发生“戊戌政变”,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和人生理念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社会和人生的问题,日萦脑际,促使沉静忧郁的王国维去思考。因此王国维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穿透时空表象的深邃和莫可名状的孤独。1899年,时仅23岁的他,便咏出:“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题友人三十小像二首》其一)他只身异地,心头无端地涌起“四海一身原偶寄”的凄凉。身体之病弱和心灵的忧郁敏感强化了他心头上与环境的生疏对立:“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杂感》)此时的东文学社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务,而王国维的兴趣则偏重于哲学。通过日籍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治二君,王国维间接得知康德、叔本华哲学。 1903年春,王国维应张謇邀请,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这一年夏天,开始读西方哲学、心理学著作,沉浸其中,眼界大开,非常快乐。《端居三首》其一曰:“端居多暇日,自与尘世疏。处处得幽赏,时时读异书。高吟惊户牖,清谈霏琼琚。”这异书就是康德专著《纯粹理性批判》之类的西方哲学书,当时“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王国维一直在思索人生的本质,此时他是苦闷的。《端居三首》其二曰:“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身处的环境、人事似乎总与他相矛盾,激起心中的不平。既未闻道,“逐物又未能”,“冥然逐嗜欲,如蛾赴寒檠”,所以他希望像庄子那样“吾丧我”,可以“表里洞澄莹”。稍后,王国维读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今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好之”,称其“思精而笔锐”,读之不已,更广涉叔本华其他哲学论著。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之所以和王国维一拍即合,一方面是由于叔氏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顺应当时的时势思潮,也顺应王国维少年时即表现出的求新求异的、叛逆的倾向;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两人有着深度的契合点。叔氏悲观主义哲学可谓深契“性复忧郁”的王国维的心,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有深刻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抹上一层厚重的悲观色彩和悲剧精神。1903年《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的“江上痴云犹易散,胸中妄念苦难余”;《偶成二首》(其一)的“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免襁褓,役物固有馀”;《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的“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等诗句,其中的人生意识都浸透着叔本华哲学的内涵。此时他因为接受西学,自谓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有“众人皆醉我独醒”感觉,所以“人生过处”二句之后又感慨说:“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似乎众人都还在睡梦之中。王国维家在浙水滨,农村的养蚕,给他深刻的印象,他以蚕比喻人生:蚕化为蛾,蛾生籽再孵为蚕,“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蚕》),人生也是如此,造化弄人,让人“草草阅生死”却无法摆脱。人生就像蚕,作茧自缚,还在茧中钻营。“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偶成二首》其二)。首句来自《老子》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如何摆脱嗜欲的挟制呢,此时他想到佛教,“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此语说得容易,“践之良独难”。甚至就连释迦牟尼也只好在尘世里枯老终生了。《平生》就说:“人生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王国维诗词并非全部都是如此的低沉抑郁,也有过明媚的光亮。1904年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聘请王国维来任教,并协助《教育世界》的编辑。这时王国维心情有过短暂的晴朗,赴任时经过嘉兴西南的石门镇,“老桑最丑怪,亦复可怡悦”;“非徒豁双眸,直欲奋六翮”(《过石门》),似乎自此可以奋翮远翥。甚至他也偶尔年少轻狂过,如作于1904年秋的《浣溪沙》:“草偃云低渐合围,雕弓声急马如飞,笑呼从骑载禽归。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但是短暂的激扬之后,随即而来的是沉重无法排解的忧愁。 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忧生”和“忧世”一齐挤压着他,驱策他不断地去解索人生的困惑,追寻人生的真谛,为疲惫的心灵讨取片刻的安慰和宁静。青年时期的王国维就抱有浓郁的厌世情绪,甚至想找一个安静处隐居起来,读尽天下奇书。1903年的《重游狼山寺》曰:“此地果容成小隐,百年那厌读奇书。君看岭外嚣尘上,讵有吾侪息影区。”身体有病的人,总感觉到肉体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人生的累赘,是对精神自由的羁绊。因此灵魂和肉身往往是分裂的。王国维诗中就表现这种分裂。《来日二首》其一云:“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精神寄寓在肉体之内是很偶然的事。但沉重的肉身,像荆棘一样阻止他的步伐。“我力既云痡,哲人倘见度。”唯有哲学可以超度灵魂,洞彻人生,所以他乞灵于哲学。恰在此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像闪电一样击中他的心灵,似乎他苦苦追寻的人生问题,有了彻底的解答。他的《欲觅》诗云:“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与生俱来的忧愁没有穷尽,需要安顿。当时的安顿之处,就在叔本华哲学的启示。《叔本华像赞》曰:“公虽云亡,公书则存。愿言千复,奉以终身。”似乎终身要成为叔本华的追随者。30岁之前,王国维主要精力在介绍和钻研西方哲学美学,特别是自己所信奉的叔本华、尼采哲学。1904年就发表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谢国桢《悼静安先生》说他“首倡尼采学说,实为介绍西哲之学第一人”。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全以叔氏为立脚地”,此外像《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都是运用叔本华、尼采、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学问题的有名之作。 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指定阅读,全本名家注评无障碍阅读,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诗词美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