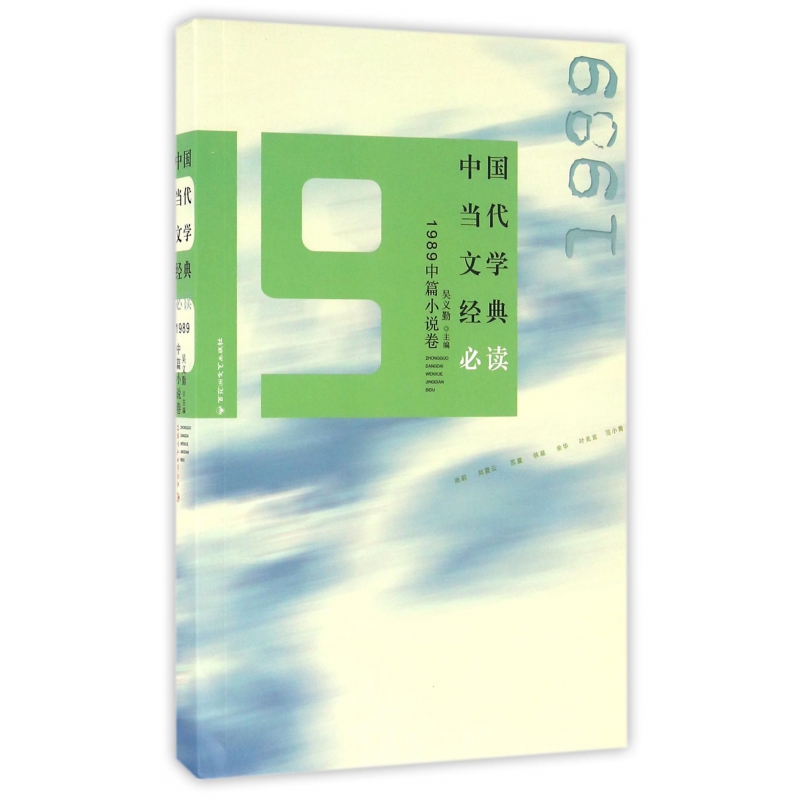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1.30
折扣购买: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中篇小说卷)
ISBN: 9787550017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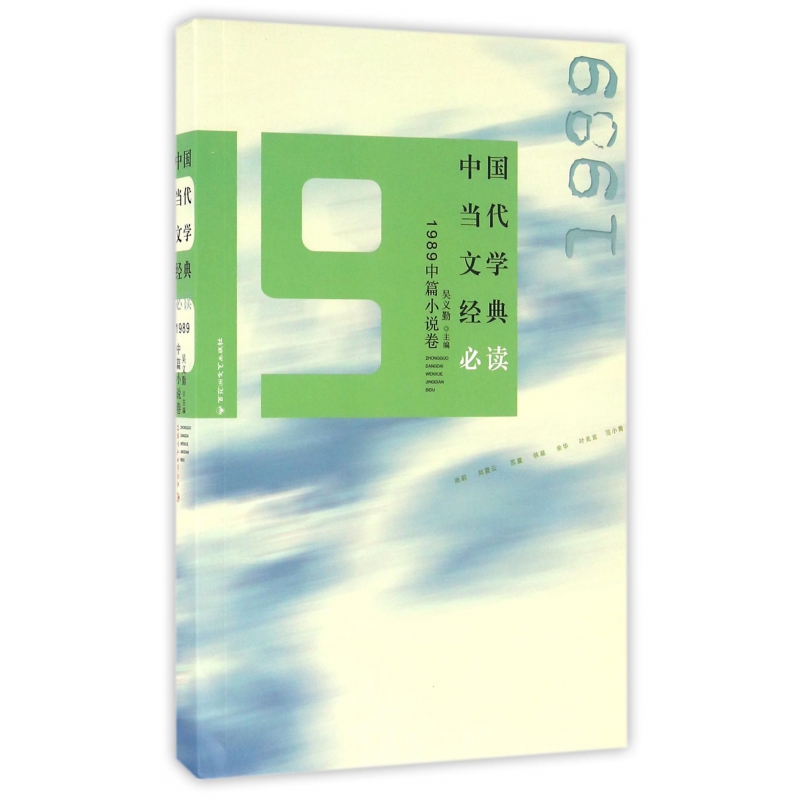
吴义勤,文学博士,教授,博土生导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 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 ,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 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 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但吉玲的母亲对她的五个女儿一再宣称:“我从 没当过婊子。” 吉玲的母亲是个老来变胖的邋遢女人,喜欢坐在 大门敞开的堂屋里独自玩扑克牌,松弛无力的唇边叼 一支香烟,任凭烟灰一节节滑落在油腻的前襟上。但 是一旦有了特殊情况,她可以非常敏捷地把自己换成 一副精明利索洁净的模样。她深谙世事,所以具备了 几种面目。五个女儿中,她最宠吉玲。她感到吉玲继 承她的血脉最多。 “胡说八道!”吉玲恼火地否定。母亲只管嘿嘿 地笑。 吉玲的父亲这系人祖祖辈辈住在花楼街。别人用 什么眼光看待花楼街那是别人的事,父亲则以此为荣 。他常常神气十足地乱踢挡住了路的菜农的竹筐,说 :“这些乡巴佬。”就连许多中央首长都经不起追溯 ,一查根基全是乡巴佬。而他是城市人。祖辈都是大 城市人。父亲从十三岁起就到馨香茶叶店当徒工。熏 得一身茶香,面色青白,十指纤细柔弱,又出落了一 张巧嘴巴。其巧有二:一是品茶,二是善谈。属于那 种不管对象是谁都能聊个天昏地暗的人物。 五个女儿全都讨厌父亲,公开地不指名地叫他为 “鼻涕虫”,因为几个女儿先后找的几个男朋友都因 为被父亲黏住大谈其花楼街掌故和喝茶的讲究而告失 败。 母亲经常率领四个女儿与父亲打嘴巴仗,吉玲从 不参与,只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瞥一眼父亲,而 父亲倒有几分怯她。 吉玲是个人物。 吉玲上学时学习成绩不错。但命运多舛,高考参 加了两届都未能中榜。母亲开始威逼父亲退休让吉玲 顶替,吉玲说:“不。我自己想办法找工作。”父亲 因此对女儿感激涕零。 吉玲的穿着打扮与花楼街的女孩子格调相反。她 以素雅为主。不烫发,不画眼影,最多只稍稍描眉和 涂一点肉色口红。常是浅色衬衣深色长裙,俨然一个 恬静美丽的女大学生。 她在社会上交朋结友不久,便找到工作,在一家 酒类批发公司当开票员,几个月后又换到一个群众团 体机关办公室当打字员。打字工作很辛苦,半年后一 个朋友的叔叔把她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较大的新华书 店。 新华书店文明、干净,到处是知识,又是国家事 业单位,这种位置来之不易,吉玲满意了。她全靠自 己,声色不动地调换了几次工作,既没花什么实质性 的代价,又没有闹出什么风言风语,她深感自豪。她 的父母也深感骄傲。花楼街的邻居街坊自然地为之骄 傲。 “你看吉家的幺女儿,我们花楼街的嘛。”他们 说。 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吉玲的身价。 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轮到找对象。 吉玲的四个姐姐在这事上都是自己蹦跶过一阵子 ,其中两个姐姐还未婚先孕,但终归哭呀闹呀的没成 功,最后还是由介绍人牵线搭桥完的事。四个姐夫第 一个是皮鞋店售货员,第二个是酱油厂工人,第三个 是铁路上搬道岔的,第四个是老亏本也不知做什么生 意的个体户,腰里总是别一把弹簧刀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这群人,吉玲眼角都不斜他们。眼看母亲、姐姐 又在为自己的婚事蠢蠢欲动,吉玲说:“我的事不用 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她们四个都放过这种屁。”母亲说。 “我不是她们。” “那就走着瞧吧。”母亲把扑克洗得哗哗脆响, “我的儿,不是做娘的没教导你。你可是花楼街的女 孩子。蛤蟆再俏,跳不到五尺高。是我害了你们,我 受骗了,揭了红头盖,才看清嫁到了花楼街。” 父亲眉头一扬,抿了一小口茶。 “好好。那我倒要与你理论一番了。你说是上当 受骗,那媒人——” 吉玲喝道:“又来了!不斗嘴没人把你们当哑巴 的。”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