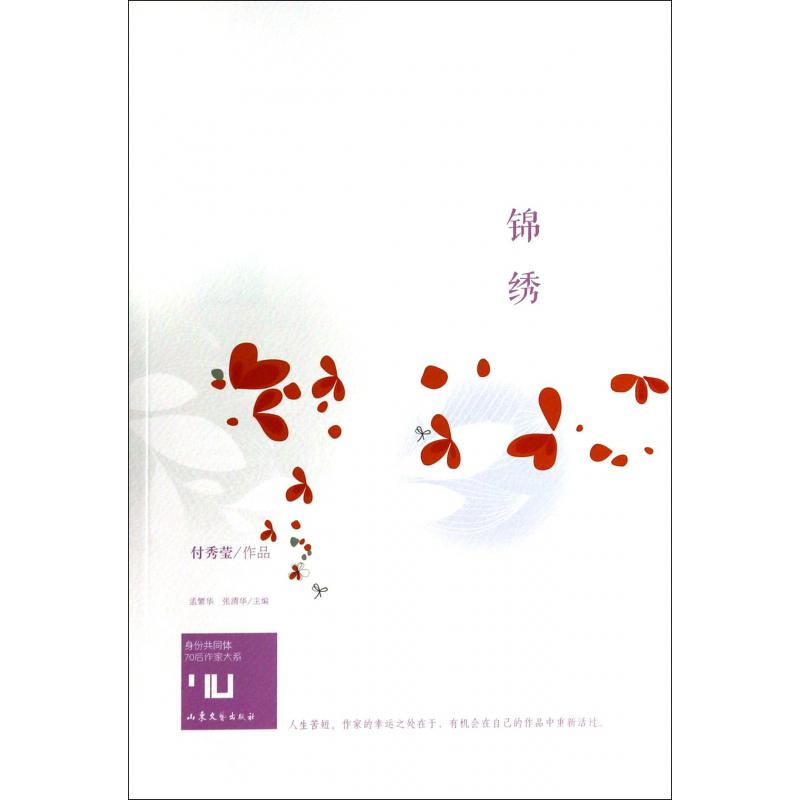
出版社: 山东文艺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2.80
折扣购买: 锦绣/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
ISBN: 9787532944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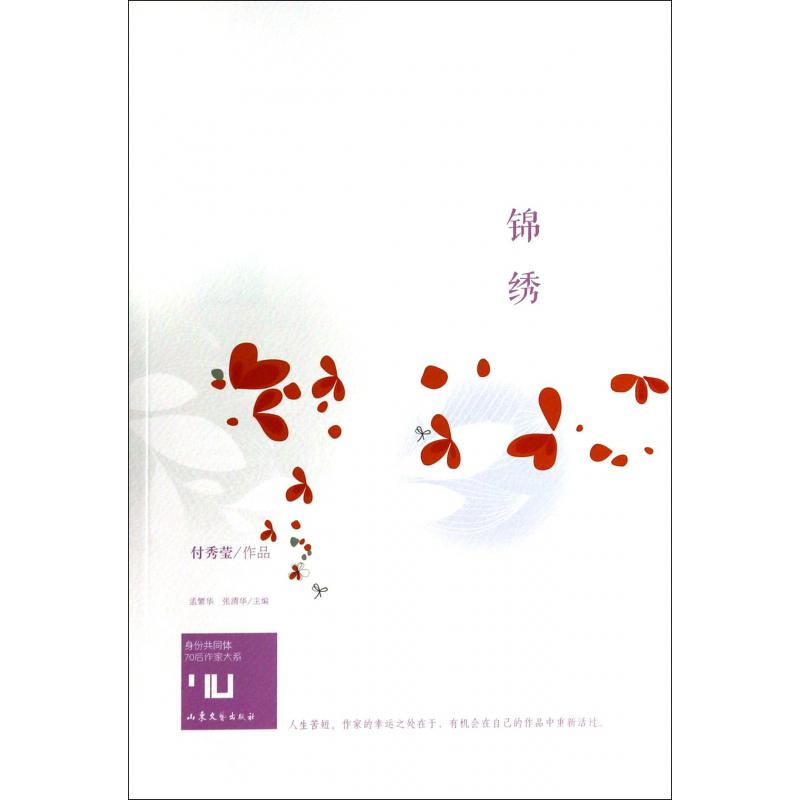
付秀莹,女,有多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著有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等。曾获首届、第四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品奖、优秀编辑奖,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旧院 一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旧院指的是我姥姥家的大院 子。为什么叫旧院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过。 当然,也许有一天,我想了,可是没有想明白。甚至 ,也可能问了大人,一定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我 歪着头,发了一会呆,很快就忘记了。是啊,有那么 多有趣的事情,爬树,掏蚂蚁窝,粘知了,逮喇叭虫 。这些,是我童年岁月里的好光阴,明亮而跳跃。我 忘不了。 旧院是一座方正的院子,在村子的东头。院子里 有一棵枣树,很老了。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房 顶。春天,枣花开了,雪白的一树,很繁华了。到了 秋天,累累的果实,在茂密的枝叶间,藏也藏不住。 我们这些小孩子,简直馋得很,吮着指头,仰着脸, 眼巴巴地看着表哥攀上树枝,摘了枣子,往下扔。我 们锐叫着,追着满院子乱跑的枣子,笑。每年秋天, 姥姥总要做醉枣,装在陶罐里,拿黄泥把口封严。过 年的时候,这是我们最爱的零嘴了。 姥姥是一个很爽利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大概 也是个美人。端庄的五官,神态安详,眼睛深处,纯 净,清澈,也有饱经世事的沧桑。头发向后面拢去, 一丝不苟,在脑后梳成一只光滑的髻。在我的记忆里 ,似乎,她一直就是这种发式。姥姥一生,共生养了 九个儿女,其中,有三个,夭折了。留下六个女儿。 我的母亲,是老二。 谁会相信呢,姥姥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嫁给姥爷 。并且,一生为他吃苦。说起来,姥爷祖上原是有些 根基的,在乡间,也算是大户人家。后来,到了姥爷 的父亲这一辈,就败落了。姥爷的母亲,我不大记得 了。在姥姥的描述里,是一个刁钻的婆婆,专门同儿 媳妇过不去。姥爷是家里的独子,幼年丧父。寡母把 独子视为命,视为自己一世艰辛的见证。儿子是她的 私有物,谁都不允许分享,即便是儿媳妇。有坚硬强 势的母亲,往往有软弱温绵的儿子。在姥爷身上,有 一种典型的纨绔气质。当然,我不是说姥爷是吃喝嫖 赌的纨绔子弟——以当时的家境,也当不起这个字眼 了。我是说,气质,姥爷身上有一种气质,怎么说, 闲散,落拓,乐天,也懦弱,却是温良的。在他母亲 面前,永远是诺诺的。而对姥姥,却有一种近乎骄横 的依赖。里里外外,全凭了姥姥的独力支撑。姥爷则 从旁冷眼看着,袖着手,偶尔从衣兜里摸出一把炒南 瓜子,或者是花生,嘎巴嘎巴剥着,悠闲自在。老一 辈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姥姥生养了九个儿 女,竟没有给翟家留下一点香火,真是大不孝了。只 为这一条,姥姥在翟家就须做小伏低。作为一个女人 ,她欠他们。姥姥日夜辛劳,带着六个女儿,不,是 五个——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姨,被寄养在姨姥姥 家。姨姥姥是姥姥的姐姐,嫁给了一位军人,膝下荒 凉,就把我大姨要了过去,做女儿。姨姥姥家境殷实 ,把大姨爱如掌上明珠。虽如此,后来,大姨成人之 后,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甚至,有一回,她来看 望姥姥,言语间争执起来,大姨说,我早就知道你不 喜欢我,那么多姊妹,单单把我送了人。姥姥一时气 结,哭了。她再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女儿会这样 指责自己。当然,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生产队。我一直对这个词 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那一代,有谁 不知道生产队呢?人们在一起劳动,男人和女人,他 们一边劳动,一边说笑。阳光照下来,田野上一片明 亮,不知道谁说了什么,人们都笑起来。一个男人跑 出人群,后面,一个女人在追,笑骂着,把一把青草 掷过去,也不怎么认真。我坐在地头的树底下,饶有 兴味地看着这一切。那时,我几岁?总之,那时,在 我小小的心里,劳动,这个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温暖,欢乐,有一种世俗的喜 悦和欢腾。如果,劳动这个词有颜色的话,我想,它 一定是金色的,明亮,坦荡,热烈,像田野上空的太 阳,有时候,你不得不把眼睛微微眯起来,它的明亮 里有一种甜蜜的东西,让人莫名地忧伤。 我很记得,村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经了多年 的风雨,很沧桑了。树上挂了一口钟,生满了暗红的 铁锈。上工的时候,队长就把钟敲响了。当当的钟声 ,沉郁,苍凉,把小小的村庄都洞穿了。人们陆续从 家里出来,聚到树下,听候队长派活。男人们吸着旱 烟,女人们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子。若是夏天,也有 人胳膊底下夹着一束麦秸秆,手里飞快地编小辫。水 点子顺着麦秸淌下来,哩哩啦啦洒了一路。村子里骤 然热闹起来。说话声,笑声,咳嗽声,乱哄哄的,半 晌也静不下来。我姥姥带着女儿们,也在这里面。这 些女儿当中,只有小姨上过学,念到了六年级,在当 时,很难得了。有人重重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人群 渐渐安静下来。生产队长开始派活了。 生产队,是记工分的。姥姥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 ,时时处处都不甘人后。多年以后,人们说起来,都 唏嘘道,干起活来,不要命呢。我至今也不明白,姥 姥那样一个秀气的身子,怎么能够扛起那么重的生活 的重担。姥爷呢,则永远是悠闲的,袖着手,置身事 外。我姥爷最喜欢的事情,是扛上他那支心爱的猎枪 ,去打野物。我们这地方,没有山,一马平川的大平 原。有河套。河套里面,又是另一番世界。成片的树 林,沙滩,野草疯长,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绚 烂极了。夏天的清晨,刚下过雨,我们相约着去河套 里拾菌子。在我们的方言里,这菌子有一个很奇崛的 名字,带着儿化音,很好听。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 两个字。这种野菌子肥大,白嫩,采回来,仔细洗净 沙子,清炒,有一种肉香,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 河套里,还有荆条子,人们用锋利的刀割了,背回家 ,编筐。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也去河套里挖扫帚苗 ,摘蒺藜。村里的果园子也在河套。大片的苹果树, 梨树,一眼望不到头。秋天,分果子的时候,通往河 套的村路上,人欢马叫,一片欢腾。对于我姥爷来说 ,河套的魅力在于那片茂密的树林。常常,我姥爷背 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里转悠,一呆就是大半天。黄 昏的天光从树叶深处漏下来,偶尔,有一只雀子叫起 来,跟着一片喧嚣。忽然就静下来。四下里寂寂的, 光阴仿佛停滞了。我姥爷抬头看一看树巅,眼神茫然 。他在想什么?我说过,我姥爷的身上,有一种纨绔 气质。这是真的。弯弯的村路上,一个男人慢慢走着 ,肩上扛着猎枪,枪的尾部,一只野兔晃来晃去,有 时候,或者是一只野鸡。这是他的猎物。夕阳照在他 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虚,很长。 通常情况下,我姥姥对我姥爷的猎物不表达态度 。几个女儿倒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叫着,知道这两天 的生活会有所改善。姥爷把东西往地下一扔,舀水洗 手,矜持地沉默着。这沉默里有炫耀,也有示威,全 是孩子气的。在这个家庭中,以姥姥为首,姥爷除外 ,全是女将。姥爷这个唯一的男人,在性别上就很有 优越感。姥姥比姥爷大。姥爷的角色,倒更像一个孩 子,懒散,顽劣,有时候也会使性子,耍赖皮。对此 ,姥姥总是十分地容让。当然,也生气。有一回,也 忘了因为什么,姥姥发了脾气,把一只瓦盆摔个粉碎 。姥爷呆在当地,觑着姥姥的脸色,终于没有发作。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