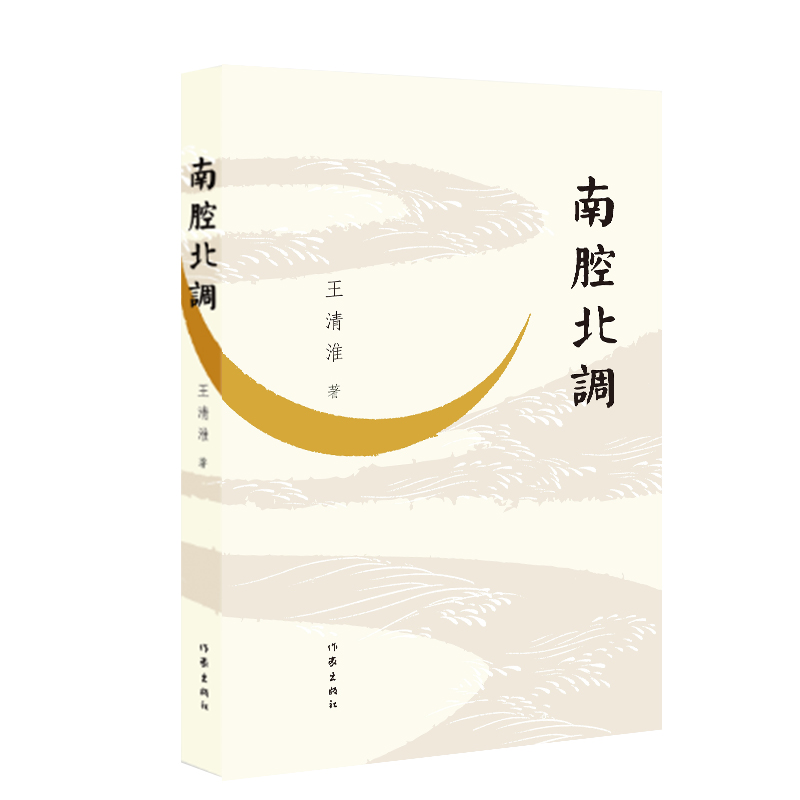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3.80
折扣购买: 南腔北调
ISBN: 9787521217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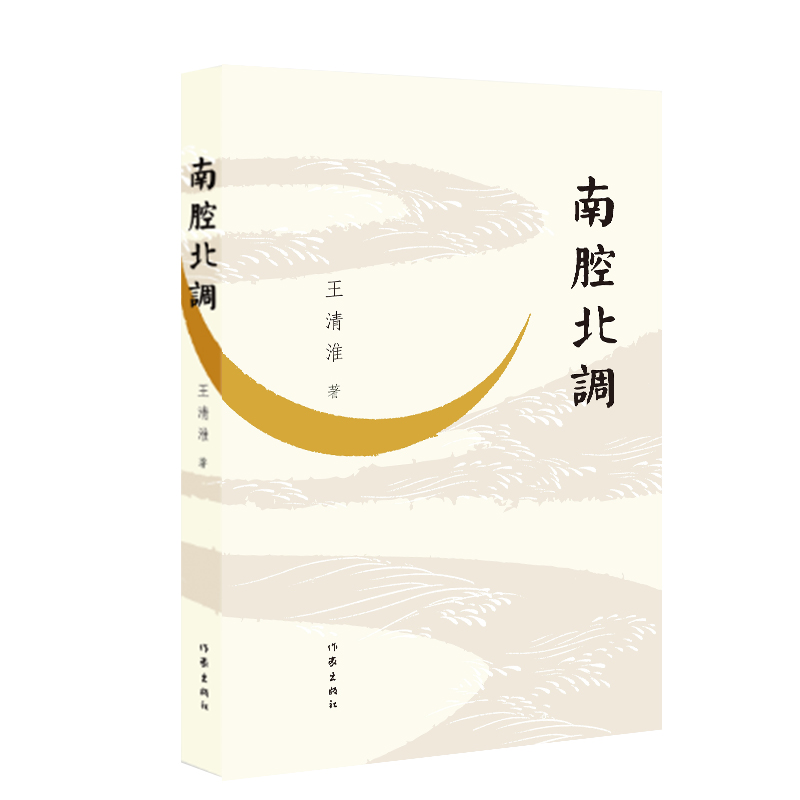
王清淮,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多年从事鲁迅研究。著有《问天者——张衡传》《新史记》(一)(二)《唐太宗》《中国文化别论》《中国文化史略》《中和论》《公安文化通论》《唐诗品》等。
“王二羊”煎饼 辽宁喀左县城关不大,却叫“大城子”,大城子镇有一家羊汤馆,卖羊汤和羊杂,名“王二羊杂馆”,可能风水所致,来来往往的人都叫它“王二羊”,省去“杂馆”,店主想方设法在招牌上做记号,强调自己是“王二”,不是“王二羊”,可是毫无效验,人们还是叫他王二羊,外地人到喀左,蒙古族地界,想喝碗羊汤暖和暖和,一抬头:“嘿,王二羊?就它了!”紧着招呼:“快来这里呀,王二羊!” 王二羊的羊汤才是真正的羊汤,以羊为主,汤做陪衬,“羊”又分羊肉羊杂羊内脏三大类,都是满满冒尖的一大碗,羊肉汤填缝,使羊肉羊杂更扎实。肉多汤少?没关系,汤任意添,一家三口一份“王二羊”,几张煎饼,就是可以吃到得意忘形的一顿早餐。在外地,我从不喝羊汤,外地的羊汤绝对不是羊汤,该叫“米汤”:一大碗浑浊的液体,羞涩地漂浮着几片羊肚羊肺。喀左不比凌源有“凌钢”,朝阳有“朝重”,北票有煤矿,喀左的优势项目是吃喝,喀左人到哪儿都不打怵,因为他们吃喝的底气足:“陈醋、紫砂,王二羊!”外地人便灰溜溜,肯定比不过啊,陈醋、紫砂那么著名,王二羊,虽然没听说过,但是能跟陈醋、紫砂并列,也一定是厉害角色,也就不敢打听“王二羊”到底是啥。 给王二羊的食谱排座次,第一位的竟不是羊汤,而是煎饼,朝阳地区特有的煎饼,以喀左为代表。宋晓峰一伙山贼打劫饭店,劫到一盘饺子,宋晓峰一口咬下去,场上煽情的音乐响起,小宋脸上千变万化,张开大嘴喊道:“好吃啊——”这情景我太熟悉了,那年我带儿子回喀左老家,在十二德堡镇上买煎饼卷小葱,儿子咬了一口,张开嘴大叫:“好吃啊——”跟宋晓峰的表情一模一样,咬下的那一节煎饼掉在地下,也跟那饺子一个下场。 中国的煎饼分三派。山东煎饼干而硬,算原味煎饼,适合卷大葱,但煎饼硬大葱柴,紧慢咬不动,吃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结果,往往是把煎饼卷重新展开,煎饼和大葱分别吃。临沂应该是原教旨的煎饼,绵软润甜,朝阳煎饼也正是继承了山东临沂的煎饼,才是今天的模样,可是当今临沂人有钱任性,改用白面摊煎饼了,这就违背了煎饼“粗粮细做”的原则。煎饼原材料应该是粗粮,高粱玉米小米等等,细粮是贵族,刚摊成时绵软柔润,稍一冷却就酥脆如薄冰,不是煎饼了。第二项原则是磨浆,磨浆的煎饼才更有韧性,小麦磨浆与白面打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今山东煎饼包括临沂的,都是打浆,味道口感都逊色了许多。第二派是直隶煎饼,以北京、天津煎饼为代表,这两地的煎饼跟北京人、天津人一样讲究排场,明明小市民填饱肚子的食物,却设计得跟姑娘出嫁一样隆重,主料三四种,辅料七八种,叮叮当当整得热闹。这种被誉为“中国麦当劳”的街头食品,过于瘫软,没咬头,薄脆完全失去本色,在软兮兮的煎饼里消失不见了,鸡蛋也吃不出鸡蛋的味道,被酱料等掩盖住。吃北京煎饼,总能听到周星驰的配音:“碱水面没有过过冷水,所以面里面都是碱水味;鱼丸也没有鱼味,但是你为了掩饰,特别加上了咖喱汁,想把它做成咖喱鱼丸,但这么做太天真了!因为你煮的时间不够,咖喱的味道只留在表面上,完全没有进到里面去,泡进汤里又完全被冲淡了,好好的一颗咖喱鱼丸让你做得是既没有鱼味有没有咖喱味,失败!萝卜没挑过,筋太多,失败!猪皮煮得太烂没咬头,失败!猪血又烂稀稀的一夹就散,失败中的失败!最惨的就是大肠了……你有没有搞错啊你!” 北京煎饼,整个就是被周星驰批判的火鸡莫文蔚失败的杂碎面! 第三派就是朝阳煎饼,王二羊煎饼代表喀左,也代表朝阳煎饼,因为朝阳煎饼的发源地就在喀左大城子。其实,王二羊店面很小,只做羊汤,不摊煎饼,他的煎饼都是专门从煎饼店里趸来的,但是吃煎饼的才不管那些,从哪家吃,就认定是哪家煎饼,所以“喀左王二羊煎饼”横空出世,大的煎饼铺比如“和发煎饼”,名气反倒不如王二羊。 朝阳煎饼也叫热河煎饼,这里蒙汉杂居,饮食习惯融合,热河煎饼即喀左煎饼,以山东煎饼为底子,改革掉它的干硬,拒绝京津煎饼的瘫软,以平和的韧性为特长。原料小米或玉米,辅料黄豆,一定要用石磨磨成浆,然后半发酵。成品煎饼微酸,然后用小葱和香菜,蘸少许面酱中和,卷成黄绿相间的圆筒,煎饼的韧和小葱的脆自然交汇,半发酵饼的甜香和葱的微辣在空气中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不等入口,食客就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真香!”感慨很可能就是一阵欢呼:“好吃啊——” 喀左茶 喀喇沁左翼县的特产,还有另一种排序:紫砂、陈醋、茶。 喀左出产茶叶?茶业专家怯怯地问我:“请问贵乡地理位置,北纬多少度?”我说:“北纬42°!”专家很为刚才的谦卑懊恼,他说:“纬度这么高,有茶?山东临沂,北纬35°,是茶分布的最北界吧?”疑问随他去,事实我坚持:这里就是有茶!喀左县城旧称利州,全城三五步一个茶庄,一条街几座茶馆,而且茶叶价格便宜,质量过硬! 喀左产茶的事等一会儿再说,先说喀左人喝茶。喀左虽然是蒙古族自治县,居民却九成是汉人,但这些汉人沾染了胡风,跟胡人一起喝粗犷豪迈的红茶,南方人钟爱的绿茶,北京人喜欢的茉莉花茶,文人气太重,蒙古人不喜欢,喀左的汉人也不喜欢。在喀左,喝红茶也能喝出小资情调。原来,只要喝红茶,不论穷富,都能成小资。 老爸上山割柴,第二天肩挑一担柴二百斤……哦,没那么重,那时候我年龄小,一捆柴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山。老爸担柴一二百斤,走路十五公里,到县城去卖。那时候物价超级稳定,几十年不变,一担柴一定卖一块钱。忙活两天,收入一块。老爸喜滋滋,出了柴草市就奔酒馆,两角钱饭菜,两角钱烧酒,酒足饭饱,且不忙回家,出了酒馆奔茶馆,一盏红茶一壶水,再花两角钱,底气充足支使茶博士:“老板,添水!”喝到日头偏西,怀揣四角钱回家,交给我老妈,老妈眉开眼笑:这么多钱哪! 喀左人爱茶,不管时代变迁,大饥荒年代,茶也未曾绝迹,原来小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不拘贫富。我家居住偏僻,路远隔深辙,穷巷寡轮鞅,忽然一个年轻人造访:走路口渴,想进门喝茶。说完赶紧补充:“我自己带着茶叶的。”进屋盘腿打坐炕上,打量简陋的屋舍,不像能够给他提供茶点摆几个果盘的样子,就算了,寡饮。水烧开了,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纸包,展开,是刚买的红茶,整整齐齐的红茶梗,他捏出一小撮,展开在桌子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数了三十颗,余下的放回去,重新包好,又装回背包。古人说“称薪而爨,数米而炊”,这事就发生我的面前。更奇的是那三十颗茶梗,他喝完三壶水,茶汤依然浓烈如新烹。 喀左本地出产一种名贵茶:喀左岩茶。这种茶草本,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背阴不见阳光没有足迹踏过的高耸岩石。这样的岩石原本不多,岩石上有土的更少,所以喀左岩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只有少数“小资”自采自制,晾晒揉炒。初时乐趣盎然,久之不免生惰,于是工艺渐渐失传。我曾经尝试制作喀左岩茶,汤色翠绿,明艳胜过龙井碧螺春,但味道苦涩。据说喀左岩茶的制作极为讲究,工序有一丝误差,味道就由清香突变为苦涩。 我每年春节回喀左老家,买几斤红茶备一年之用,价格,十几元到几十元,鲜有百元以上的。问商家茶的进货地,说是云南,具体云南哪里呢,嘻嘻哈哈不说了。不说,我自己去找,云南的朋友听说我喝的茶几十元,极为惊讶:“那不是茶叶,那是树叶!”给我寄来七八种“滇红”,要培养我纯正的滇红口味,可是很遗憾,都不对。可能那些滇红太高尚,已经“大资”了。 刘军来我家做客,我用喀左茶招待他,喝一口,眼睛直了,胖脸蛋子挣得通红,宛如正月十五的红灯笼,嘴巴半天才张开:“阿弥陀佛呀,这么好喝!”紧盯着我的茶叶罐,我准备从罐里倒出一些茶叶给他,他抢过去,倒出一点在桌上,“这么好的茶,必须珍重!”仔细地数茶叶的颗粒:“一五一十, 十五二十, 二 十五三十……” 低调的易县李家包子 在易县一家很小的餐馆,我指挥服务员:这四个菜,一样一份!服务员看看我和李君实,再看看那四样菜,看看菜,看看我,三看两看,我就有点不高兴:“你瞅啥?”她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呢,你们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两个菜合成一份,才好。”六个座的小公交,走街串巷爬山越岭十九公里到后山奶奶庙,每客才五块钱。见满山坡的红柿子,我不由得食指大动,小心问乡民:“我可以摘一个柿子吃吗?”乡民大手一挥:“摘!爱摘多少摘多少,开车没?装!能装多少装多少!” 易县汽车站很小,设施极为简单,车站往西不到一百米,一家包子店,店名“李家特制包子”。古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车站附近三教九流大杂烩,所谓“服务行业”大多不服务专劫财,我一般都避开车站一带的饭店。但这家包子店人头攒动,异乎寻常,去看一看。 店员忙得脚打后脑勺,却能看见我,“几个人?两个人哈,一笼包子,两碗粥是吧?”就这么替我作出决定。稀里哗啦,摆上桌子了。包子确实“特制”,叫作“包子”,却是饺子形状,表面凸凹不平,白灿灿的像是生面。但是,咬一口——眼前金星闪烁,星光中推出无数的光辉形象,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许云峰……同志们哪,你们没吃到这样的包子,怎么就牺牲了呢?张思德同志亲切地说:“我们牺牲,正是为了让你们大家都吃上李家包子啊!”张思德同志转身离去,我才缓过神来,张思德同志在安塞县山中烧炭,出差的机会极少的,身上也没有闲钱,再说他那陕北票子现在也不能用。我应该请他吃一顿李家包子才对。 李家特制包子是灌汤包,汤汁色淡味浓,味觉分层次,先是香,然后鲜,再后醇,各层悠远绵长,如饮上好佳酿,从口腔直达肚腹。春日载阳,温暖身与心。李君实看见还有素包子,要了两个,新鲜菜蔬,宛如菜畦新摘,采苹采绿,青翠欲滴,世上做得好的素包子成千累万,包括功德林全素包,与李家相比,却不在一个时代——李家特制包子完全保留着“大饥荒”之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味道——对,就是这个味道! 一笼哪儿够?再要一笼!两个素包子哪行?再要两个!李君实鲸吞一般,俩包子霎时入喉,抬头看看我:“我把你的也吃了?”一脸的茫然。 香港影星薛家燕偶然来到易县,更偶然来到李家包子店,咬一口包子就掉眼泪,一顿饭吧嗒吧嗒眼泪如珠,放下筷子还不走,忽然在大厅号啕大哭,后来竟打着滚哭,全不顾明星形象——以后吃不到这么好的包子,可怎么办哪!成龙也偶然来到易县,更偶然来到李家包子店,吃完包子就叫店家:“拿笔来!”飘飘洒洒写下一行大字:“天下无包。”成龙的字实在不咋样,可是他名气大啊,李家包子这下该大火啦! 几年后成龙再过易县,想看看李家包子火成什么样子。门面还是那个门面,招牌还是那个招牌,里里外外,“天下无包”难觅踪迹。有点失望,询问店家,店家说:“我不想出名。我不想火,我现在这样就挺好。”成龙忍不住问“为啥呢”,店家说:“我们易县,从古到今,就没有出名的人。”成龙急忙说:“荆轲!”“荆轲是河南人,在易县只是暂住,骆宾王北京人,在这里也是暂住。他们就算半个易县人吧,结果,一个尸骨无存,一个下落不明,荆轲墓只是一座衣冠冢。易县人,不可以出名,出名了一定不祥。” 店家几句话道出大道理。易县低调,低调得令人绝望。易县城关镇有五座古塔,都是辽金时代文物。有五座古塔的县城,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正定县城有三座塔,外地人到正定,就很震撼于它深厚的文化内涵。易县荆轲塔,辽代建筑,八角实心密檐,须弥底座,莲花基盘,饰门束腰,叠涩出檐,整体保存完好,我觉得这座塔应该是文物保护单位,至少是保定市级,但大门、中门都没有一片说明,寻觅很久,才在一个小角落找到“光荣碑”:它果然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竟然是国家级,更是1962年公布的,第一批! 忽然明白,易县后山“奶奶庙”,为什么那么难看,那么土气,那么不成样子,那么叫人连吐槽的力气都没有,那么……原来,那是易县人怕出名,在集体自行污损。 附?记 “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牙,有人写作衙,还作注解说,衙门里头没好人,挨个杀了不冤枉。衙门毕竟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国家机构,是皇权的延伸,不能说衙门人全部该杀。牙,是旧时代一种不很光彩的行业,牙行,除了承担掮客的功能,更多是做贩卖人口的黑心买卖,拐卖人口是重罪,所以该杀。 徐州把子肉 把子肉,百度专家解释说,古人举行公祭之后,把祭祀用的肉切成长方块,分给参祭的众人,由于这种肉块分割时必须扎缚上青蒲草或马蔺草,形成“扎把”的形式,故称“把子肉”。古人公祭的确有肉,公祭的肉的确要分给参加祭祀的人,但是分的肉必须扎成把,却是专家望文生义。分祭肉,是国家大事,得由太宰亲自操刀,一块两块三块,斤两分毫不差,也正因为他分割得准确公平,才当上太宰的,宰,割也,后来称为宰相,还是割肉的意思。再后来叫总理,所谓国家总理,原始意义是红案高级厨师。肉都分完了,还在乎什么把不把?捧着抱着拎着,兴冲冲回家接着祭祀,这回是打牙祭。 把子肉没有这么复杂,说把子肉,一句话的事:拜把子时候吃的肉! 山东好汉秦叔宝,拉帮结派,与当时的好汉四十六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其中从老二到老六都是山东人:秦叔宝、徐世绩、程咬金、单雄信、王君可,还有老十一尤俊达。结拜地点贾家楼也在山东历城,就是现在的济南。古时候人们很难吃上肉,孟子说“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七十岁下的人们,除非年节,平时沾不上荤腥,赶上坏年岁,不免于饿死填沟壑。平白无故地,忽然有人请你吃肉,天哪,是不是要地震!但是,主家说,要吃肉,还有那么一点小条件——什么条件?快说,快说!——结拜为异姓兄弟。——拜,拜,快点拜。你老大,我老二,他老三。拜完了,拿肉来!由于秦叔宝一伙人带头拜把子,山东这地界拜把子蔚然成风,紧跟着供应拜把子的猪肉馆也火起来,店家把猪的五花肉切成三寸长半寸厚的大块,加简单的香料和酱油,急火煮开,文火慢炖,三个时辰出锅,盛在碗里的把子肉,看上去亮晶晶,闻起来香喷喷,夹起来软乎乎,吃下去,香甜软糯。把子肉以香为主调。闻着香,吃着比闻着更香,吃完的回味比吃着尤其香,香得悠长辽远,三个月嘴里都是这道肉的滋味。山东人叫它“把子肉”,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当代。 我在山东济南,就职的部门没有食堂,我每天流连市井,“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就发现了这山东把子肉,结果一吃定情,终生不渝,看见把子肉就挪不动脚步,一顿接着一顿,吃遍济南。把子肉虽然好,也有一点小缺点:能把人吃得肥胖,不出半年,我就愉快地迈入大胖子的行列。 二十年后,我再来济南,土狼扑食先找把子肉,出租车司机很是不屑:“把子肉?谁吃那玩意儿!”把子肉式微,是他们每天都可以吃肉,吃肉和拜把子失去了必然联系,也就是不必拜把子才能吃肉啦!于是拜把子活动锐减,把子肉饭馆也跟着萧条,我跑遍济南,把子肉实在难找,而且,味道也大都不如从前,其中鲁能酒店旁边小胡同里有两家把子肉饭铺,卖的把子肉算是差强人意。 山东开门就是江苏,迈步就到徐州,在徐州高皇帝羊肉馆,一个本地汉对同桌的客人科普徐州美食,犹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想当年,汉高帝刘邦与项王决战,韩信、彭越、英布三支军队,在九里山摆下战场,项王战败南奔,高皇帝在徐州大宴群臣,这座羊肉馆,就是高皇帝当年开宴会的地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咱徐州最精彩的菜品是什么。”“一定是高皇羊肉。”“不不,羊肉哪都有,徐州美食一定是外地没有的东西。”“那啥?”“对对,就是那sha汤!”“啥汤?”“是啊,sha汤!”“啥汤,你倒是说呀!”我听得着急,对那个客人说:“sha汤,不是啥汤,那个字,字典里没有,电脑字库里也没有,食字旁,右边一个它字,读如‘啥’,也借读做‘蛇’。”“冷子兴”以徐州美食行家自居,没想到半路跳出一个我,对我不免冷面相向,冷语相加:“来了一位大明白。你听他说吧,我还有事。”悻悻而去。 这位徐州人说得不对,sha汤是饮品,不是菜品,临沂写作“糁汤”,音sa,也有历史了,孔子在陈蔡挨饿,“藜羹不糁十日”,就是连糁汤都没得喝。五省通衢的徐州,菜品当然要有五省的范儿,起范最帅的,冠军就是徐州把子肉。把子肉在山东静悄悄了,在江苏徐州却大火,这是因为徐州人务实,他们喜欢把子肉的味道,不管是不是拜把子时候才可以吃,秦叔宝程咬金,与我面前这碗把子肉有关系吗?既然没有,我吃肉,他们拜把子,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徐州把子肉的制作,与山东的做法一致,但是更精致,一定选猪的肋五花肉,其他部位的五花肉或者软,或者硬,都不如肋五花富于弹性的柔软。也许是水土的关系,徐州把子肉更讲究入味,肉的香味从里向外扩展、释放,先入唇,过齿,到舌,然后是牙,再到喉,各层次鲜明,但又浑然成一体,不是一个“香”所能了得,比如齿的香是心里感觉,牙的香却是肌理,因为牙根深深嵌入,与髓相通,形成骨髓记忆,这种记忆将伴随他的终生。古人说“齿牙留香”,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吃过徐州把子肉。 把子肉是徐州城的主打菜,全城有一百多家把子肉菜馆,任何一家肉馆,都有一大盆油亮软糯的把子肉含情脉脉向客人招手,一片分明在说:“你可来了!”另一片跃跃欲试:“我等了好久。”一碗大米捞饭,盖上这两片亲亲热热的把子肉,再浇上一两勺子同样亲亲热热的肉汤,这碗饭,给一个当朝宰相都不换! 我从徐州回到北京,带来一盒把子肉,盒子保温,到北京,还温热如刚出锅,把子肉上桌,香气弥漫整座饭店,吃饭的跑堂的甚至做饭的大师傅都尖起鼻子寻找香气的来源,我的同事却不给他们更多享受的机会,三下五除二,一盒把子肉霎时见底。最后一片,我急忙护住:“大家别吃了,给郭图嘉留下。”郭图嘉不吃红肉,牛羊猪骆驼马的肉,都不吃,她说,吃草的动物牛羊肉膻,吃粮的动物猫狗肉臊,吃水草的鱼类肉腥,猪杂食,啥都吃,所以它的肉腥臊恶臭。她自己不吃红肉,看见别人吃红肉,她的眼睛里都闪着仇恨的光。今天大家在她面前大吹大擂把子肉,竟然把她当空气,而且,那肉的香味实在太诱人……试试探探地用筷子夹起那幸存的把子肉,尚未沾唇,目光的愤怒色彩消失大半,牙舌齿次第检阅,目光变得柔和灿烂,如三月艳阳,我非常担心她的脸上会像领袖一样闪烁起红色的光辉。忽然,大颗的眼泪顺着郭图嘉面颊流下,说话的音声带着几分懊恼:“他们骗我!” 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告诉郭图嘉:“吃草的动物牛羊肉膻,吃粮的动物猫狗肉腥,猪杂食……” 以鲁迅先生杂文集的名字、行文风格贯穿全书,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仿照鲁迅笔法,描摹时下社会百态,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对山川民俗中华文化的精准记述……生动恣意,才思横溢。作者丰厚的学术功底为本书增添了引人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