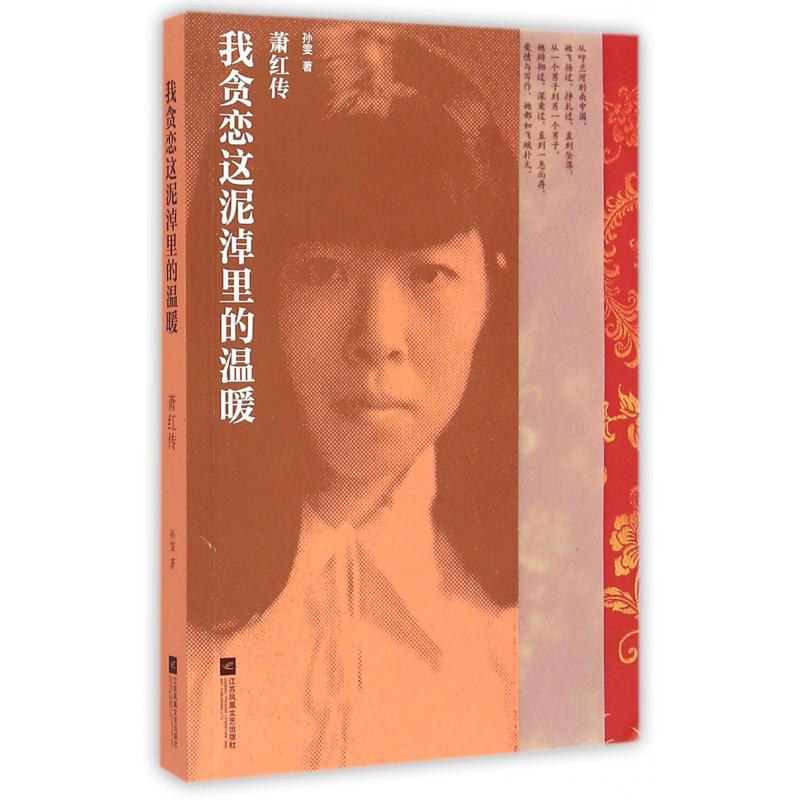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34.00
折扣价: 20.74
折扣购买: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ISBN: 9787539979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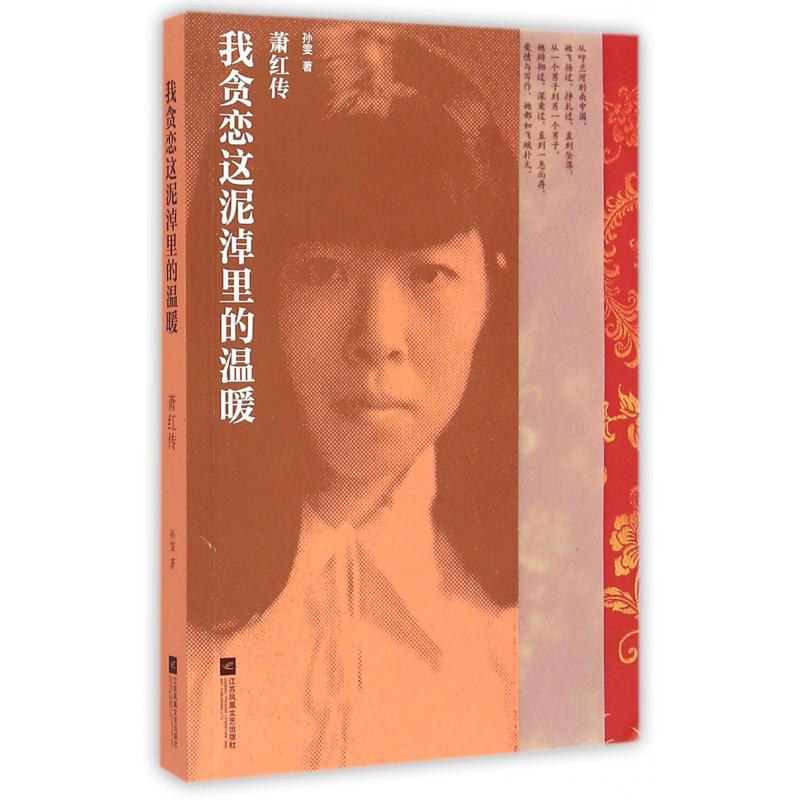
孙雯,生于山东,居在杭州。 媒体人。每日码字,次日过期。不说也罢。所幸,可以表达,可以暗藏一点小小的忧喜与企怀。
1928年冬天,呼兰小城照旧被大雪覆盖。 雪一层一层堆覆,夹杂了烟囱里飘落的灰烬和世 俗的气息,那原来的白,慢慢地,也就灰了。 酷冷的边地小城,街面上几乎没有行人,好动的 孩子,也缩首埋进白雪后的堂屋。偶有卖馒头的老人 走过,后脚掌缀满冰雪,步履维艰。 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却异常热闹。 十七岁的萧红订婚了。 这一婚约,自然是父亲做主,保媒的是六叔张廷 献。父亲为离家一年的萧红找来另外一条绳索,那就 是婚姻。 所幸,那个叫汪恩甲的男子,看上去还算顺眼。 他家住哈尔滨顾乡屯,其时,已从吉林省省立第三师 范学校毕业,在哈尔滨道外区基督教会创立的三育小 学任教。 说起来,这桩婚事也是在两家知根知底的情况下 确定的。 六叔张廷献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当年在吉林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二 人都在哈尔滨任职,交往甚密。而且,汪大澄在张廷 献处见过萧红,这个沉静的女子,看上去端庄有礼, 他也颇为满意。 对于订婚一事,萧红并未表现出极力的反对。且 不管她在离家的当年,是否早已同意了这门婚事,若 是只看眼前,这位汪公子总算识得诗书,也相貌堂堂 。 订婚后,萧红与汪恩甲往来较为密切,除见面外 ,也常有通信交流。据说,萧红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 以表爱意。这段婚事,并无萧红想象的那般无趣,也 并无世人想象的那般充满了父权的压制。 十几岁的女孩子,虽说叛逆,但对生活总是充满 新奇。再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虽 然不允许女学生随便与男性来往,但是,如果男方确 系女生未婚夫,则网开一面。所以,校园里,不乏的 是成双入对。订婚,亦是满足了小女子那不能说出的 虚荣。 若是萧红就此收敛起叛逆的脾气,生活就此平顺 ,她与汪恩甲或许能做一对终老夫妻。 然而,对于萧红而言,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 立第一女子中学”所给予的开放思潮与新式生活,远 比眼前这个还看得上眼的男子更有魅力。因而,少女 心思,哪能就此牵系于一人之身。 学校坐落于一处环境优雅的俄式住宅群中,老师 们思想前卫,可读的书多了起来,她也开始尝试写作 ,并将那些小文发表于校刊,而且,她还有人生中的 第一个笔名——悄吟,即为“悄悄地吟咏”。 在课外时间,萧红得以时常去野外写生,这所学 校给了她一个对于绘画终生的梦想。 订婚时,萧红正在度寒假。假期未结束,祖父已 经病重。 年初,萧红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而八十岁的 祖父,却一天天变了模样。 祖父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给予萧红温暖的男人。相 比父亲给予的禁锢,祖父给了萧红一片开放自由的世 界——那不仅仅是后花园里的花红柳绿,还有《千家 诗》里的执着、浪漫,与一切的爱与失离。 “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这是祖父留给萧红永生难忘的絮叨,绵软,却是 有力的。 因为祖父,萧红对世界仅存的温暖与爱,怀着永 久的憧憬和追求。同样因为祖父,在离家的经年岁月 ,她笔下描摹的始终是呼兰这片土地。 夏天了,祖父却不能如草木一样,在炙热的阳光 下撑起绿阴。他终究还是没有撑住。 六月初,萧红在学校得知祖父病故的消息。匆忙 赶回,还未踏入家门,便见白色幡杆高挂,空气里鼓 噪着鼓手吹奏出的哀号。祖父安静地躺在床上,手是 冰凉的。后花园一个童年的欢笑,从此,让他带走了 。 祖父下葬的那天,后院的一树玫瑰正开得艳丽招 摇。那花有多艳丽,萧红的心就有多凄绝。往年的六 月,祖父蹲在菜地里拔草,萧红时常将红彤彤的玫瑰 在祖父的帽檐上插满一圈,祖父并未察觉-只是会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 里路外也怕闻得到的。只有那时,祖母与父母都能开 怀大笑,而萧红可以笑得在炕上打着滚。 就在三个月前,家里还大摆宴席,为祖父庆祝八 十大寿。此时的父亲,已经是呼兰的教育局长。宴席 上来了不少头面人物,他们撑起了父亲的面子。而对 于祖父而言,这如同一场喧闹的回光返照,并未挽留 他已然走向颓弱的生命。 1928年6月4曰,由北京返回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 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迫使张 学良签订了《满蒙新五路》条约,激起东北各界抗议 。 11月,哈尔滨的学生走上街头,为衰弱的民族呐 喊。萧红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她在散文《一条铁路的 完成》中记叙了这个故事。 一场游行,如同一个仪式,将个体的命运与时代 的风潮合二为一。 热血与激情,一直隐匿于年轻人的身后,危亡关 头,这些年轻的男女总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呐喊 出历史的呼啸。 祖父离去,让萧红失去了在家庭中最后的庇护和 精神支撑。仅剩下“冰冷和憎恶”。奔丧回来,她小 心翼翼地收拾好旧忆,偶尔在内心痛哭一场,白日里 ,掩盖着伤痕,照旧生活。 如同萧红一样,东特女一中不少女学生有未婚夫 ,那些男子基本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读书 。似乎,只有这样,他们看起来才更像比肩的一对儿 。不知是为了迎合这样的风气,抑或是其他的原因, 不久,已在三育小学执教的汪恩甲,也进入法政大学 读夜校。 然而,这样的刻意,并没有让两人的情感更为牢 靠。 多数时间,萧红与汪恩甲,她读她的书,他教他 的学。少女的芳心,当然不会因为一个与她订了婚的 男子而收起探索世界的触角。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