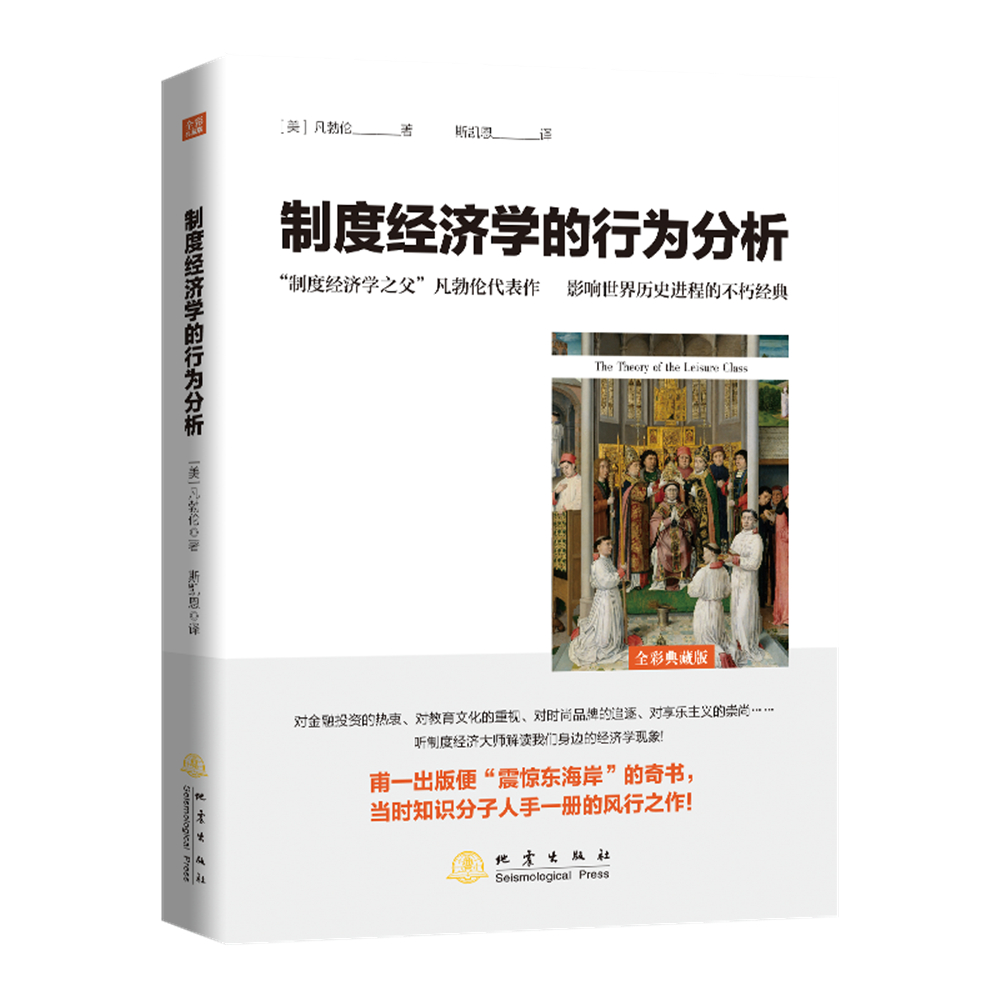
出版社: 地震
原售价: 80.00
折扣价: 48.00
折扣购买: 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分析
ISBN: 9787502852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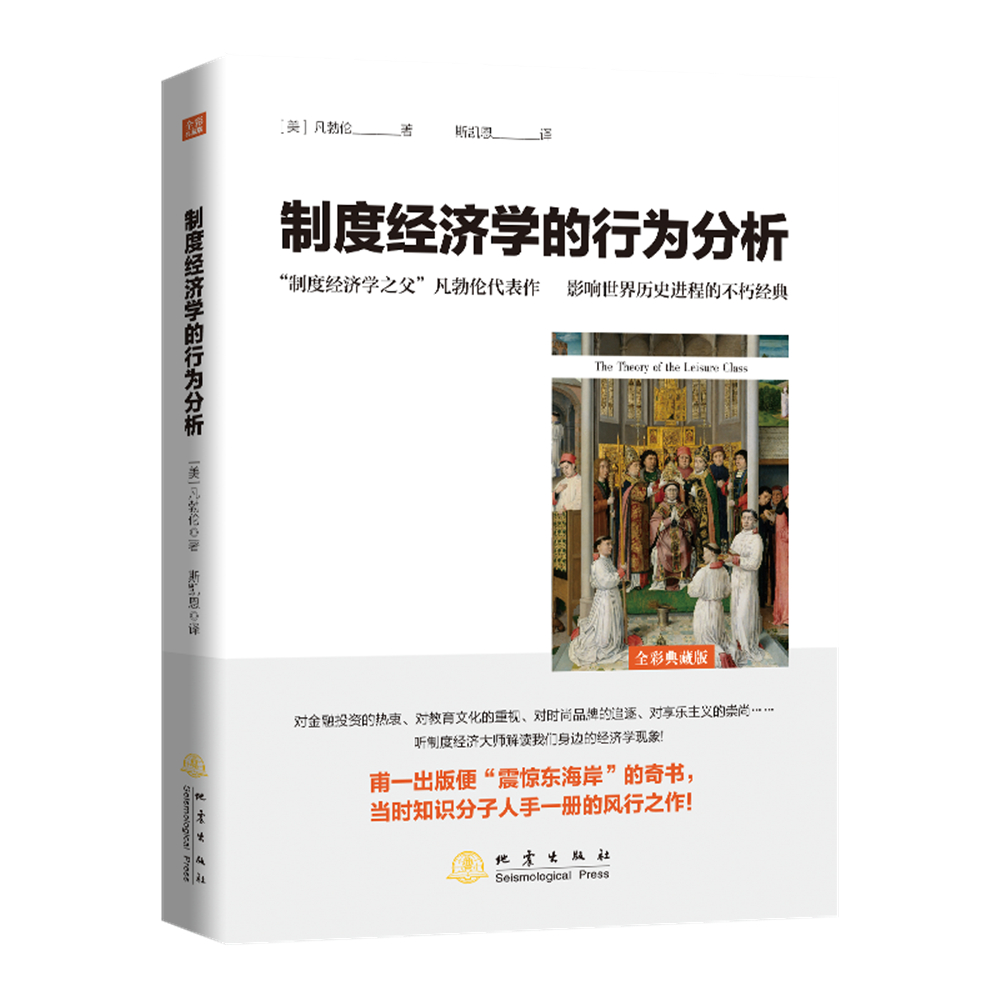
凡勃伦(1857—1929),美国20世纪初期zui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制度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拓展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具体地说,他阐述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正是由于上述成果,凡勃伦成为“制度经济学派的智慧之父”。 斯凯恩,男,生于20世纪70年代,拥有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是资深的金融圈人士,也是多家财经媒体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其作品《从零开始读懂金融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长期位居京东、当当等各大网上书城金融与投资类排行榜TOP50。
第七章 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解释了不断变换的时尚式样后,我们要用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来印证这一解释。众所周知,某一时期流行的式样是人人喜爱的。当一个新式样出现时,总会博得人们一时的喜爱,至少当它还没有丧失作为一个新奇事物的资格时,人们通常会觉得新式样是漂亮的。流行的式样总是动人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新式样与旧式样有所不同时会产生一种轻松感,部分原因是流行的式样包含荣誉性。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我们的爱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荣誉准则的控制,因此,在荣誉准则的指导下,任何事物在其新奇性尚未消失之前,或在其荣誉性转移到适应同样目的的其他新奇结构上之前,这些事物在人们看来都是适当的、可以接受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流行式样中所感受到的美或“可爱”,都只是暂时的、虚幻的,由此看来,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式样,没有一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是当时最精美的新式样,过了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尽管不会不堪入目,也会令我们感到大吃一惊,觉得古怪可笑。我们对于任何新鲜事物的一时爱慕,并不是以审美观念为依据,而是受了其他原则的影响。一旦我们原有的审美感重占上风,对这个新设计感到难以接受,它就要寿终正寝了。 审美上的厌恶感,其发展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时间的长短由某一特定情况下的某一新式样的内在丑陋程度决定。依据新式样的可厌性和不稳定性,可以对这种时间关系做如下论断:新式样代替旧式样的速度越快,这种新式样与正常审美的抵触就越大。由此可以推断,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富有阶级,在富裕程度、流动性、人际交往方面发展的程度越高,明显浪费在服装上的强制性就越大,审美观念会更易于陷入停滞状态,更加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抑制。这时,时尚的变换会更快,相继出现的新式样也越来越怪诞奇异,令人难以忍受。 关于这里提出的服装理论,至少还有一点有待研究。上文所述普遍适用于大部分的男子和妇女的服装,在现代社会,虽然上述各点似乎在妇女服装方面更加适用,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妇女服装的情况与男子服装完全不同,妇女服装具有一个格外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可以证明其穿着者并不从事也不宜从事任何粗俗的生产工作。妇女服装的这一特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使服装理论更加完善,而且印证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过去和现在的妇女的经济地位。 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有关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问题的论述中谈到。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主人执行代理消费已逐渐成为妇女的职责,妇女的服装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设计的。于是这样的结果出现了:明显的生产劳动对贵妇的身份是一种特别的损害,因此在妇女服装的设计中必须尽力使旁观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假象),即这种衣服的穿着者不习惯也不可能习惯从事实用性的工作。按照礼俗的要求,有身份的妇女应当始终摒弃生产劳动,表现出比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男子更加彻底的有闲。如果我们看到一位出身高贵、有良好教养的女子被迫从事实用性工作,总不免愤愤不平,因为这不是“妇女分内的事”。妇女的活动范围在家庭内,她应当在家里发挥“美化作用”,成为家里的“明星”,男主人一般不会被说成是家里的“明星”。这一特点,加上礼俗要求妇女始终注意衣着和其他饰品上的奢华炫耀这一事实,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上文指出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制度继承自过去的族长制,于是证明家庭的支付能力成为妇女的一项特殊职能。依照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的荣誉应当是妇女特别注意的事情,而这种荣誉主要通过荣誉消费和明显有闲来证实,因此,如何进行荣誉性消费并表现出明显有闲就被列入了妇女的活动范围。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往往在高等金钱阶级的生活中才能实现—关注物质与劳动力的明显浪费,通常成为妇女唯一的经济职能。 当社会还处在妇女是完全意义上男子的财产的经济发展阶段时,明显有闲和明显浪费是她们必须执行的一部分任务。那个时候的妇女没有自主地位,由她们执行的明显有闲和明显浪费,其荣誉自然不属于她们而属于她们的主人。因此,家庭中的妇女越是奢侈浪费,越是明显地不从事生产活动,就越能达到增进其家庭或家长荣誉的目的,也越值得称道。这一情况愈演愈烈,以致妇女不仅要在证明有闲生活方面有所贡献,还要使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实用性活动。 基于这一点,男子服饰的发展无法赶上妇女服饰的发展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明显浪费和明显有闲是金钱力量的证明,因此具有荣誉性,但归根结底,因为金钱力量是优势力量的证明,所以它才是荣誉性的、光荣的。因此,任何人,当他为自身利益而做出浪费或有闲的证明时,如果不能采取这样的形式或趋于这样的程度,就会使自己显得无能或明显处于不舒适、不自如的状态。这种情况所表明的不是优势力量而是劣势地位,这样做会破坏其自身的目的,从而作茧自缚。因此不管在哪里,只要浪费性支出和免于劳动的表现,在正常情况下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表现出明显不舒适的状态或自然导致的体弱无能,就可以断定,此人进行这种浪费性支出,忍受体力上的无能,并不是为了自己在金钱荣誉上的利益,而是为了她在经济关系上所依赖的另一个人的利益。从经济理论上来看,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奴役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试着将这一结果应用到妇女的服装方面进行具体说明。那些高跟鞋、长裙、紧身胸衣、不切实用的女帽以及不顾及穿戴者舒适感的一切现象,都是文明妇女服装的显著特征。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从理论上来说,妇女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依赖男子的地位,从高度理想化的意义上可以说,妇女依然是男子的动产。妇女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明显有闲,穿着那些衣服,实际上是由她们的奴役地位决定的,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她们被赋予了证明其主人所具有的支付能力的任务。在这些方面,妇女的服装与家庭仆役,特别是着装侍从的服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两者同样费尽心机地表现出不必要的奢华,同样有明显不顾及穿着者身体舒适的倾向。不过,即使主妇的服装不一定要显出穿着者的羸弱之躯,也至少要蓄意衬托出穿着者的娇惰闲逸,这一点是仆役的服装望尘莫及的。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按照金钱文化的理想方式,主妇是家庭中的首要奴仆。 除了这类仆役之外,至少还有一类人,他们的服装与仆役阶级的服装相似,而且具有妇女服装表现女性气质的类似特点。那就是教士阶级。教士的法衣有力地、突出地显示了奴仆身份与代理生活的所有特征。法衣看上去精美华丽、光怪陆离,而且穿着非常不方便,至少在表面看来非常不舒服,简直可以达到痛苦的程度,这一点比教士的日常服装表现得更为突出。按理说,教士是要摒弃一切生产劳动的,他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示出冷静、沉闷的表情,这与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仆役的神色很相似。此外,教士的面颊应当修得十分光亮,家庭仆役也是如此。教士阶级之所以会在态度、装束上与仆役阶级极为相似,是因为这两个阶级具有相似的经济职能。从经济理论上来说,教士也处于随身侍从的地位,他是神的随身侍从,穿着神赐予他的制服。他的制服理所当然是非常华贵的,这样才能恰当地显出其崇高的主人的尊严。但在服装的设计上,这种制服则很少顾及或者说完全不顾及穿着者身体上的舒适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穿着制服是一项代理性消费,这种消费增进的是那位不在场的主人的荣誉,而不是仆人自己的荣誉。 男子的服装与妇女、教士、仆役的服装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但实际上这条分界线并没有被始终如一地遵守。这条分界线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习惯中,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放纵随意的人,而且这类人不在少数,他们狂热地追求服装上的荣誉,超越服装上的男女分界线,甚至把自己装扮得不像人类,但所有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男子这样打扮是脱离常规的。我们习惯于说那类男人的装束“有女人气”,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批评—某位先生衣着考究,但看上去如同一个穿着体面的跟班。 ?有钱人为什么要炫富?为什么商品价格越高越想购买?“凡勃伦效应”至今仍在影响世界! ?“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凡勃伦里程碑式著作,将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消费”上来! ?人们追名逐利背后所隐含的动机为何?其与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凡勃仑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入解析现代生活中的经济谜题! ?20世纪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用辛辣的文字讽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用进化论思想研究现代经济生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离经叛道者”! ?四色全彩插图,优质纯质纸印刷,经典重译,可读可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