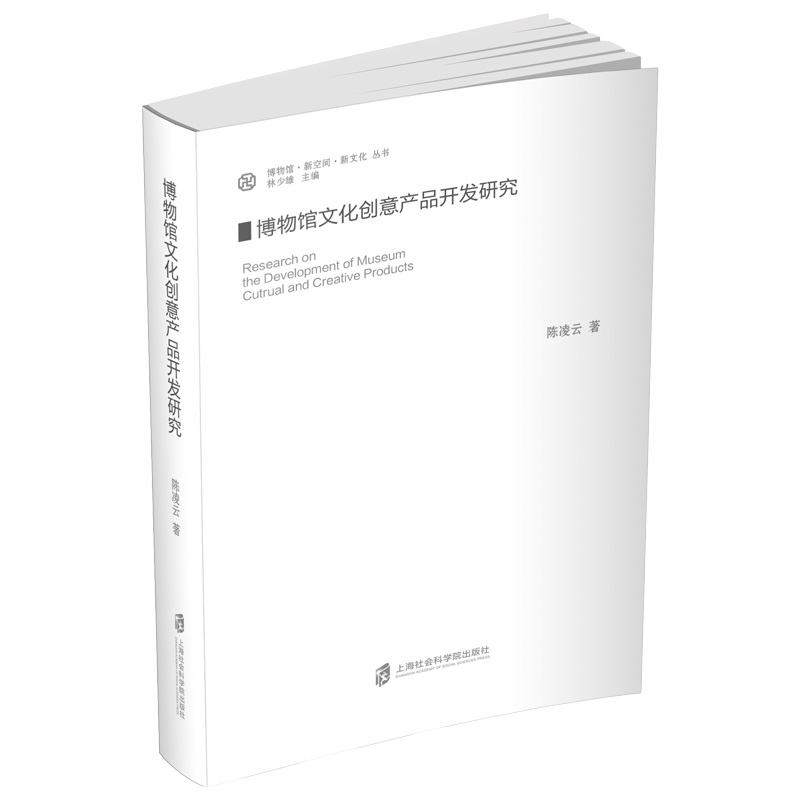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9.80
折扣购买: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研究/博物馆新空间新文化丛书
ISBN: 9787552027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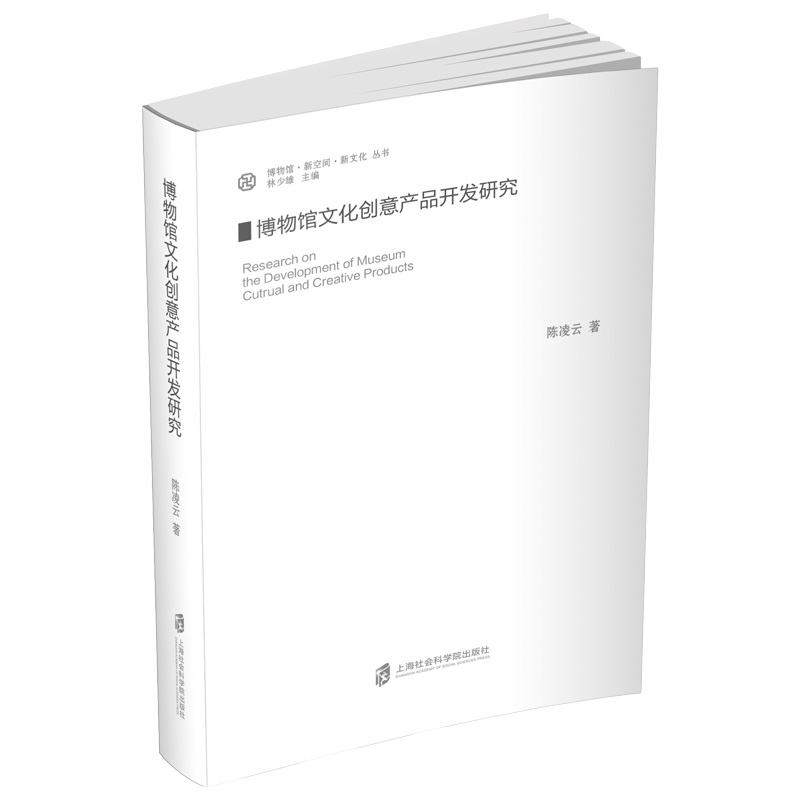
陈凌云,1983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助理,复旦大学史学学士、硕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博物馆学、艺术学理论。自2003年至今,在《文汇报》《文化产业研究》《上海文化》等报刊发表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博物馆管理、艺术学理论、文化经济学的论文与文章20余篇,并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项目。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选题缘起 自17世纪诞生至今,现代博物馆的定位、性质、使命和功能几经更迭英国牛津大学阿西莫林博物馆被公认为是第一座对外开放的现代博物馆,详见[美] 休·吉诺韦斯、玛丽·安妮·安德列编: 《博物馆起源》,路旦俊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8—11页。,从传统意义上的文物收藏展览场所和曾经的民族国家权威教化工具,演变为以教育服务大众为根本旨归的公共文化机构和大型城市的主要文化地标,在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20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及随之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创意经济,则给博物馆创新管理模式、增强文化传播力、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新契机。 无论是为了建立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以维持日常运营和扩充收藏等显而易见的利益,还是出于树立博物馆品牌形象进而突显地区文化特色等潜在动机,大多数博物馆均已无法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之外,纷纷以其独具的文化资源禀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获取经济收入和社会效益。欧美等国博物馆因政府拨款有限,社会基金赞助亦无法满足所有运营需求,故而在创建早期即致力于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以谋求拓宽资金渠道,在文化创意领域先行一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部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博物馆亦在创意产品开发上多有开拓。 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一直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两翼,并且,政府和学界普遍认为前者属于公益性文化设施的主要职能,后者是经营性文化企业的主营业务。因此,有别于欧美国家,我国内地博物馆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探索从事产业化经营活动,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定位使其一直“耻于谈利”,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外部政策环境、内部体制机制和从业人员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和制约,进展相当缓慢。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原本判若有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呈现出融合的态势,博物馆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就是两者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4873家,其中4246家向社会免费开放,占比高达87%;近年来平均每年举办展览3万多次,年均参观人数约9亿人次数据来源: 《国家文物局: 我国博物馆每年接待约9亿人次参观者》,新华网2017年5月19日。。博物馆免费开放在促进全民共享文化福祉的同时,也给博物馆自身运营带来了重重压力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内地博物馆借鉴国际知名博物馆的运营经验和筹资模式,在坚持公益性文化机构定位和功能的前提下,以丰富的馆藏文化资源为基础,研发、销售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品,无疑是树立自身品牌形象,增加经营性收入的关键途径。 2015年以来,《博物馆条例》《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旨在推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密集出台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已经发布了八项关于促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政策,详见附表3。,为我国内地博物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法律保障,指明了发展路径。近两年来,我国各地博物馆提取、应用馆藏文物创意元素设计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众视野,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了一定的话题热度。在国家政策支持与社会民众的鼓励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内地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和产业经营的整体水平还不高,面临多重发展瓶颈。博物馆内部环境方面,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设计的思路和理念不够清晰,同质化现象严重,提取文化元素流于表象,时尚性、创新性不足,后续市场反馈和评价机制尚未形成;外部环境方面,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管理和激励机制落后,资金投入和扶持政策不足,艺术授权和营销推广模式尚未完善。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亟须研究破解。 作为博物馆界和文化产业界前沿领域,目前国内对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基本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尚属薄弱,对策应用性探讨偏于简单笼统,呈现出明显的理论研究滞后于产业实践的状况。本研究试图借鉴运用博物馆管理学、文化经济学和艺术创意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如何打通从文物内涵解读、素材提取、转化、重构和再造,到投入生产应用并服务大众生活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发挥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示范效应,促进传统历史文化艺术与现代创意设计结合等问题。 二、 研究意义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工匠精神,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同时,根据党对下一阶段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部署,应着力于深化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文化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传统文化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是推动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博物馆建设及其展现的文化风貌是提升国家和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发展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一是呼应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的整体文化文物工作战略;二是有助于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消费需求,融合文化产业与新兴技术,构建高端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吸纳多元社会创意主体参与文化创意产业;三是弘扬工匠精神,发掘文物中蕴含的优秀传统工艺技术,为中国艺术创意设计领域实现整体观念转型升级提供思路。 1. 理论价值 本研究将深化对博物馆营销、博物馆教育等博物馆学核心理论的认识。广义上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包括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教育阐释、经营管理、营销推广等学科分支,随着现代博物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型,博物馆教育和博物馆营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既是博物馆有效筹集资金,实现永续经营的手段,更是其教育传播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延伸。因此,本研究将拓宽博物馆学既有的研究视野,深化学界对于博物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教育和营销功能的认识。 本研究将对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创意经济学理论形成有益补充。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目前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等市场化主体的产业实践,多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加以阐释。本研究尝试探讨博物馆这一非营利机构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规律和动力机制,将对既有的创意经济学理论形成有益补充。 本研究将对完善艺术创意学理论和提升中国本土艺术创意设计应用能力提供思考。18世纪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某种程度上是艺术的“赋魅”过程,艺术和宗教功能相联结,艺术品由寻常之物嬗变为膜拜对象。20世纪以来出现反转,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经历了“祛魅”过程,引入“艺术界”概念,更为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艺术,艺术品重新回归为可亲近、可把玩、可使用,亦可欣赏的日常物品。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作为“日常审美泛化”下的艺术品,对其有别于普通商品的特殊价值取向和研发规律的探究,将对现有的艺术学理论提供案例思考。21世纪特别是2015年以来,伴随着“文化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艺术领域的“中国风格”盛行于国际舞台,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国际视野接轨,提升中国本土艺术的创新设计能力以及国人的整体审美素质,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本研究亦可从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设计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面向。 2. 应用价值 本研究将针对我国博物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症结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对策建议。目前在我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前端、中端、后端等环节上,博物馆、企业、设计师、公众、政府、消费环境等各个参与要素彼此影响,存在大量制约产业健全发展的难点与障碍。本研究拟对这些问题成因和症结所在进行深入剖析,并从提升研发设计水平、畅通销售传播渠道、加强平台支撑体系、构建高效发展模式、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等角度提出参考建议。 本研究将为破解我国博物馆研发文化创意产品中面临的各种发展瓶颈提供案例参考和模式借鉴。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博物馆在数十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和理论积淀进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理论研究框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案例的分析和比较,演绎、归纳和总结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价值特征和研发规律,结合对具体国情与博物馆情况的分析,构建适合我国内地不同类型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对我国博物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借鉴。 本书运用艺术营销学、艺术创意学和博物馆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案例调研为基础,分析作为非营利性公益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如何定位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资本理论和教育传播学视域下如何界定“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概念内涵和价值构成,阐释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关键战略环节和主要发展模式,剖析目前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在研发设计环节和市场营销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如何从整体上突破我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面临的瓶颈,进行完整高效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