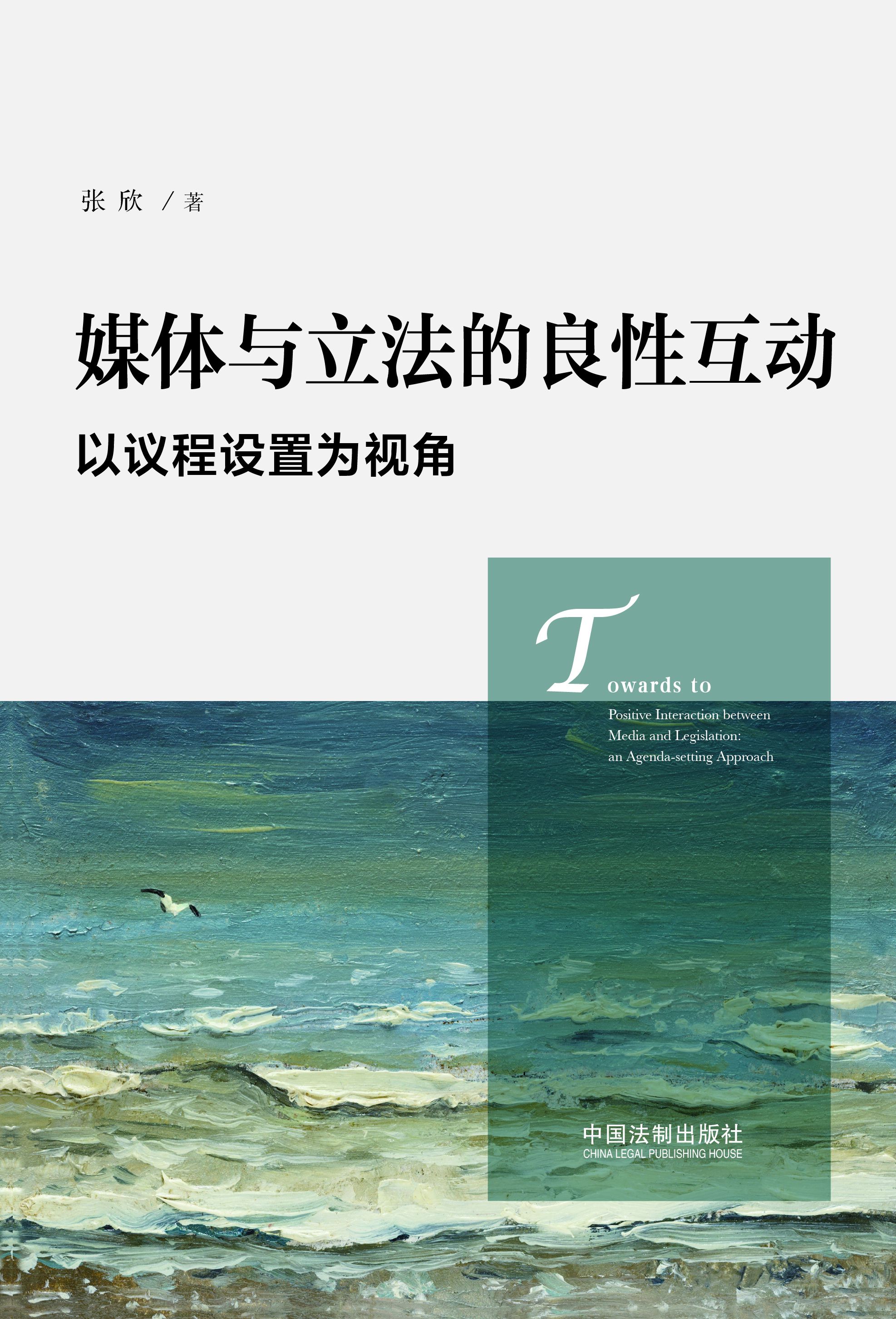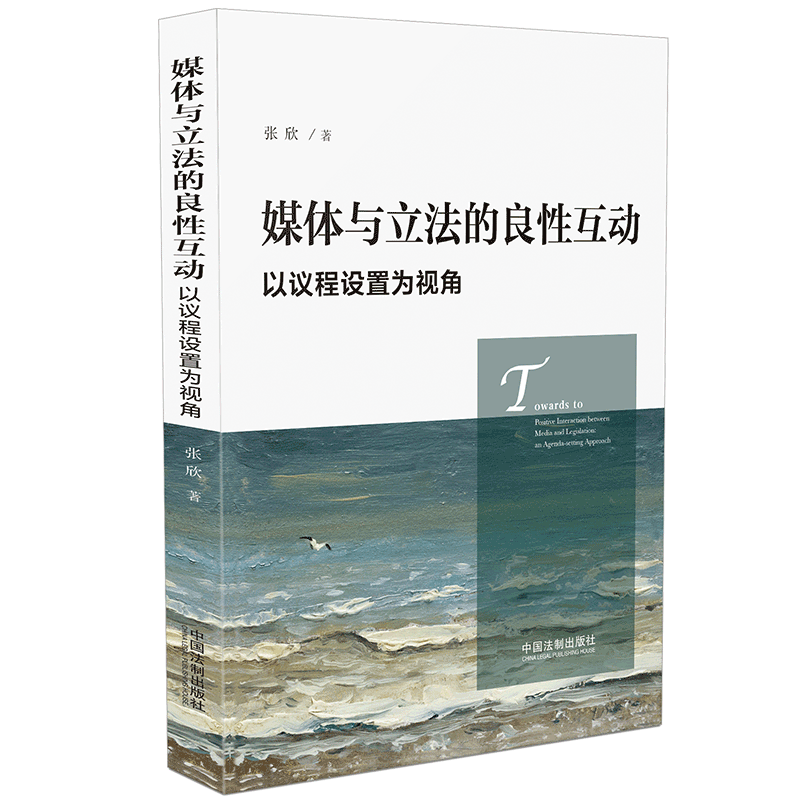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法制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53.25
折扣购买: 媒体与立法的良性互动(以议程设置为视角)
ISBN: 9787509392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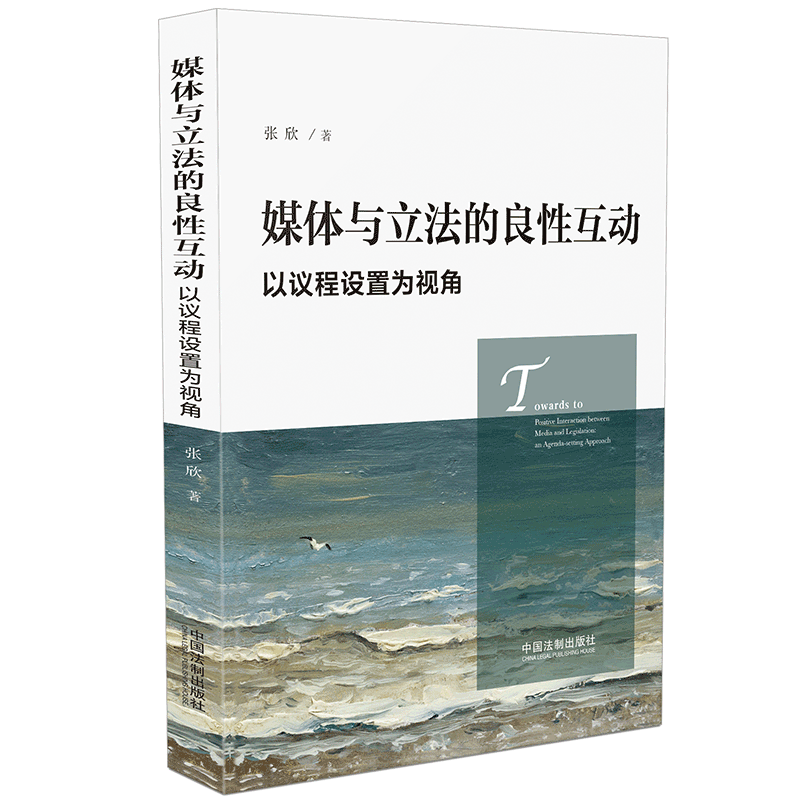
张欣 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和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科(法学、经济学双学位)、博士(硕博连读)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法、立法学、法律社会学。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曾在《法商研究》、《法学评论》、《环球法律评论》、《中国法律评论》等多家法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兼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亚洲法律协会ASLI Fellow。曾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一等奖、第十二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二等奖等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曾应邀于荷兰、意大利、美国、新加坡、墨西哥等地进行英文学术报告。
第一章导言第一章导言 法律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法律制度的供给和需求恰是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规范与社会变革衔接和互动的两个触点,是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面临信息获取不完全的刚性制约。当法律制度需求主体利益集中、聚合时,政府主导型的制度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制度信息获取的不足,因而体现出较好的回应性和效率性特征。随着法律制度需求主体呈现分层化、多元化的趋势,当缺乏正式、有效的制度需求传递机制时,政府主导型的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因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无法及时获取法律制度需求,逐渐呈现出被动回应型和滞后型特征,并与社会需求呈现出日益显著的脱离化趋势。当正式的制度需求传递渠道缺失时,制度需求的客观存在会促使一系列非正式化的制度需求传递渠道逐渐形成,并推动法律制度变迁的集体一致行动。 就我国而言,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具有“去分层化”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1.特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具有立法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性,能够满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构中国法律制度基本格局的客观需要。但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分层的日益复杂化,不同阶层主体逐渐呈现出利益多元化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政府主导型的法律制度供给模式难以帮助立法者全面探知各阶层主体的制度需求。因此,当一部分社会主体的制度需求被长期忽略,且无法有效地对立法议程产生影响时,立法需求和立法供给间的矛盾会逐渐聚合、加深。在这一背景下,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立法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图景。张欣:《美国行政规则制定请愿制度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随着网络技术裂变式的发展,我国媒体格局经历深刻调整,舆论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媒体不仅负责宣传、报道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负责动员群众和响应改革的号召,还为政府撰写内部信息收集报告,受理民众的诉求,帮助民众寻求正义的实现。Benjamin L Liebman,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5, 2005, pp1-157.伴随着中国媒体商业化的进程和媒体采编裁量空间的逐步扩展,公众对社会和法律问题的关注使得媒体具有强烈的激励来扩展其传统角色。因此,出现了以批判、曝光等方式深入报道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新闻,并试图影响公民纠纷处理结果的趋势和现象。Benjamin L Liebman,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5, 2005, pp1-157.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自治化的提升打破了传统媒体报道的地域限制和功能限定,为公众提供话语权的同时还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和相互沟通的平台。谢新洲: 《舆论引擎:网络事件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因此,中国媒体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法治领域活跃的参与者。继介入法律宣传、监督司法公正后,媒体通过充当公众参与立法议程的商谈平台,“已经或正在通过受众实质性地介入立法活动中”周雪:《论媒体对立法的促进作用——以若干公众关注案件为例》,载《人大研究》2012年第8期。,成了互联网时代立法决策的新型重要约束。 从政策议程设定的视角出发,本书主要围绕影响立法创制、修改和废止活动的议程创建阶段对媒体和立法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本书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媒体报道和舆论渗透影响下的立法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论证,以此作为探求我国法律制度供给和社会制度需求衔接规律的切入点,为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达致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主体的立法能力建设,以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理论支持。李林:《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加强立法能力建设》,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8期。本章拟从主要研究对象所在的时代背景入手,对研究源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本研究力求带来的理论创新进行系统论述。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1〗一、研究源起作为后发国家,与西方法律体系自发且漫长的演变道路截然不同,确定法治发展道路的中国为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开始加快立法步伐,选择了一条具有计划性和立法者主导的法律体系形成道路。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因此,在经历权力本位主义、人治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立法万能主义谢晖、陈金钊主编:《立法:理想与变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等立法阶段后,从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立法机关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近200年才构建的立法规模。2011年3月1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宣布这一阶段性立法目标的完成。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实现。杨景宇:《中国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载《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我国立法工作获得重要阶段性成就,从法律制度的整体格局和框架上形成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相协调的法律制度规模。而阶段性目标的形成则意味着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立法工作重点需要逐渐转化为对法律制度结构和内容上的精细化修改和完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2)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立法重点主要放在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上。其主要包括: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更加注重法律体系的科学和统一,开展立法后评估试点工作。同时,该报告还着重强调:“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201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要将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放到推动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修改上,同时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法律体系动态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现阶段深化改革时期对立法所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立法工作中对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提高立法质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都有对“科学立法”的明确说明。的要求进入新阶段。李林:《当前我国立法的新要求》,载《北京日报》2017年9月4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种新形势,面临着各种新任务。如何让立法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引领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以保障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成了我国改革新时期的立法重任。李林:《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加强立法能力建设》,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8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立法与改革要齐头并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目标,描绘了法治的力量和可期的美好未来。这一系列信息预示着新时期的改革大业中,立法活动应当担以重任、因时而宜,并树立自身的精神向度和新改革时代的精神品格。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时代背景下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信成了所有法学尤其是立法学研究者致力于理论贡献的阵地。 围绕媒体与立法的良性互动展开细致讨论,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的变迁脉络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