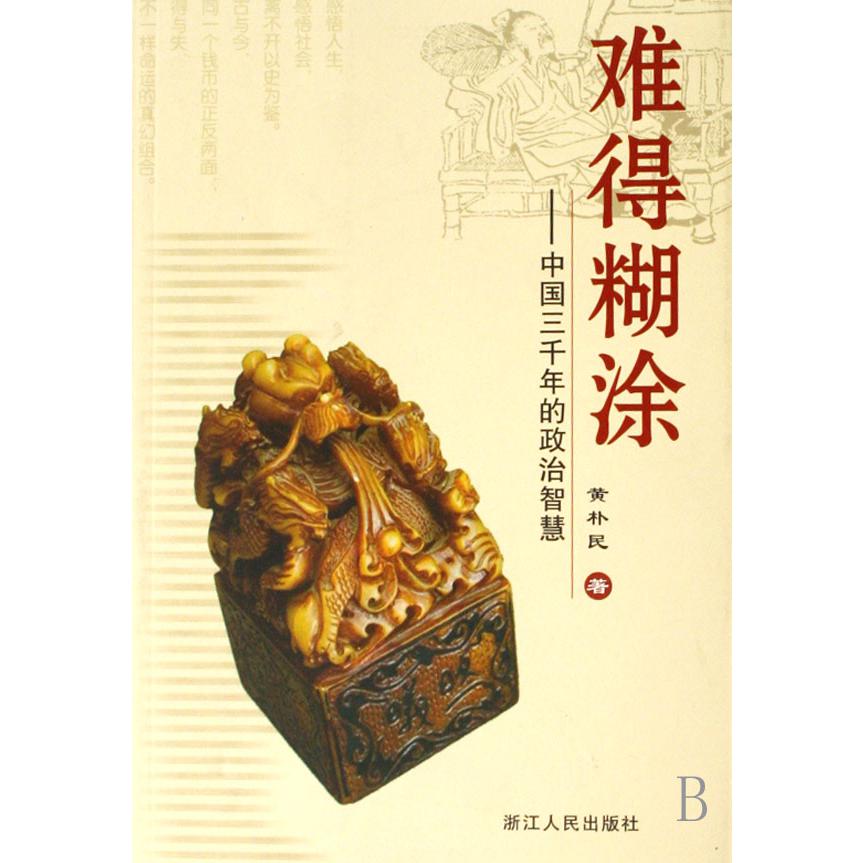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难得糊涂--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智慧
ISBN: 9787213034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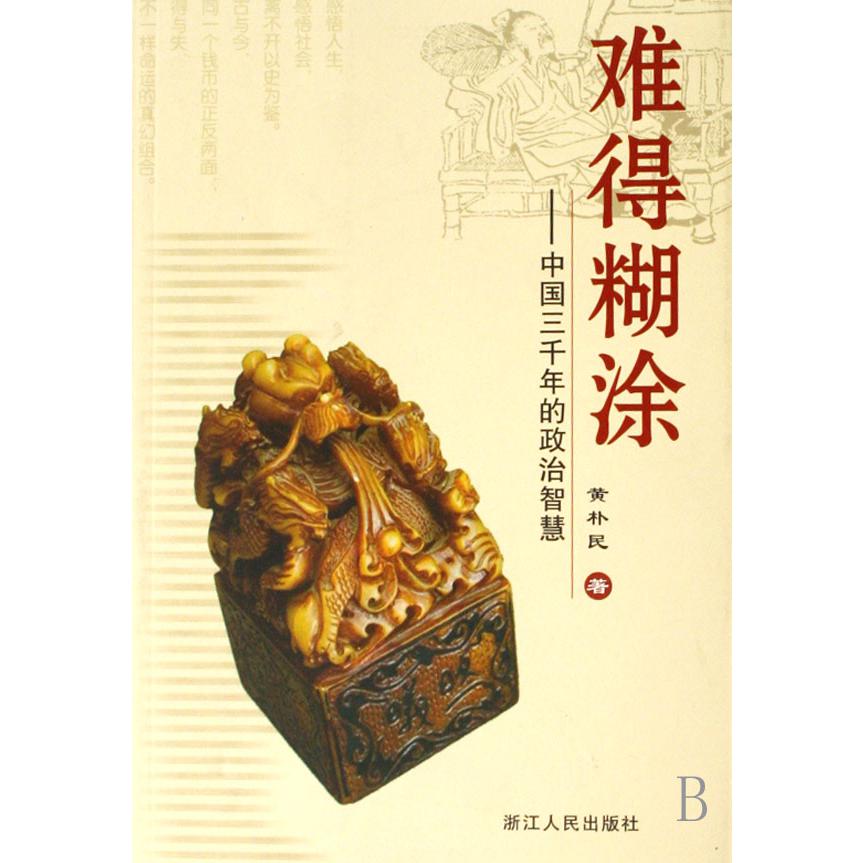
黄朴民,男,浙江诸暨人,1988年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详解》等:主编有:《孙子探胜》、《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等;并著有《寻找本色》、《历史无间道》、《难得糊涂:中国古代官场政治智慧》等学术随笔集;曾在《历史研究》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儒家二掌门孟轲先生对本门开山鼻祖孔老夫子曾经作过很妥帖的评论 ,称道孔子是“圣之时也”。意思是说,孔子不拘泥、不固执,他最能省 察时代嬗递的趋势,最懂得历史演变的规律,最理解人性的本质,最明白 世风的浮沉,他不会拘泥于各种教条,不会沉湎于虚幻假象,时刻保持着 清醒的头脑,处处把握着适宜的进退,不作无谓的较劲,不冀无谓的幸运 ,一切“与时迁移”,万事“应物变化”。典型的“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在社会生活中找 到最合适的位置。 历代统治者一再褒封、百般推崇;大批腐儒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其结果是,孔子脱离人间的大地,走上神圣的祭坛,由人转化为圣,由圣 晋升为神,于是乎,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孔子思想的理性精神沦 丧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尊古崇圣”情结,总是能 让历史人物蜕尽人性而铸就神性! 值得庆幸的是,大量相对比较原始的文献的传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 神化的迷雾而窥看到历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赏历史人物固有的个性风采, 认识和借鉴历史人物深邃的思维理性。孔夫子的情况亦复如斯,《论语》 、《礼记》、《左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使孔子作为一位平 凡随和而又伟大高明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换句话说,这些典籍有 关孔子言行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孔子属于典型 的性情中人,时常流露真情而不加任何掩饰;二是孔于具有睿智的文化理 性,其所反映的思想能够切合社会的实际和人性的秘密。前者让我们倍感 亲切和自然;后者则让我们深深地折服于孔子的智慧,使得我们乐意穿越 时空的隧道,随同他神游思想的乐园,徜徉于精神的港湾。 先说说孔夫子的平凡人性和本色人格。《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竹林 名士王戎之言:“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孔夫 子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肉有血、倜傥风流、喜怒哀 乐皆形于色的普通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物,他的举手投足、一 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充满着“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在孔子 身上,绝对见不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虚伪。有的只 有表里如一、内外澄澈的纯真! 你看他多么的自负,多么的不安于位,热衷于表现自己,执著地推销 自己,孟夫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自命不凡和 心高气傲是儒家人物的通病,所谓“人之患好为人师”。就是他们为人处 世的真实写照,以孔夫子为最甚,他动辄就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 用我者,“三年有成”。甚至连三年时间都不要,“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 孔夫子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站着吆喝不腰疼”, 理由很简单,乃是他自以为系“天纵之圣”,是古代优秀文化的唯一承继 者,理所应当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崇高义务,并且具备这方面的杰出 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遗憾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有眼无 珠,就是鼠目寸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没有发现他这位经纶之才, 害得他栉风沐雨,东奔西走。无人间津,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 。天道不公,命运不济,莫甚于此,每每念及这种辛酸遭遇,孔子的心理 就无法平衡,用今天的流行词语来形容,就是很“郁闷”、很“不爽”。 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发牢骚,讲讲怪话:我难道仅仅是一只悬挂在墙 壁上的大葫芦,中看不中吃吗!他可没有那种“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 宜放眼量”式的雅量和雍容,越想越发不是滋味,越发没有情绪,气恼懊 丧之下,破罐子破摔,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地方另开局面,寻觅 机会的奇怪念头,就像当年泰伯、仲雍万里迢迢奔赴南方卑湿之地,断发 文身充当蛮夷人的头领一样:“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圣人”应有的高雅风度,只能给人 们留下大言不惭、自我标榜,想当官急不可耐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 们看到了孔夫子富有人情味的坦率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心口如一 ,富有童心,绝对没有半点后世那些伪名教、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 的气息,也不曾有后世那些酸儒生、迂士子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表现。 为人贵在真诚,处世重在坦率,孔夫子身上的真诚与坦率,理应得到我们 的理解和尊重。 孔夫子自己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话有说得对的, 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三十而立”马马虎虎可以成 立。“耳顺”也是事实,但是“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至于“知命” 嘛,更是谈不上了。他像任何普通人一样,总是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 己的话,耳朵根特别的软,听得进表扬,喜欢别人的恭维,却难以接受批 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是出于对孔子本入的信任和爱护。我们只需 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忠言逆耳”、“从善如流”就孔 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论语》等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孔子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 ,是曾参,是闵子骞。这些人并没有突出的才能(孔子也承认颜渊是“于我 无所助也”,曾参是“也愚”),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光大儒家学说方面作出 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況稍好一些,毕竟还编过一部《孝经》)。他们之 所以为孔夫子所器重、所称道,好学不倦、恪守孝道、为人善良厚道、做 事敦实诚朴等等,统统是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善于揣摩 老师的心思,总是挑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着孔子的耳朵里猛灌。在他们的 身上,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是不存在的,自由的思想、出格的言行更 是不见踪影。用孔夫子自己的话讲,就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是因为 他们甘心当老师的应声虫、留声机,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低眉顺眼,像 鹦鹉学舌,依葫芦画瓢,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弟 子。 相反,像子贡、冉求、子路这类学生,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一举 一动不那么中规合矩,有时甚至快人快语,敢于对老师的某些做法大胆质 疑,爽直针砭,孔子心里难免不舒服,脸上自然挂不住,动辄要斥责、“ 修理”一番:“野哉,由(子路)也!”“(冉求)非吾徒也,小于鸣鼓而攻 之可也!”一副妇姑勃谿的样子,半点儿没有“尊长”者的雅量,离开孔 子自己提出的“温、良、恭、俭、让”君子标准远去了。 在《论语》、《左传》、《礼记》等典籍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兴之所至随意开口骂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樊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地向 孔子请教怎样耕田,如何种菜,这本来是勤工俭学的好念头,知识分子放 下身段,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高姿态,无可厚非,但结果却让“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的孔夫子大动肝火,臭骂一顿:“小人哉,樊须也!”孔 子的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认真听讲,大白天在课堂上昏昏 沉沉打瞌睡——“昼寝”。孔子不反省检讨自己授课方面的问题,反而大 光其火,勃然震怒,声色俱厉地斥责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类感情冲动,充分反映了孔子 和芸芸众生相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正因为孔子不讳言、不 掩饰“人性的弱点”,孔子才不是道貌岸然的“圣人”,才有最大的亲和 力,才让他的学生对其产生休戚与共,“与子偕行”的深厚感情。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孔夫子风格个性的形象写照。 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夫子的言行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因 为感情的偶然冲动而迷失惘然,从而对人对事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他的理 智始终是清醒冷静的,所以,尽管他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弟子有所保留 、有所不满,但是依然肯定他们的大节,为他们去做官、去做事积极创造 条件,依然认可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他称道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为之宰”;赞扬子路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认可 子贡长于经营之道“亿则屡中”,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依然怀有深 厚的感情,为自己弟子们的遭遇所揪心,所牵挂。对于路惨死的悼念,就 体现了这种至情实感:当子路在卫国的政治动乱中不幸殒命,被暴徒砍成 一坨肉酱的噩耗传来,孔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吩咐门人倒掉厨房里所有的 肉食,整天不吃不喝,整个人如同傻了似的,伤心欲绝的真情彻底流露, 没有丝毫的掩饰。不乏理智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 追求。这正是孔夫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夫子的伟大之处!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