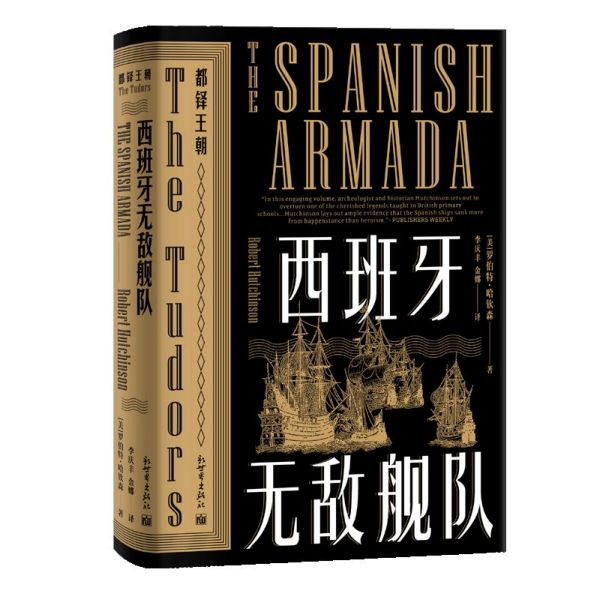
出版社: 新世界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6.10
折扣购买: 西班牙无敌舰队/都铎王朝
ISBN: 9787510469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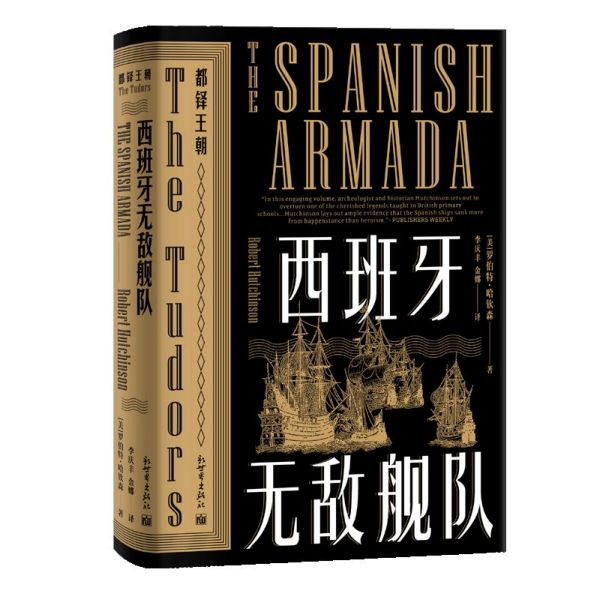
罗伯特?哈钦森是英国国家通讯社的防务记者,后成为《简氏防务周刊》的出版总监,负责图书、报刊出版和电子出版。哈钦森同时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伦敦古文物协会会员、苏塞克斯大学教会考古学方面的助理导师、宗教改革时期考古学专家,在2008年新年受勋名册上被授予英帝国勋章。 哈钦森相信英国历史中的真实故事比任何电视节目或银幕作品都更富戏剧性和感染力。在他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如“都铎王朝”系列中,他尽可能多地在探索研究中使用原始资料,因为“阅读人物自身在那个时代说出的特定语言,是十分有益的”。哈钦森拥有强大的叙事能力,“让叙事本身独立而纯粹”是哈钦森的写作理念,他的作品正文均一气呵成,不需要读者做出停顿,读之令人酣畅淋漓。
1568年5月16日晚7 时,伊丽莎白一世的宿敌踏入了一片前途未卜之境。这位宿敌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英格兰西北部那片遥远的海滩登陆。这天是星期六。旷野上,风在呜咽。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位宿敌,便是她的表侄女——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在横渡索尔威湾(Solway Firth)暗礁密布的浅滩后,玛丽女王终于逃出了苏格兰。而后,玛丽女王乘着一艘小渔船在坎布利亚(Cumbria)沃金顿(Workington)附近登陆。和内战中两眼一抹黑的逃难者并无二致,她也是满身淤泥,除了一身污秽不堪的行头,已是身无分文。然而,纵使困难重重,追随者已所剩无几,且个个筋疲力尽而又心灰意冷,这位一头褐色长发、身高1 米8、年仅25 岁却结了3 次婚的女人,依然傲然伫立在他们面前,浑身上下散发出一个女王应有的、难以掩饰的气魄和威严。只不过,连续数月的恐惧、心碎和窘迫之后,她红褐色的眼眸已不再明亮。 3 天前,她手下的6000名将士在兰塞德(Langside)即今天格拉斯哥(Glasgow)的南部,被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她父亲的私生子莫里伯爵(Earl of Moray) 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率领的效忠于苏格兰新教贵族的小股武装一举击溃,战事历时仅45分钟。而在此之前,她已经被逼逊位。其年幼的儿子被拥立为苏格兰国王,是为詹姆士六世(James Ⅵ)。莫里伯爵则出任全权摄政王。现在破晓将至,玛丽投书表姑伊丽莎白,哀求能私下谒见,渴望她能施以援手助自己夺回王位,并让那些乱臣贼子血债血偿。 作为访客,玛丽这个表侄女确实不怎么招人待见。她曾将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的纹章并置于自己的私人纹章之上。彼时的她是何等英姿飒爽!此举无异于宣称她不仅是苏格兰女王,同时也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她是亨利八世的妹妹、长公主玛格丽特(Margaret)这位曾经的苏格兰王后的后人。 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相处得不甚融洽,她还曾拒绝了玛丽立其为自己的继承人的要求,但她依然很同情自己这个表侄女的不幸遭遇。在她看来,君权神授,苏格兰逼迫女王退位背离天道。但与此同时,她很清楚,在自己治下的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眼中,她伊丽莎白才是异端。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父亲亨利八世在合法妻子——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尚未过世时,便和安妮·博林媾和而产下的孽种。多少人都在祈祷,祈祷不久之后头戴英格兰王冠的是玛丽而不是她伊丽莎白,对此她同样心知肚明。 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则与伊丽莎白所虑不同。他既没有她作为王室一员的兔死狐悲,也没有她对神圣王权可能受到侵犯的种种隐忧。在他看来,苏格兰女王玛丽踏上英格兰的领土,不仅对其主子的王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还威胁到了他自身的政治地位,乃至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仅如此,苏格兰女王玛丽笃信天主教,她的到来无异于将羽翼日渐丰满的英格兰新教置于险境。新教目前的地位来之不易,是多少殉教者在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执政时期从血与火的抗争中争取的。所以,这位苏格兰女王来到卡莱尔城堡(Carlisle Castle)东南塔楼伊始,纵然城堡再舒适,她还是立刻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全天候严密监视。但这一切已不足为奇了。即使是在噩梦中她又何曾想过,接下来她会被伊丽莎白当作最不受待见的客人囚禁长达18 年之久。虽然获准保留苏格兰女王的虚衔和待遇,但她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将被关押在英格兰北部,继而被押解到中部地区,常年受到严密看防,每日度日如年。 塞西尔很不安,因为他很清楚,在英格兰国土上的不少地区,人们依然虔诚地信奉天主教。伊丽莎白治下臣民凡300 万之众,一多半都是顽固的天主教徒。例如,直到16 世纪末,兰开斯特郡(Lancashire)大部分臣民都还信奉着天主教。 在苏塞克斯郡和汉普郡这些沿海战略要地,在保守的乡绅和逃亡神父的滋养下,天主教这一陈年老教竟依然散发着蓬勃生机。在苏塞克斯郡,很多教堂的圣坛依然傲然矗立着圣坛屏7,公然向政府叫板。1568年的一份官方报告同样让人忧心忡忡:在那些已经拆除圣坛屏的教堂,“教众还精心保管着圣坛屏,时刻准备拿出来再派上用场”。圣像并未毁掉,而是被藏匿了起来。“天主教其他教具也都被藏了起来,如果要做弥撒,一天之内就能凑齐所需的全部用具”。圣杯也悄然藏匿,静待天主教古老仪式的回归。在参加新教会仪式时,教众带的竟然是弥撒书;而女人们和老家伙们公然谈论着念玫瑰经时应该戴什么样的念珠,全然将上帝的福音抛在脑后;牧师们身着黑袍却在衣领处佩戴白色领巾。 在汉普郡,主教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发现想找一名能传播“合乎教义的、可靠的真理”的牧师竟比登天还难。他还发现,即便是在温彻斯特大教堂,顽固鼓吹“天主教的权威和教义”的牧师也不乏其人。对此,他极为愤慨。9 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到来是个不祥之兆,必然遗毒无穷,这就是塞西尔对此的精确研判。其后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他的判断。第四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在英格兰可谓身份显赫,贵为一等勋爵,却是个自私又自负之人。翌年,即1569 年上半年,这位天真到近乎愚蠢的家伙竟紧锣密鼓地谋划着要迎娶囚牢中的苏格兰女王为妻,做着有朝一日成为王配(king consort)的春秋大梦——即便做不了英格兰女王的王配,总要混个苏格兰王配当当。而玛丽本人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同谋。为了摆脱伊丽莎白的既不情不愿又强人所难的好客之道,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个天真到家的公爵,然而机关算尽,却只落得事与愿违。她又密信通知虔诚的天主教徒诺森伯兰伯爵(Earl of Northumberland)和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希望他们能帮忙解救自己。信中还扬言若有必要,可诉诸武力。 在16 世纪,霍华德家族成员有一个通病,他们简直骄傲自大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诺福克公爵也不例外。其为人一向狂妄自大,身败名裂只是早晚的事。一提起自己让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和位于诺里奇(Norwich)的富丽堂皇的豪宅,他便不知廉耻地吹嘘,说自己的岁入“与整个苏格兰相比也不遑多让……站在诺里奇的自家网球场上,他寻思自己应该和某些国王平起平坐了”。伊丽莎白生性多疑,又嗜财如命。不阿谀奉承女王就罢了,若他真想打消伊丽莎白的疑虑,就应该闭嘴,可他偏不。王室向其发出传票强制其出庭,他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怀疑,公爵这是要当那些天主教臣民们的领袖,打算起兵造反了。事情一发不可收拾。这年10 月,诺福克公爵在去温莎(Windsor)途中被捕,随即被押往伦敦塔下狱。这里曾经关押过不少其家族成员:1547 年1 月,其父就是因狂妄自大(事实已构成谋反),擅自将“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即爱德华三世)的王室纹章私刻于私人纹章(heraldry)上而触犯了僭越罪在这里被处决。 1559 年起伊丽莎白开始施行新的宗教政策,但是无论是在经济薄弱的郡县,还是在靠近苏格兰边境的北部地区都收效甚微。与伦敦金碧辉煌、精美绝伦的王宫相比,诺森伯兰郡、达勒姆(Durham)和约克(Yorkshire)等地仿佛不在同一个世界。在这些地区,仿佛已故女王玛丽一世仍在坐镇朝堂,人们一如既往地遵守、执行宗教改革运动前的旧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圣水、玫瑰经、玫瑰念珠、圣像和用于祭祀的蜡烛等天主教教具都在向官方宗教新教教义公然挑衅。狂热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北部地区就像一口沸腾的大锅,锅内掺杂的种种发酵的怨恨和反动思想,迟早会外溢殃及其他地区。 1 5 6 9 年1 1 月9 日, 第七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 珀西(Thomas Percy)和第六代威斯特摩兰伯爵查尔斯·内维尔(Charles Neville)起兵谋反。教堂的钟声回荡不息,这是佃农的集结号。在他们看来,不久前才刚被转移到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塔特贝里城堡(Tutbury Castle)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虽未登英格兰大位,但还是真正合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他们决意南下,将玛丽从监狱中营救出来,以恢复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1211 月14 日,叛军高擎“耶稣受难旗”抵达达勒姆,并准备继续征伐。“耶稣受难旗”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上次出现还是在32年前的“求恩巡礼”叛乱(Pilgrimage of Grace)中,而彼时叛军讨伐的对象正是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现在,叛军开始冲击11 世纪建造的大教堂,他们扯下一切与新教相关的物什,并将英文祈祷书和《圣经》全部付之一炬,而后便开始兴高采烈地做弥撒。 在约克郡,枢密院北区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North)第三代苏塞克斯伯爵托马斯·拉德克利夫(Thomas Radcliffe)陷入了兵源不足的窘境。他手下只有400 名装备不齐的骑兵,其忠诚度也要打个问号。一想到要在战场上与叛军对决,他心里便直打鼓。对于身处425 千米之外的伦敦、虔诚地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来说,此次叛乱不过是历史的再现,本质上与曾经多次威胁都铎王朝的叛乱并无二致。13 1485 年,她的祖父亨利七世(Henry Ⅶ)在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 Field)中击败理查三世(Richard Ⅲ)后称王,此后便不得不应付此起彼伏的叛乱。1536—1537 年,她的父亲亨利八世数次镇压抗议拆除天主教修道院的叛乱,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赢得并不轻松。1549 年,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尚未成年的爱德华六世因推行英文祈祷书而承受了来自英格兰西南部、南部、中部及约克的叛乱,最后不得不躲进温莎城堡避难。同年,诺福克郡爆发克特叛乱(Kett’s Rebellion)。随后的1551 年,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拉特兰郡(Rutland)等多地又先后爆发叛乱。参与叛乱的“不仅有盲流,还有骑兵和手工业者”。直至1554年玛丽一世当政时期,英格兰的玛丽一世才通过与西班牙的腓力联姻最终平息了叛乱。现在,终于轮到她伊丽莎白面对这些手持简陋武器的愤怒平民了。都铎王朝好斗的天性在她胸中燃成了烈焰,她恨不得走上战场将那群乱臣贼子撕得粉碎。任何消极应战的举动都让她大为光火。 在约克,兰开斯特公爵领事务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of Lancaster)拉尔夫·萨德勒爵士(Sir Ralph Sadler)耐心地向塞西尔做着解释。目前,苏塞克斯伯爵不能贸然与叛军开战,他认为:“天主教这种古老的信仰正如积压在人们心底的沉渣,只需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泛起。” 纵观英格兰全境,支持女王(伊丽莎白)宗教改革事业的绅士屈指可数。百姓因为无知,迷信、盲从教皇推行的过时教义,明里暗里支持打着天主教信仰旗号的叛军。表面上看他们是支持我们,实则不然,他们是身在新教,心归天主教。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支军队去戡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从目前的形势看,圣子耶稣基督与圣父上帝各自为政、势同水火。圣子与我们为友,另一个却与我们为敌。 11 月16 日, 两名伯爵率叛军南下抵达勒姆郡的达灵顿(Darlington),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接着,他们发布了讨伐檄文,旨在争取民心、捍卫天主教传统习俗。檄文气势磅礴,既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又极其虔诚,呼吁饱受宗教改革折磨而郁郁寡欢的保守派民众揭竿而起。檄文中他们自称自己才是“女王陛下最忠实、守法的臣民”,强烈谴责女王身边那些怀着狼子野心的暴发户,指责他们整日挖空心思颠覆“古老而高贵的信仰”,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护“与《圣经》格格不入的新教异端教义”。他们警告民众,国外敌对势力将不惜动用武力,迫使英格兰回归天主教信仰。“我们自己必须快马加鞭,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如若不然,在不久的将来,敌人就将入侵英格兰,将我们彻底摧毁”。 我们要知错改错,如若不然,外敌就会大兵压境,我们都将沦为奴隶、契约工。是故,我们在此呼吁、命令……各位……16~60 岁间的所有教众。这是上帝的要求!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上帝的真教义,即天主教信仰。兹事体大,关乎我们的共同福祉。起来吧!披上你们的战甲。起来吧,扛起你们的武器!现在就参加战斗!胜利属于我们!战斗吧,否则国破家亡就在眼前,我们别无选择! 檄文结尾处保留了“上帝保佑女王”的传统句式,但他们要保佑的女王究竟是苏格兰女王玛丽还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就只有天知晓了。佃农们积极响应,但其他大部分人对叛乱并不热衷。对于年长的自耕农来说,亨利八世在30 多年前对“求恩巡礼”叛众的杀伐果决或许还记忆犹新吧。所以, 11 月16 日,当叛军在约克郡北部塔德卡斯特(Tadcaster)西郊的布拉默姆旷野(Bramham Moor)集结时,只招募到了3800 名装备简陋的步兵和1600 名装备差强人意的骑兵。16 这哪里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的信心遭到了重创。所谓“不知进退非真勇”,为了不做无谓的牺牲,他们一枪未发便掉头回家了。 叛军迟迟未能兵临伦敦城下, 这让新任西班牙驻伦敦大使——老谋深算的唐·格拉·德·斯派斯(Don Guerau de Spes)感到惊讶。他分明已经感受到,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伊丽莎白政府已近乎乱了阵脚。伦敦城紧急招募了2000 余“贱民”在莱斯特郡集结,以充实王室军队。政府军不仅兵员短缺,战马数量也明显不足,伊丽莎白女王已然无计可施。为维持新招募军队的运转,伊丽莎白不得不向国外富商巨贾贷款。17 据说她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她不仅在温莎城堡外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还选拔了不少步兵做自己的贴身侍卫。苦于长期无法在北部地区恢复有效统治,她无奈只好在温莎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签发诏令,宣布诺森伯兰公爵犯有叛国罪,剥夺了其嘉德骑士称号。 叛乱还有望呈燎原之势吗?在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奏疏中,德·斯派斯写道:“坊间传言称西部各地和威尔士的天主教徒准备效法北部天主教徒起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在马德里西北部45 千米处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圣洛伦佐巍峨的埃斯科里亚尔宫(palace of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坐在自己简陋的书房中。他盯着驻英大使发来的急件,陷入了沉思。自从与玛丽一世联姻,他已将英格兰天主教徒视为自家人。所以,当收到英格兰发生叛乱的消息时,他内心虽保持着警觉,更多却是高兴。腓力二世随即致信正在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执行镇压新教徒任务的战区总司令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费尔南多·阿尔瓦雷·德·托莱多(Fernando Alvárez de Toledo)。这封信措辞十分谨慎,他在信中向托莱多透露,恐怕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迫使伊丽莎白皈依天主教。 这个妇道人家给寡人的臣民、朋友和盟友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我们却一拖再拖,迟迟未能帮助他们逃离苦海。时至今日,该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声誉。上帝的神圣教义理应恢复……我们也理应将善良的天主教徒、基督徒从受压迫中解救出来。 若其(伊丽莎白)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你应通盘考虑,拿出一个最优解决方案。依寡人之见,我们应鼓励英格兰北部的天主教徒,私下给予他们经济援助。我们还要协助爱尔兰人,让他们拿起武器与异教徒做斗争,把本属于苏格兰女王的(英格兰)王位夺回来。 事实上,苏格兰女王玛丽和法国君主关系密切,腓力二世内心并不希望其成为英格兰的主宰。只是由于腓力二世无条件效忠于圣母教会(Holy Mother Church),他才打消了这重外交顾虑。他宣称“教皇和全体基督教徒都将毫无保留地支持”玛丽继承英格兰王位。 而在英格兰国内,北部叛军在撤退后依然不断寻衅滋事。11月第一周,4500 多名叛军包围了乔治·鲍斯爵士(Sir George Bowes)镇守的巴纳德城堡(Barnard Castle)。鲍斯爵士虽已须发花白,但久经战阵,曾多次参加对苏格兰的边界之战。无奈城堡戍卫已人心涣散,不少人翻过充当外围工事的矮墙临阵脱逃,有的在逃跑过程中丧生;有的则直接打开城门,迎叛军入城。最后,鲍斯迫不得已向叛军投降。叛军给的投降条件相当宽大,他们同意鲍斯率手下400 随从移师约克郡。随后,叛军再次告捷,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城防设施多处垮塌的哈特尔普尔港(port of Hartlepool)。此刻,叛军士气高涨,竟开始幻想西班牙军队可以即刻登陆与他们合兵一处。然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而就在此时,伊丽莎白的复仇之箭已在弦上。 12 月16 日,伊丽莎白万人讨逆部队的先头部队挥师北上,饮马冰封的蒂斯河(River Tees)。两名伯爵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抛下部队,向赫克萨姆(Hexham)方向逃窜。他们穿过英苏边境,向苏格兰寻求庇护。圣诞节这天,塞西尔致信萨德勒。他在信中引述了一个关于捕猎的故事来讥讽避难的逃亡者。如此类比颇为牵强,读来也显得不够自然: 几个人渣(害虫)逃到了异国(小树丛)避难;收留叛逆之徒、宵小之辈者,纵非贼寇,也该是同流合污者吧。他们是在等猎人走远,再逃往天涯海角吧。事已至此,英格兰的宿敌们却依然不死心。在他们看来,叛军并非在逃窜,而是适时进行战略撤退。直至1570 年1 月中旬,威尼斯驻法国大使阿尔维斯·孔塔里尼(Alvise Contarini)在报告中还声称,叛军正在赶往英苏边界的贝里克(Berwick)。他们将在此越冬,而且叛军“规模正日渐壮大,待到冬去春来,必能强大无比”。但是,栖居伦敦的德·斯派斯不久便洞悉了现实的残酷,他心痛地说:“英格兰天主教徒的表现着实令人汗颜,其梦想的事业已经破灭……他们缺的不是动力,而是坚强的领导。如此下去,必难以为继。” 噩梦接踵而至,诺森伯兰伯爵被出卖,交给了莫里伯爵。寡廉鲜耻的莫里又以2000 英镑的赎金将其移交给了英格兰当局。1572年,诺森伯兰伯爵在约克被斩首。威斯特摩兰伯爵则逃到了西属尼德兰。由于所有财产均被罚没,他只能靠西班牙人的施舍勉强度日。伊丽莎白眉飞色舞地告诉法国驻英大使,她已彻底击溃叛军,还赦免了约克郡和达勒姆郡民众。27 她还声称“我们生来就慈悲为怀”。然而, 这不过是漂亮的外交辞令罢了。她随后严令众将将所俘800余名叛众尽皆处死,死者绝大部分是底层“ 贱民”。 要将不法教徒一一处以绞刑需要不少时日,苏塞克斯伯爵担心“女王陛下觉得夜长梦多,心生不悦”。 1 月19 日,他提醒鲍斯“圣心难测……即使我如实相告,女王亦未必能听得进去。你现在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得越远越好。再耽搁下去,女王难免不对我心生龃龉,恐连累了你”。伊丽莎白果然大开杀戒。托马斯·加格雷夫(Thomas Gargrave)曾坦言,这种合法的杀戮将“使很多地区荒无人烟”29,这些地区的经济200 年内都将难以恢复。 表面上看,苏格兰女王玛丽对英格兰王位的威胁已经化解。事实上,塞西尔心里清楚,威胁并未得以根除,只不过是蛰伏起来了而已。1570 年1 月30 日,伊丽莎白的表兄——一向以心直口快著称的汉斯顿勋爵(Lord Hunsdon)就直言不讳地警告女王: 请陛下谨记,要时刻警惕苏格兰女王。否则,祸不远矣……目前,外部势力所策划的种种事件(阴谋)都和她撇不清关系。 在处理对都铎王朝的关系方面,梵蒂冈(Vatican)一贯慢半拍,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在协助英格兰天主教叛乱势力时也不例外。他自始至终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最终导致此次叛乱流产。 【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哈钦森“都铎王朝”系列拼图中的一块】 “都铎王朝”系列选取了英国都铎王朝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编织出一个传奇王朝的全景。 【以新视角解读无敌舰队的败北】 作者尊重史料,没有避重就轻一味夸大英格兰海军的力量,而是客观地铺陈史料,既表现了西班牙的犹疑,又写出了英格兰缺人少物的尴尬,突出了这场战争中的偶然性成分,并对沃尔辛厄姆领导的情报战着重墨描述。 【以史诗般的笔法重现海战场面】 这场战役是氛围英西力量对比的关键事件,书中场景描写大气磅礴,极富现场感,让人身临其境。 【运用前沿史料】 相比其他关于无敌舰队的作品,本书写作时引用了年代更新的史料和更新的研究成果。在正文之后还附上了相关数据,更直观,更具说服力。 【故事性强,情节环环相扣】 本书虽为非虚构历史,但采用叙述方式,行文流畅,阅读感受不亚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