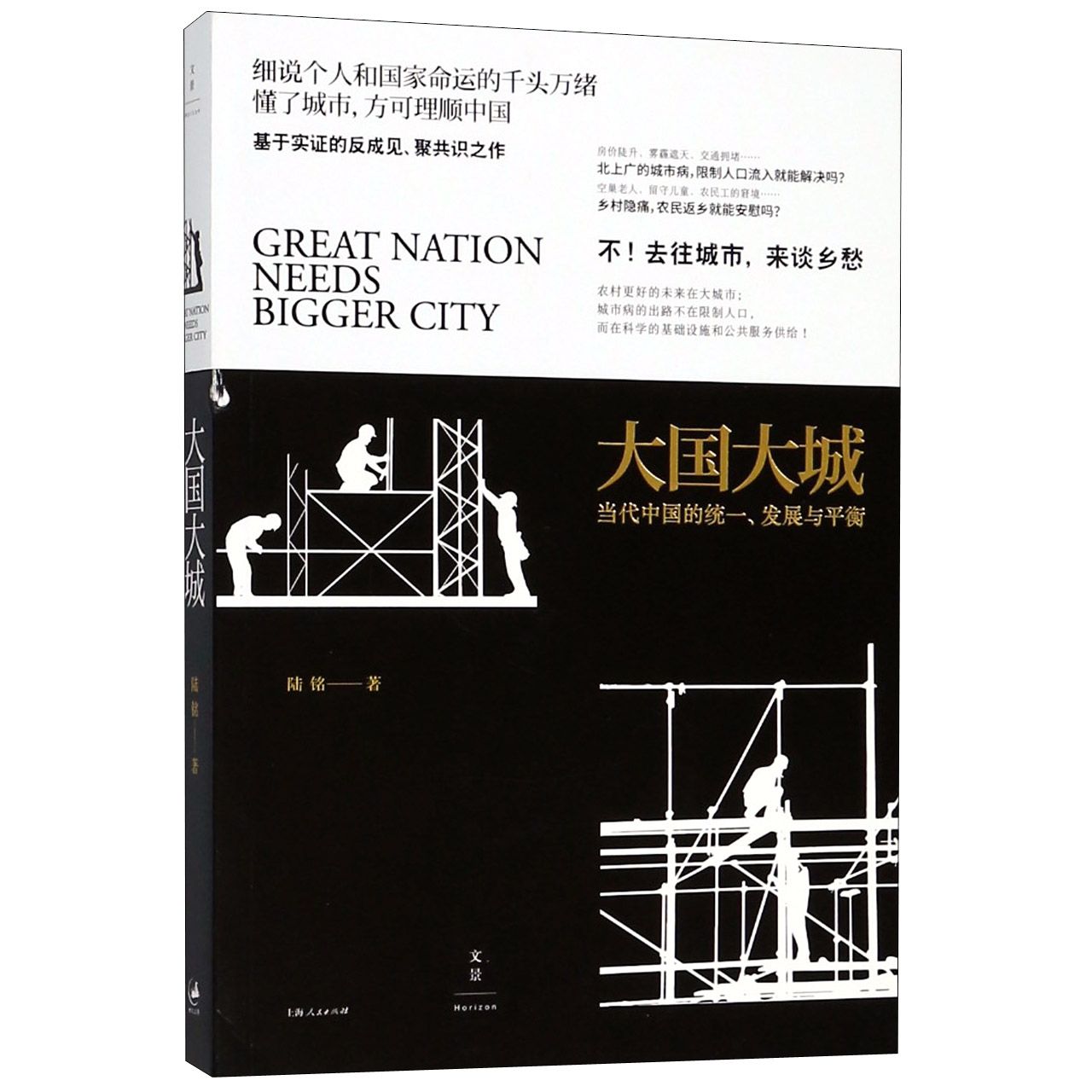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ISBN: 9787208138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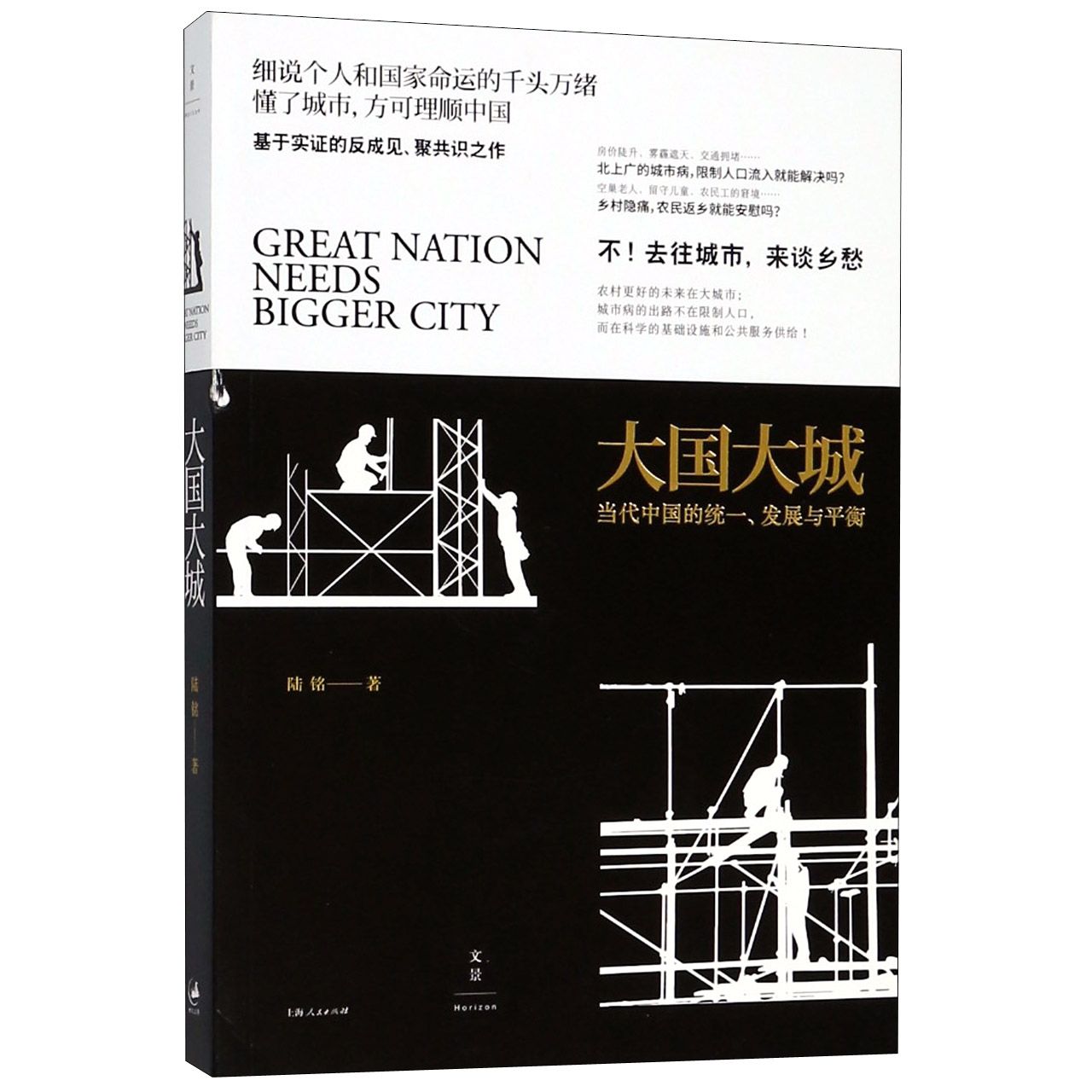
暂无
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业机会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 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 高校、***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多地分配给了***、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 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讲到。 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数据分析的结果。10 余年来的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Edward **aeser)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也用中国的数据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大。 通常来说,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规模相对*大的城市。于是,反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仅凭直觉就说,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反对大城市的人还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竞争,从而对工资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益提供证据。针对这些政策争论,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 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 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 至6.61 个百分点。 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大。对于*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 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 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个百分点。而对于*教育年数在9—12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 个百分点。*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益*小,仅为2.12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本地户籍居民享有*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这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到制度制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低技能者反而*容易找工作。 近来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两位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高,大型工业企业*多,而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大,公路*多,工业排污*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愿意去大城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愿意牺牲1.72% 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放心吧,不会的。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呢。 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务其实是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 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 年的40.5% 增长到了2014 年的48.2%,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与**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约低了10 个百分点。无**偶,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也是比其他相同发展阶段的**低了10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 其一,在*近10 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 相应的,使用资本*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检讨, 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多年。 1. 比较**经验,解析本土现状,立足当下中国发展困境,聚焦上海发展道路。 2. 呼吁取消人口自由流动门槛,倡导用发展大城市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谏言以人均GDP的均衡取代对区域GDP均衡的追求。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省流转,让农民工同等享*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待遇,让留守儿童进入城市接*教育,让城市病在拥挤中解决……成见之外,情理之内。 3. 逃回北上广!系统论证发展大城市对个人、群体、**的好处! 4.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影响力青年学者陆铭教授多年研究、力倡观点结晶,基于实证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