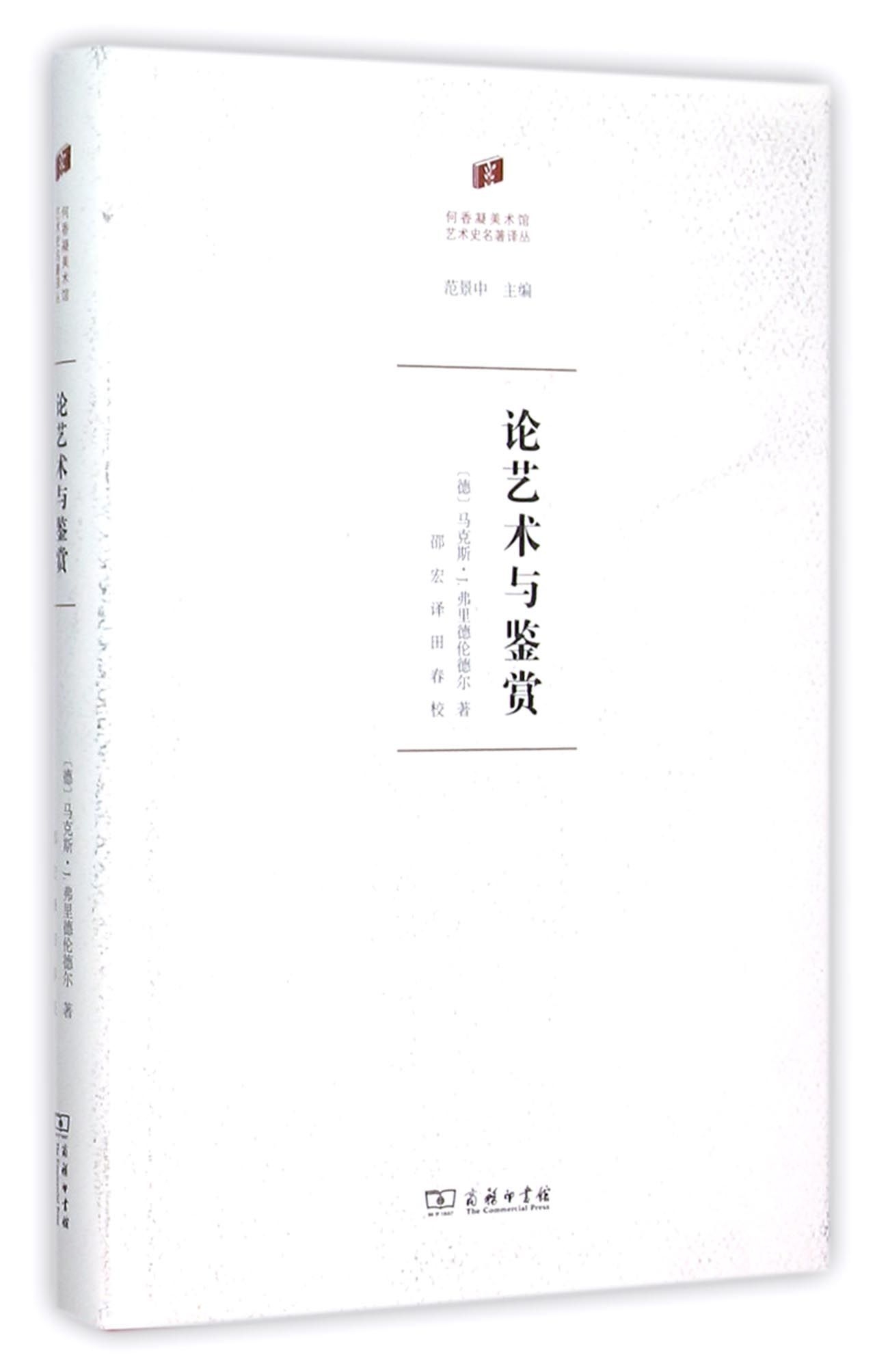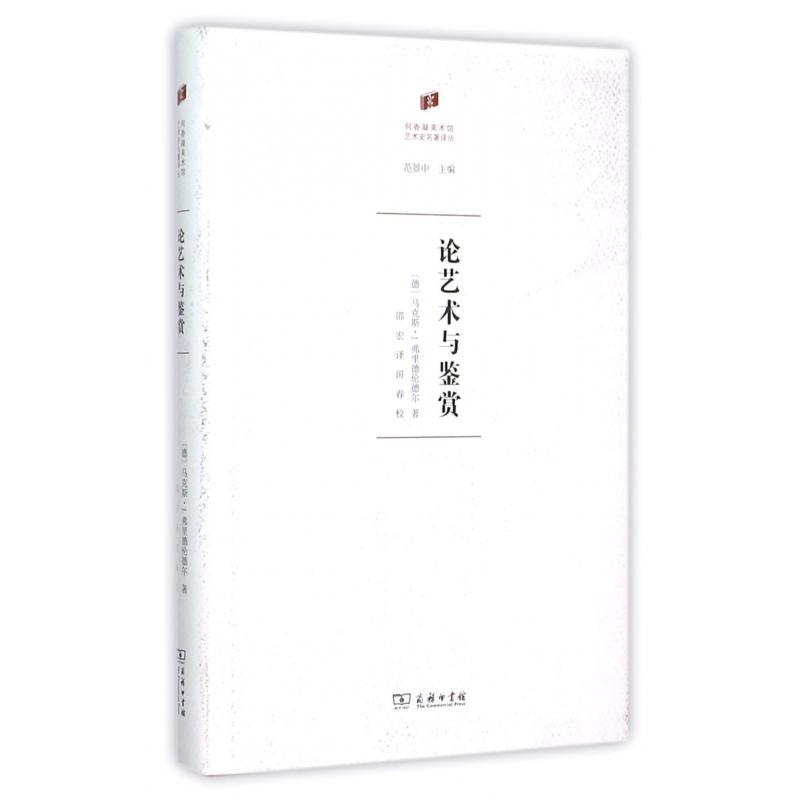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44.80
折扣购买: 论艺术与鉴赏(精)/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17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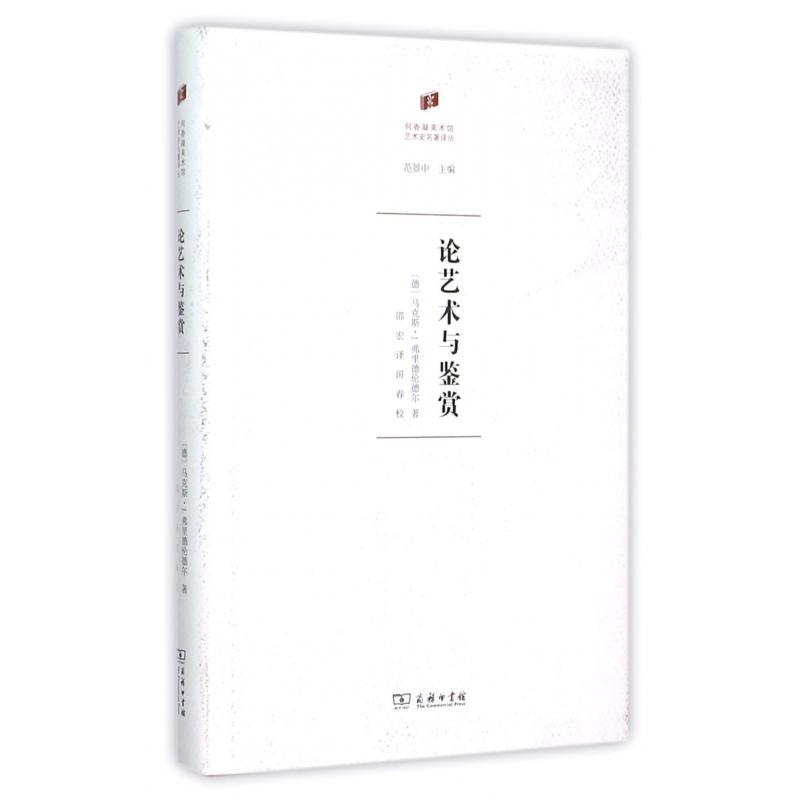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马克斯J.弗里德伦德尔(Max J.Friedlnder,1867—1958),曾任德国柏林绘画馆馆长、艺术史家;擅长以鉴赏家式的方式研究艺术史。其基本观点是:不应通过宏大的艺术和美学理论,而应基于感受力,即以风格批评的方式来审视作品。主要著作有:《十五和十六世纪尼德兰绘画中的杰作》(1903)、《从杨凡艾克到布鲁盖尔》(1916)、《丢勒》(1923)、14卷本巨著《早期尼德兰绘画史》(1924—1937)、《真迹与赝品》(1929)、《论艺术与鉴赏》(1946)、《论风景画》(1947)。 译者简介: 邵宏,195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艺术史博士,现为广州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译著有:《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合译,1995)、《美术术语与技法词典》(合译,1995)、《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2008)、《风格问题》(2015)。
二存在、现象、对事物的客观兴趣 存在着的事物作为现象[appearance]映入眼帘。心灵阐释现象,心灵由此推断物的存在并构建起物的幻象,从而制作成艺术品;在这一过程中心灵不仅需要对对象做补充、填空和强调,而且还要对对象容忍、 有耐心和做挑选。 现时存在的艺术家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会依据艺术家对工作的构想,对他必须创作和希望创作出的作品的构想做改变。这种受到改变的关系有无数个阶段,我们可以依据年代顺序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只要艺术家是描绘诸神或圣者、叙述传奇或神话,他就得将精神的观念和心灵的情感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如果不是绘画传统的话——并 且运用从自然中获得的印象,赋予自己的创作以栩栩如生和真实存在的错觉。 为了应对自己的工作,他毫无必要去观察在偶然的情景和背景中出现的自然特征,或者甚至不会将其视为值得入画的[picture-worthy]。他“选取”、挑出和拣出符合自己意图的东西。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在某处提到“艺术家鬼鬼祟祟的偷窃”。一位希腊瓶画家或一位中世纪的祭坛画家,他需要的是多么少啊!需要得少并不是因为他无能,也不是因为他缺乏精确的视觉——这个少不是缺少毫发不爽的肖似——但相反的是,无限得多——过多的世俗空间和个人特征——不仅无助于他的意图,甚至会降低、混淆和败坏画家的视觉,从而危及作品。画家要展示的是户外无法见到的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某种事物,并且他是将绘画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视觉的经验。 每一个时期对逼真的要求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几百年前看起来很逼真的东西,现在给我们的印象却是程式化的[stylized]。继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之后,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时代、发现的时代。人们的兴趣由不可见的造物主转向可见的宇宙万物。随着15世纪的到来,艺术家变成了类似自然科学献身者的角色。他在观察中获得了中立、宽容和多视角的态度。尤其不同凡响的是,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日益受到重视,譬如人与空间和光线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之物不再依照先入之见来描绘,而是必须与现象保持一致:现象受到人们的如此信任,以为它能提供有关这个欢快而令人迷惑的世界的可靠信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入画了。不论以何种方式,视觉经验都要与展示清晰的现实这一意图相联系和协调。 对事物的客观兴趣——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干预了这一意图。在查验树叶的学究的植物学家身上我们能够找到那种客观兴趣,那是最纯粹形式和最高程度的客观兴趣。首先,植物学家比艺术家对树叶了解得多,因此他看到的也更多。然而他的观察受到了限制,因为树叶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是作为它所属种类的标本使他感兴趣。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不同于其他的树叶,这一事实只能使他感到困扰和迷惑。他还有一个麻烦来源于,他的学术观察对象在空间的位置、与肉眼的距离以及在特定的光线条件下,会产生变形、扭曲、短缩[foreshortened]和褪色。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不受任何偶然情形干扰的树叶的固有形状和颜色。 实际上,对事物的纯粹客观兴趣与艺术毫无干系,但它与造型的能力一道能够丰富艺术创作。于是,17世纪的荷兰绘画便极大地得益于对有关存在之物的知识的渴求,这一情形在许多天赋不足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自诩的荷兰“写实主义”[Realism]未能如希冀的那样理解个性问题,那么对这种情形可以做如下解释:有关存在之物的描绘被要求和制作成准确可靠的记录;人们绝不可能满足于现象——这就得由知识来补充,于是导致类型化[type]。当然,肖像画[portraiture]提供了一个例外,肖像画里对事物的客观兴趣和对个性特征的反应有部分重叠。 荷兰画家们是描绘真实事物的专家。波特[Potter]像农夫一样熟悉牲畜,桑雷达姆[Saenredam]像建筑师一样懂得建筑,威廉凡德菲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则对造船术无所不知。 就像对事物的客观兴趣一样,叙事的倾向也侵入了绘画。杨斯滕[Jan Steen]并不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机智的阅人无数者和原创性的喜剧作家。就其天生的才能而言,他并不弱于任何同代人或同胞,但作为画家,他没有取得或至少未能保持像格拉尔德特博赫[GerardTerborch]那样均衡的画技,谨慎使得特博赫学会了聪明地自我约束。斯滕在画故事、作乐或欢宴时,其画面过于喧哗和毫无修饰,他常常牺牲了制作的谨慎性。睿智的画家,曾冒险越过可见世界的终点与想象世界的起点之间的边界。19世纪上半叶,追求“诗意”[poetic]的倾向对绘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9世纪下半叶,画家们抛弃了诗歌、历史和逸事。随着对事物的客观兴趣的减弱,叙事的倾向也受到抑制,艺术变得独立和自主起来。画家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改变。哲学家们已对“自在之物”[thething-in-itself]产生怀疑,并且宣称现象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出于可靠的直觉——如果不是为了捍卫正统的利益——艺术家必定会反对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在19世纪,到处都兴起了——来自对那个消极信条的积极演绎——对现象的热烈关注。如果哲学家悲观地说“现实只是现象”,艺术家们则会乐观地回答“现象就是现实”。出于对毁坏有机联系的恐惧,画家们开始将构图、程式化、补充等所有主动的干预视为拙劣之举。印象主义给艺术家指出了一个立足点,他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必须毫无顾忌地描绘那些进入其视野的事物。对独特的视觉经验的自信需要有更明确的错觉,偶然挑选出的场景,粗犷、迅疾的用笔,以及漠视固有形和固有色: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在三度空间中偶然的位置和偶 然的光线环境中呈现出来的。既然画家再也不将一些概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了,于是类型便让位于具有个性的形式。画家让图画自己去记录故事、激起故事、讲述故事——“让”[let]的意思是laisser[任凭],而不是faire[促使]。画家不愿意变成一个与作品交谈的对话者。 杨凡艾克在画锦缎斗篷的时候,他对事物的客观兴趣使他本人服从于存在的对象:于是他创造出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同真实的锦缎斗篷一样;然而马内[Manet]的作品只是他本人满足于现象的产物。说这种差别只是在于主观的看法,这不会遭到反对,但在结果中却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站在一英尺、三英尺或两码远的地方,会发现杨凡艾克的作品呈现出丰富的错觉,而马内作品的效果则固定在一个明确的观看点——画家正是从这一观看点描绘对象的。 凡艾克的眼睛面对静止的世界而运动;马内的眼睛面对运动的世界而静止。 我不想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有能力给每位大师在大厦的同一层楼里各分配一间房子。每位画家——除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之外——根据个人的意向而对现象采取与他人不同的态度。尤其是自15世纪以来,诸多的边界已经被移动过了。天才的大师们——如提香[Titian]或是伦勃朗[Rembrandt],直到他们生涯的最后——超越了我所说的那些边界。丰富和复杂的创作拒绝被压缩在一个公式里。 至少还有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倾向清晰可见:从主动、有选择地改变多彩的生活影像,转变为接受以及坦率和虔敬地献身于多彩的生活影像,并且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身处的、相互联系着的、此时此刻的存在。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由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担任主编,由广州美术学院黄专教授担任学术策划,是一套系统介绍西方艺术史和艺术史学的丛书,精选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哈斯克尔、弗里德伦德尔、扎克斯尔、温德、库尔茨等世界一流艺术史家的西方艺术史学研究的经典论著约50种,并由资深艺术史研究者和中青年译者共同精心翻译完成,力图全景式呈现现代西方艺术史学一个多世纪来的面貌和形态,为国内西方艺术史学研究提供全面详尽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同时也展示了中国艺术史学薪火相传的学术历程。 本书汇集了是作者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所写的、汇集了一位权威鉴定家一生的个人经验的艺术鉴赏指南。它代表着从莫雷利、贝伦森到弗里德伦德尔西方美术史研究中鉴定学派的全部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