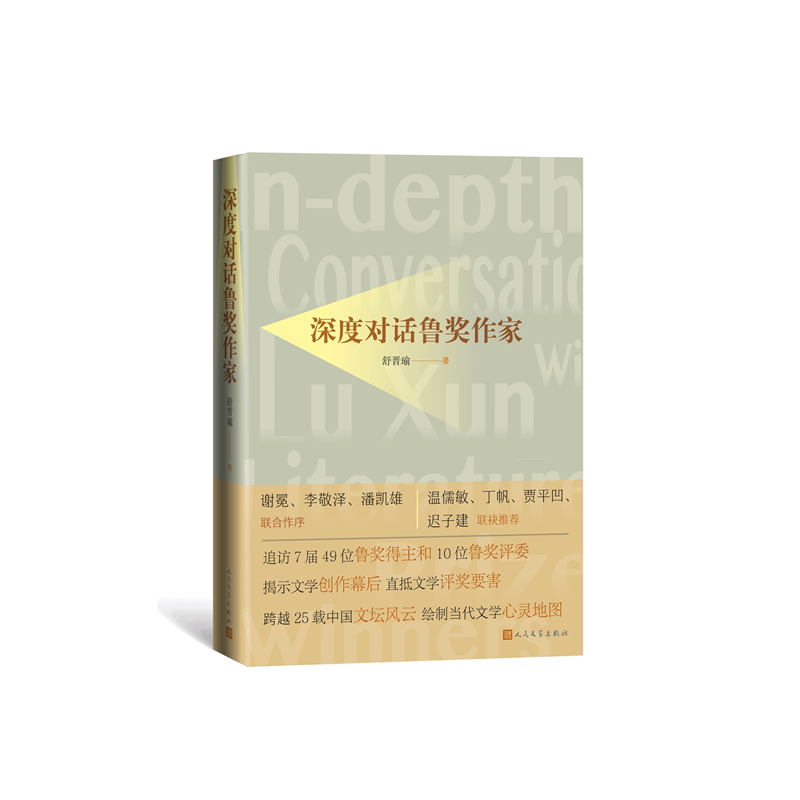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ISBN: 9787020169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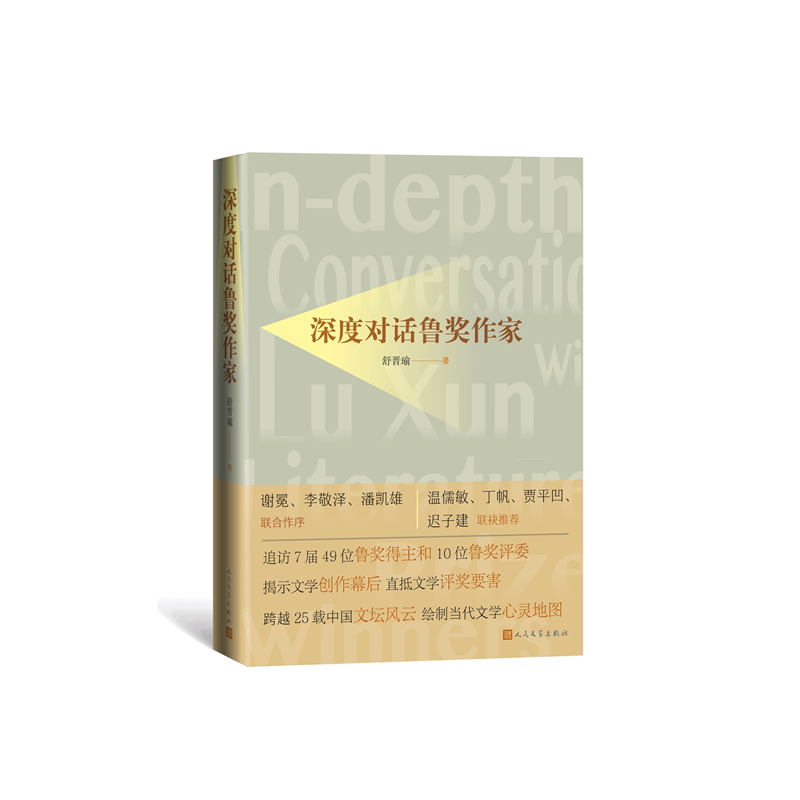
舒晋瑜,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自1999 年起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现为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史铁生: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史铁生 1951年生于北京,2010年12月31日逝世。1967年初中毕业于清华附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常年透析。病情稳定后,出版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作品多次获奖。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采访手记 看史铁生的作品,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思索。但是,这种思索相对于文字的内涵来说也往往显得浅薄。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于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 史铁生身体不好,也因此惜时如命。2001年,通过E-mail,我们的交谈方式算不得直接,然而当我看到他熟悉的语言展现在电脑屏幕上,仍然感受到一种力透纸背的真诚。 很喜欢看史铁生的作品。从《务虚笔记》《我与地坛》到《病隙碎笔》。他去古园了,我们便随他“去古园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是他作品的魅力。 “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地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地去看这些文字,而是借助这些蹒跚的脚印不断看那一直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2010年,“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永远地离开我们,只有他生前写下的文字,仍闪烁着生的光芒。 史铁生的写作没有计划。因为精力不济,多数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已。“我想对读者说的,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都在我的作品里。” 问: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历,是什么给予您如此大的写作动力,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 史铁生: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当然,用目前流行的话说“这有点儿累”,所以这历程也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轻松。我曾在《病隙碎笔》中写过:“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吗?所以被送上这条不见终点的路。”“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说到这儿,我真是有些惭愧,因为我很少能照顾到读者。所以,“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这话我实在是不敢当。 问:您的作品中常常有一种伤感,正是这种伤感和厚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和您的读书与思考有关吧? 史铁生:我并没有特意地追求伤感与沉重,但由上述写作动机 看,大约难免。我的意思是:随它去吧。说“这与我的读书和思考有关”,不如简单地说这与我的处境有关,读书和思考也是我的处境之一部分。我并不认为伤感与沉重一定就好,但既然确凿,也就有其表达的理由。 问:常常和朋友谈起您的作品,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近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一天能写多长时间?您是怎么安排写作和读书时间的? 史铁生:我的身体总是不大好。我得着两种“电视剧病”。怎么讲?您看现在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特别容易坐进轮椅,近来又特别容易得尿毒症了。这可能有助于戏剧性,可一旦成为实际,却一点儿都不浪漫。这两种病弄得我精力大减,写作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能尽力而为吧。再说,年至半百,改行怕是来不及了,只好仍在这行当中混着;《病隙碎笔》是我目前写作的实情。 问:您觉得哪些书对您影响最深?您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史铁生:关于读书,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与关注。我的体会是,一味地追求多而新,倒可能弄得自己颠三倒四不知所从。根本的问题,先哲们都想过了。其实,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只不过布景和道具日新月异,读书和思考只为不被它弄得找不着北。这只是我的看法,并无典型意义。 问:您还常去地坛吗?平常您都还有什么爱好? 史铁生:十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偶尔请朋友开车特意送我去看它,发现它已面目全非;这正是日新月异的布景和道具之所为吧。唯园中那些老柏树依然令我感动——历无数春秋寒暑依然镇定自若,散发着深厚而悠远的 气息,不被流光掠影所迷。 问:现在您忙什么? 史铁生:要说现在忙什么,大约就是透析,隔两天去一趟医院,就像上班,仿佛要弥补我从未有过正式工作的历史。我有时真觉得麻烦,可是想想,大夫和护士们是天天都得去呀,比我麻烦。我们一起透析,她(他)们透,我被透,分工不同,合作得很好。忙完了透析,总还是想写点儿什么,否则花那么多钱被透,什么都不干岂不可惜?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史铁生说,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 问:可否谈谈您的创作变化? 史铁生:最初的写作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像《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 问:谈到您早期的代表作,一般都绕不开《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那时的写作比较现实主义,那种写作的格调也没有延续下去,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假的乐观主义。我并不认为悲观 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悲观和乐观没有高低之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是我生活中比较温情的东西,有些作品写的就是比较悲观的东西,但都没有指向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我必须超越它。事实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某种风格、某种对感情的重视,在《我与地坛》中又接上了,但它又不一样,它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大了,它理解快乐和痛苦的视野要大多了。 问:您的作品涉及残疾人,但又超越了平常意义的残疾。 史铁生:我写作的题材不限于残疾人,我也写过插队的、街道工厂等其他不相干的。另外关于残疾我也有一些看法。我的残疾主题总是指向人的残疾,而不是残疾人。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作品,的确有一个个残疾主题。但是命运的力量又很强大,不是人可以改变的,人只能在一个规定的条件下去发挥自身的力量,这种规定的情境就是宿命。比如说你生来就是个女的而不是男的,你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在唐朝或宋朝,比如说我这腿,它就瘫了,你竟无办法,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人的主观力量只能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后做一些事情,你所谓接受的这个事实就是宿命。 问:您在《病隙碎笔》里强调:“写作需要真诚。” 史铁生: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务虚笔记》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问:《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 史铁生:肾衰竭之后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幸亏有透析,我才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 问:《病隙碎笔》书中谈到“残疾情结”,能看得出来您非常坦然地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问:《务虚笔记》思辨性很强,有些章节完全可以看作“冥思录”。 史铁生:许多人说我的小说思辨色彩比较重,我也不试图逃脱它。我写过一篇小文章,里面提到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命运,意思并不是说命运让我做写作这件事而没有成为一个木匠,而是说我终于要写什么大概已成为一种定局。我在《务虚笔记》的后半部分也提到这个问题:F医生对诗人L说,如果你有一种冲动要写诗,你去追踪它,那么你的根据是什么?追踪的是你呢,还是被追踪的是你?F医生的结论是,这足以证明人的大脑和灵魂是两回事,一个是追踪者,一个是被追踪者。就是说那种灵魂的东西已经存在于你的命运中,你面临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接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如果你试图离开它,也许更糟糕。所以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绝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屋子里,看看书,想些事情。世界的空间性对我来说太小了。 书摘插画 谢冕、李敬泽、潘凯雄联合作序 温儒敏、丁帆、贾平凹、迟子建联袂推荐 追访7届49位鲁奖得主和10位鲁奖评委 揭示文学创作幕后 直抵文学评奖要害 跨越25载中国文坛风云 绘制当代文学心灵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