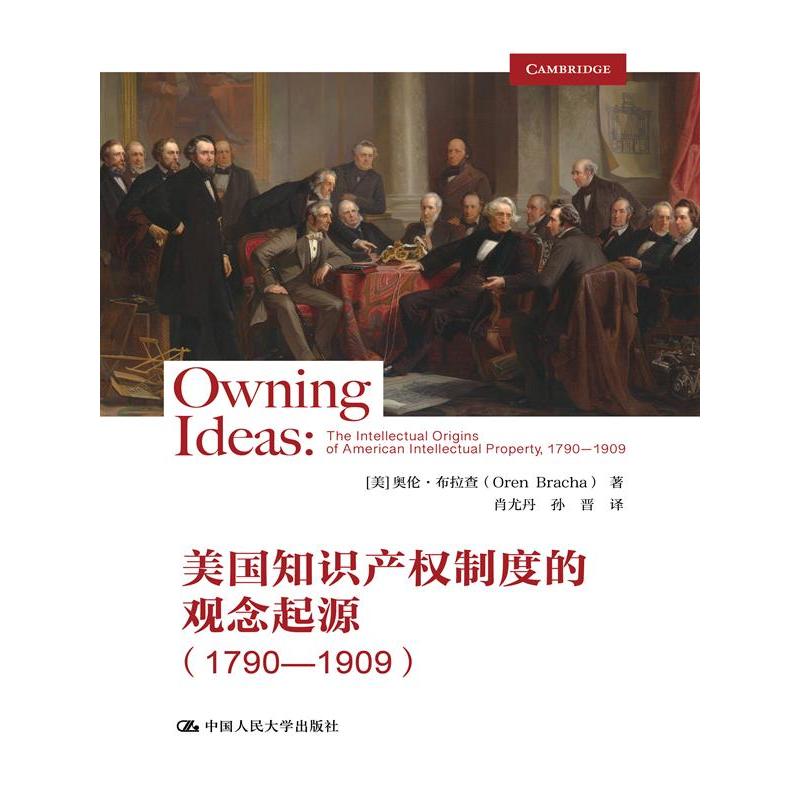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6.88
折扣购买: 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观念起源(1790—1909)
ISBN: 9787300330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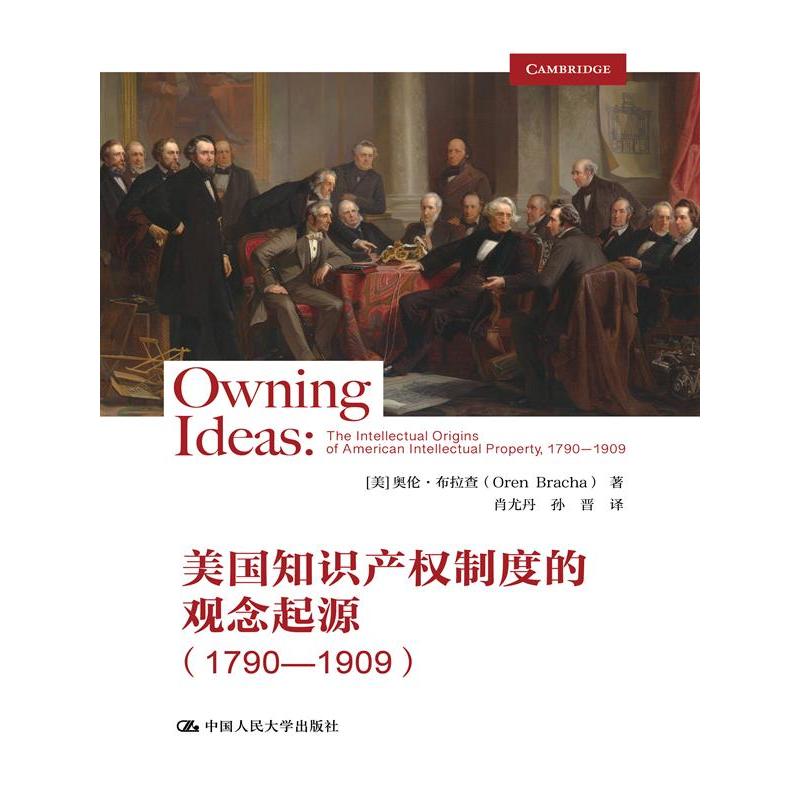
奥伦·布拉查(Oren Bracha):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院法学教授,著名法律历史学家和知识产权法学者,英美知识产权历史领域的先锋学者之一。在知识产权法和法律历史领域发表了大量论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知识产权、网络法、法律史和法律理论。
曾担任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的法庭助理。在加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之前,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参与多个教学和研究项目。
肖尤丹: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知识产权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立法与知识产权。出版《开放式创新与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历史视野中的著作权模式确立》等7部专著,《国际知识产权法》等2部译著。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修法研究支撑工作。
孙晋:法律硕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助理。参与出版译著《国际知识产权法》。
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无处不在。我们对这个观念早已司空见惯,也很容易不以为奇,但“知识财产”这一概念的确很奇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印发的精美宣传册可能告诉我们,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和其他财产权并无差异;博学的法学教授可能耐心地解释说,财产权没有理由不适用于无形的财富(intangible resources)。但这些解释无济于事。只要你认真思考知识财产的观念,就一定会觉得(某项)无形智力产品归我所有(owning an intangible product of the mind)的概念其实是非常奇怪而另类的。思想(idea)归我所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当创意、思想日益成为我们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我们为什么开始以某种财产的方式来理解和描述它们?本书要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扩展概念内涵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法官在1918年时写道:“对于人类最尊贵的产物——知识、被探明的真理、概念以及思想,法律的一般原则是,它们在被自愿传达给他人之后,就成了和空气一样自由共用的东西。”在布兰代斯写下这些话时,知识产权在范围和强度两个维度上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前一个世纪所有人的想象。现在知识产权仍在不断扩张,也极有可能远远超出布兰代斯当时的想象。被主张应当享有独占性法律权利(成功程度各不相同)保护的无形物(intangibles)的范围大得惊人,由近期的几个例子就可见一斑,比如瑜伽的动作(yoga sequences)、打高尔夫球的方法、规避投资风险的算法系统、基因序列以及街头艺人近乎裸体的牛仔造型。这不禁让人疑惑:我们是否已经突破了布兰代斯规则所能适用的界限,利用思想的自由是否变成了特例?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曾将这一进程戏称为“第二次圈地运动”(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将对知识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的私有化与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将公共土地变成私人财产的社会运动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确实正处于第二次圈地运动之中——且不管它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从最近几十年开始的,还是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那么应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最直觉的反应肯定是技术和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大一部分财富的呈现形式不再是土地或其他实体物(tangibles),而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性资源,这就大幅增加了私人通过知识产权控制这些无形财富资源的必要性。从历史来看,技术发展的确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新技术不但孕育出新的、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它们无所不包,从创造性的生产工艺到电影作品——还促进了商业化,创建了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的市场机制。不管怎样,这都导致了私人和公共利益对控制和分配这些资源价值的法律机制的需求。这种说法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它忽略了另一个强大的因素,那就是思想本身(ideas)。知识产权的扩张不只是科技发展和经济需求的结果,也是一系列特定思想的产物。自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ideology),为“思想归我所有”这一概念赋予了意义。这种思想观念虽然深受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并不仅仅是它们在智识观念上的直接映射。无形物所有权的观念正是在这种思想方法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半自发”(semi-autonomous)地形成的。至此,技术、经济和思想因素共同构成了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智识渊源(intellectual origins)。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学界对“无形物权利归属”这种现代思想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已经有相当透彻的研究,特别是在版权领域。总的来说,至少从15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关于知识财产的实践惯例和规则制度。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看成“智力”(intellectual)或“财产”。虽然在与技术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后来的图书出版活动中确实存在某些“权利”(entitlements),但它们都没有被视为“无形对象的所有权”(ownership of an intangible object)。一个人对其头脑中产生的智力产品享有所有权,这种新思想大约是在18世纪早期才开始出现的。到18世纪末,专利和版权的思想观念基础都已经被彻底改变。这两个领域都开始被一种针对智力创造物(intellectual creation)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思想所统治。个人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核心,不管是作者还是发明人,他们都是通过脑力劳动(mental labor)创造新思想的人。此时,这些个体的自然人就被视为智力创造物的所有者。
当美国的版权和专利制度在18世纪最后20年创立之时,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因此,这必然会让人觉得现代“作者所有权框架”(authorship ownership framework)已经深深嵌入了美国知识财产制度的基因之中。循着这样的假设,必然就会有人将美国知识产权从18世纪80年代萌芽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想象成这种初始遗传密码自发且必然的结果。诚然,科技发展了,新市场被开辟出来了,信息商业化的巨大机遇就会涌现出来。但是这个过程,是以作者权(authorship)为基础的原始知识财产模式向新领域延伸、完善自身的原则并且适应新环境的过程。这完全不是一回事。19世纪是知识财产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新的财产(法律、要件)元素得到发展——但它们绝非最初作者权理念的自然延伸,作者权的理念也并未成为知识产权法的核心要素和最根本的概念基础。但是作品所有者(authorial owner)的想象观念仍然拒绝退场,即使在个体作者身份从法律中消失(或者压根就没有体现在法律中)之时,它那柴郡猫式的咧嘴微笑仍然萦绕在法律中挥之不去。有时,它具有真正的力量,有时口惠而实不至,有时还表现得让人难以接受。在经历了缓慢而深刻的演进发展之后,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关于“思想归我所有”的全新思想认知框架。本书以专利和版权这两个知识财产领域中最古老且最重要的分支为背景,详细分析了现代知识财产制度架构的发展脉络。
在18世纪末,专利和版权法领域均处于深刻转型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官方对知识财产的新认识,即创造者对其智力产品享有财产权是一项普遍性规则。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专利法和版权法中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知识财产规则的旧特征。本质上,它们只是将旧制度中出版商和商人的传统特权加以普遍化,再将其赋予作者和发明人。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创造者当然享有财产权”这一基本制度框架承受住了各种挑战:经济利益的争夺、思想信念的冲突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最终结果就是完成了对“思想所有权”概念的全新整合(conceptual synthesis)。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是否有一般规律可循呢?新近的观点认为,19世纪美国知识财产制度的重大主题是推动“发明平民化”(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vention)的过程。根据这些观点,原本很难获得的、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能偶尔享有的特权被具有广泛可及性的普适性权利所取代,这使得发明,创造活动大众化。创新及其商业化活动准入和知识财产取得的程序性门槛和实体性限制大大降低。专利和版权,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只要满足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设定的制式化通行标准(standardized general criteria)即可。而制度改变的结果就是大批科技和文化创新者的创造活力得到释放,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财产权利享受其创新成果的社会价值。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大约在19世纪中期,发明活动在美国的确实现了平民化。美国的公司制度(incorporation)发展也是如此。从结构上看,发明平民化的过程与公司制发展为一种可被普遍采用的商业形式的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后者在后期的发展脉络上与前者是类似的。到了19世纪末,公司制的“平民化”促使美国的国家公司化(incorporation of America)。虽然众多个人和小企业继续依赖公司制作为有用的商业运作机制,但是大企业(big business)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且最持久的现象。公司制的平民化随即在由大型集团式私营组织主导的新兴市场中,带来了财富和权力的巨大集中。发明平民化也带来了类似结果。19世纪末,“平民化”的知识产权成为大企业重要的商业与法律工具,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公司化环境。18世纪的作者所有权个人主义遭遇了公司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一种新的合成概念出现了,作者权变成了公司作者权(authorship incorporated)。
与其他情形一样,在知识产权语境中官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并未被新的公司作者权框架所抛弃。即便在一些重要机制上知识产权制度开始倚重其他逻辑前提,其基本观念仍然是智力产品归作为个体的作者或者发明人所有。这就导致了许多古怪的法律和概念形式。在抽象的作者所有权观念之下,“思想归我所有”观念框架中的一些要素要么根本没有定型,要么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例如,“智力成果归创造它们的作者和发明人所有”这个前提,为如下两个问题留下了充分的解释空间:归作者和发明人所有的“东西”准确地讲究竟是什么?归作者和发明人“所有”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语境下,许多其他的观念或经济性力量塑造了“思想归我所有”的具体含义。而在其他语境中,官方的作者权观念就会与其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产生直接冲突。比如,“严格独创性”(strong originality)这个作为天才创造者标志的假设,既与对知识产权广泛可用性的经济需求相冲突,又与知识商品的价值只能由市场决定的当下新主流观念相矛盾。这种冲突导致了各种错综复杂、假设前提互相矛盾的思想观念,也催生了调和这些矛盾的机制。
20世纪之初出现的思想体系为知识财产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大致剖析如下:有一系列概念通过定义享有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所有者的基本特性,构建出创造者—所有者。还有一组理论则用来解释被拥有的客体是什么,它创造了一个适用法定权利的无形物概念。第三组相关理论则解释了拥有智力性客体这一观念的意义。这些理论界定了这种假设的无形物的所有者和他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