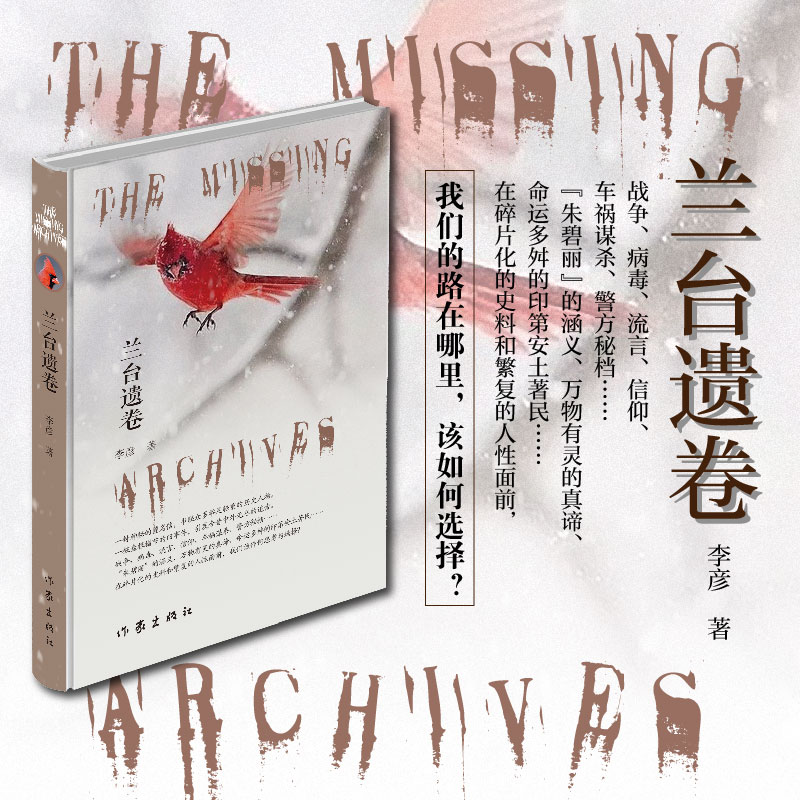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兰台遗卷
ISBN: 9787521217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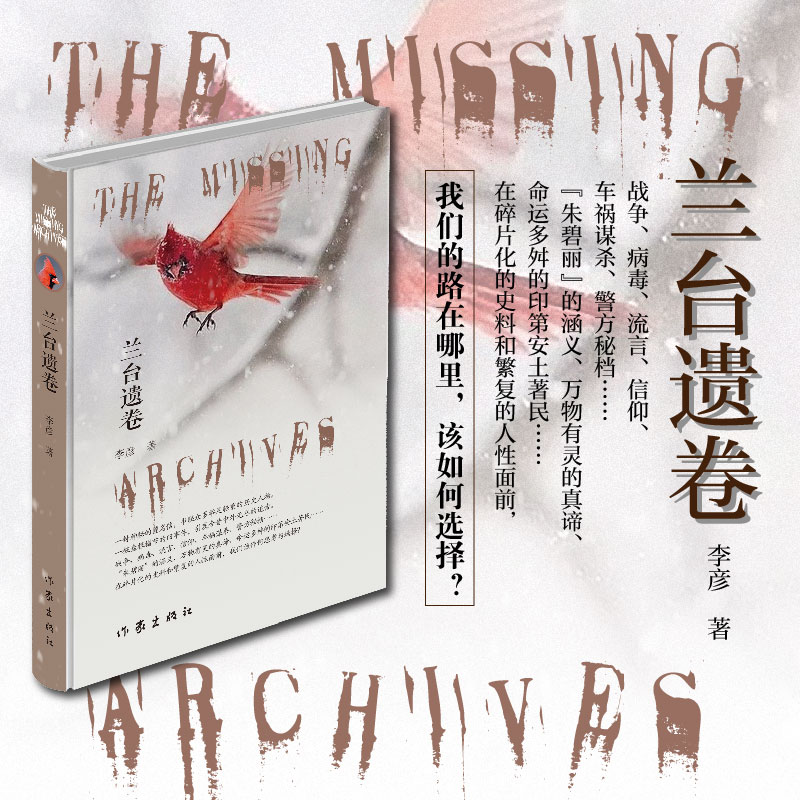
李彦,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执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兼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现为北京市侨联海外委员。 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
第一章?匿名信风波 1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兰草凋零,枫叶泛黄。一封匿名信,从天而降。 晚餐后,洗净锅碗,泡壶绿茶,端入卧室,我开启了电脑。邮箱里蹦出来的,是校长文笛的信。 “晚上好,彦!紧急求援。今收悉多伦多红衣主教转来的一封密函。此事关乎李添嫒牧师的声誉,异常棘手,甚至可能导致学校陷于尴尬困境!请阅读一下附件中的英文信并尽快将那份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知你本已超负荷工作,为此我深感不安。谨表谢忱。” 文笛校长是位白人女性,履任仅短短数月,我甚少与之交谈。见她虽寥寥数语,口气却异常紧迫,我便匆匆打开了附件。 跃入眼帘的,竟是一封用英文撰写的匿名举报信。长长的大标题,颇为骇人: 李添嫒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圣徒还是撒旦?抑或犹大转世?此女实乃披着羊皮的恶魔,公众却受其蒙骗,将她奉为圣徒,顶礼膜拜! 李添嫒?我脑中浮现出一幅油画肖像来。 学校图书馆的大厅宽敞明亮。在东北角那扇直通天花板的落地窗下,专门辟出了小小一隅,命名为“李添嫒牧师阅读角”。豆绿色的细碎格子布面沙发,配上淡黄的实木茶几,清清爽爽,赏心悦目,实乃静坐读书的好地方。 两面墙壁上,高高低低地悬挂了十多幅国画,山水花鸟,风采各异,中华格调浓郁。唯有一幅油画,却是人物肖像,一位已到暮年的华裔女性。她双颊的肌肉略显松弛,唇角含了一丝浅笑,近视镜片后的目光沉静安详,凝视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阅读角。 盯着荧光屏上那唬人的标题,我的思绪回溯到了多年前。 那时,学校突然间收到了一批画作,说是多伦多某位老华侨捐赠的。谁呢?直到那年秋天的校庆日,我才有幸一睹捐赠者的庐山真容。 一辆轿车停到教学楼的门口,众人搀扶着一位身量瘦小、着黑色衣裤的老太太下了车。只见迎接的人都毕恭毕敬,亲切地唤她为“季琼夫人”。 老太太拄一柄手杖,嘀嘀嘀敲着地面,步入了大厅,在众人簇拥下,她笑容满面,一一回应。我站在走廊里,也与她握了手。见我是华裔,她立即改用广东话和普通话,轮番寒暄。那种与其外表不相吻合的敏捷,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感谢季琼夫人的慷慨馈赠,校领导宣布,将为其过世的亡姊创建一个“李添嫒牧师阅读角”,以纪念这位全世界第一个被任命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女牧师的老人。 掌声中,在前排就座的季琼夫人伸出干枯的手掌,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方素白绸绢,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着布满皱纹的眼角。 季琼夫人离去后,学校公关处求我帮忙,把她所捐赠的这批国画上的中文全部翻译成英文,以备存档。 那时,我虽然讲授中国文化课已十多年了,却堪称画盲,仅仅耳闻过齐白石、徐悲鸿等几个丹青大师的名字而已。不消说,当我的目光扫过那一幅幅镜框,看到阮性山的干枝蜡梅、汪亚尘的彩墨池鱼、叶醉白的骏马奔腾、高逸鸿的雄鸡欢唱、屠古虹的巫山云雨时,便只是觉得赏心悦目罢了,却不懂妙在哪里,更不知画家们为何方神圣。 看着看着,眼前却豁然一亮。手下闪出来一幅画,上面的落款是“张大千”。这个名字,可算是耳熟能详了。 定睛细瞧,画面上倒没有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墨荷,仅有一位孤零零的老者,鹤发童颜,皂靴僧袍,伫立山巅。心下便琢磨,这是原作真迹,还是复制品呢?若是真迹,季琼夫人是何身份背景?怎舍得把如此名贵的藏品捐献出来呢? 接着翻看,竟然还有一幅,也是标着“张大千”,且都题了款,落了章。 暂且不论真伪,我将疑问列入备注,向公关处汇报之后,这两幅二尺大小、色彩黯淡、毫不起眼的“张大千”便被挑拣出来,郑重其事地悬挂在校长会议室里了。 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事变更频繁,校长们已经走马灯似的换过四茬了,可我发现,每当同事们聚在校长会议室里开会时,除了自己之外,竟再无其他人朝墙上那两幅画多瞥上一眼。 不由得就想,简单地归结为“对牛弹琴”“有眼不识泰山”,似乎有欠公允。一旦失去了吹喇叭抬轿子、哄抬炒作的商业环境,那么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品,便只能返璞归真,依赖人们对“美”的真实感受了。无人稀罕,也不奇怪。 一晃,八年光阴便流逝了。 在看到这封标题耸人听闻的匿名信之前,我在图书馆内查找资料时,曾多次从那幅油画肖像前走过,却甚少驻足,仔细端详一下这位华裔女性。并非她衰老的容颜不再吸引目光,只因我是个大陆来的新移民,对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知之甚少,更是从未听说过“李添嫒”的大名。 她究竟做了什么,竟被人描绘成“披着羊皮的恶魔”?我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匆匆阅读了这封英文匿名信。 李添嫒何许人也?她绝非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人士所吹捧出来的那个令人敬仰的女牧师。 何为真相?她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女人,是一条冻僵的蛇,被救活后,却反咬了那只给她喂食的手掌。 请阁下细读所附的中文资料,便知端倪,看清李添嫒是如何背叛了她的信仰、她的同仁,以及那个亲自授予她牧师头衔的何明华主教的。一句话,她背弃了天下所有人! 本人初抵北美,便惊愕地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系统竟然赋予了李添嫒如此殊荣,把她拔高到圣徒的地位,甚至以她来命名花卉、教堂、图书馆,外加多如牛毛的基金会! 那些人从未在中国见到过李添嫒,却煞费苦心地吹捧她,天晓得是出于何种动机?我所看到的种种迹象,都令我们这些了解她底细的人备感恶心! 李添嫒留下的那些文字中的口气,不仅卑鄙无耻,还亵渎神明。忠于信仰的人们义愤填膺,期盼着终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个时刻,要在全世界基督教会组织面前,纠正这一罄竹难书的巨大毁坏。 简言之,李添嫒这篇关于华南基督教会的文章,是为某情报机构搜集英、美帝国主义乃至台湾反革命政权的资料时所提供的。 换种说法,她把基督教会描绘成了破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间谍机构。何明华主教则被她描绘成双面间谍,故意与共产党友好交往,以便搜集情报。而教会帮助贫困人民改善生活所建立的各种扶贫项目,也统统都被她贴上了暗藏间谍组织的标签! 直到这些资料曝光之前,无人知晓她是一个如此恶毒的妇人。她背叛了自己的导师、信仰、教会以及朋友。 当绝大多数教会同仁在“文革”中遭受残酷折磨时,她却通过向红卫兵们通风报信,换取自身的安然无恙。 贵校的华裔人士可将李添嫒这篇文章译成英文,以供英文读者阅览。我已把该文复印后寄给了多位华裔牧师和基督徒,并将寄给美国和英国的教会组织。 这篇文史资料并非秘密文件,而是被收入了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中,并保存在广州市图书馆内。该当如何,请阁下自行判断! 一口气读完,心头被惊诧笼罩着,恨不能立刻揭开谜底,一窥究竟。想到老王还在电视机前等我,便匆忙起身,朝楼下喊了一声,嘱他不要再等了,随即反身回到卧室,关紧了房门。 案头的绿茶,已经变凉。捧起茶杯,我倚在窗台上,让头脑冷静片刻,再投入紧张的工作。 西边天际,橘红色的晚霞已经消退,残留着水墨画般的铅灰色条纹。 蓦地,一头小鹿从枫林后闪出。接着,一, 二, 三, 四,五……,一头接一头,紧随其后,踩着轻盈的步点,从湖畔的杂草丛中穿行而过,继而隐没在远方。 还是十几年前,一个盛夏的傍晚,我偶然间发现了一头身姿玲珑的小鹿,驻足湖旁,望着落满野蔷薇花瓣的水面,顾影自怜。老王悄悄拿起相机,留下了那个瞬间。 此后,年复一年,每当草木返青,小鹿的倩影便会重新出现。其队伍却在逐年壮大,由形单影只,变成结伴成双;由一家三口,到三五成群;直到眼下,竟已是大大小小八口之众,早已无法辨认出,谁是当初那头临流照影的小鹿了。 奇怪的是,无论鹿群多少次列队出行,它们经过我的窗前时,或悠闲漫步,或飞跃奔腾,却从来都是寂静无声,不闻其鸣。只是在我不经意间回眸一顾时,才会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暮色渐浓,视野里,仅余下一片朦胧的树丛,遥远的天幕上,闪烁着几颗星星。 有小鹿相伴的夜晚,温馨恬静。笔走龙蛇,乐在其中。 一封神秘的匿名信,串联众多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一桩盘根错节的旧事件,引发今昔中外无尽的追索。 战争、病毒、流言、信仰、车祸谋杀、警方秘档…… “朱碧丽”的涵义、万物有灵的真谛、命运多舛的印第安土著民…… 在碎片化的史料和繁复的人性面前,我们该作何思考与选择? 打开书,从那封漂洋过海的匿名信开始,阅读便成了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事情。地铁里、马桶上、书桌旁、枕头边……只想吃喝让路,休眠靠边,快快解开那一连串的疑窦与谜团。 走进《兰台遗卷》,当一回“福尔摩斯”,跟着书中的文字,在支离破碎的残片里修补、拼接、勾连……阅一个个曾经鲜活却陌生的生命,读一段段被遮蔽或裁切的历史,照一面镜子。 历史的“海滩”潮涨潮落,曾经的人与事,或被留存,或被掩埋,或已彻底消弭。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所经历的究竟应是怎样的历史?随着《兰台遗卷》的文字,一步步地阅读,一程程地思考、分析,你会有很多意外又惊诧的发现和收获。 了解历史,需要“读”,也需要“辨”和“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