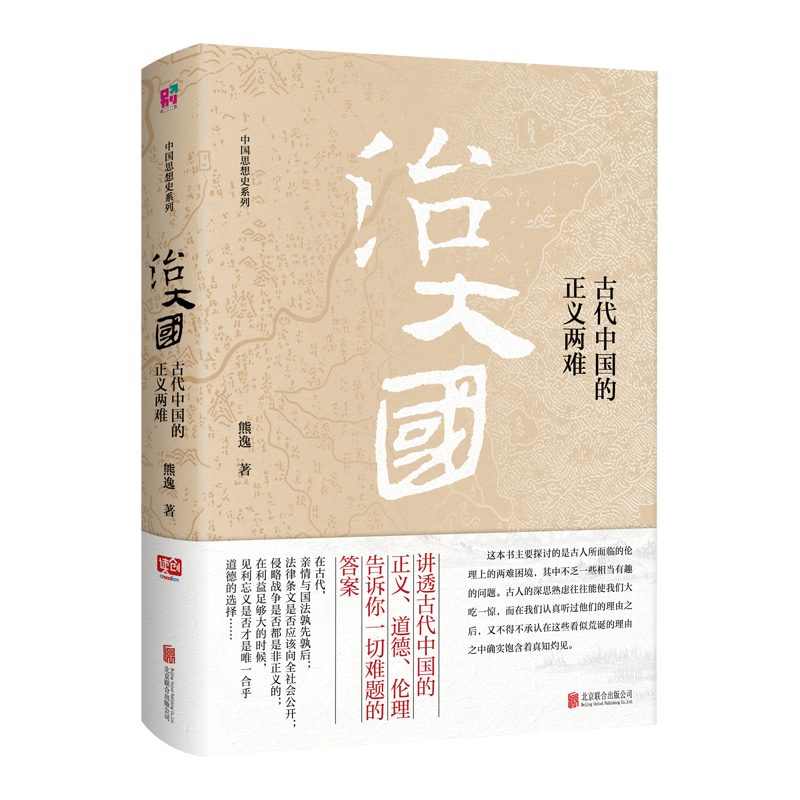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8.10
折扣购买: 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ISBN: 9787559638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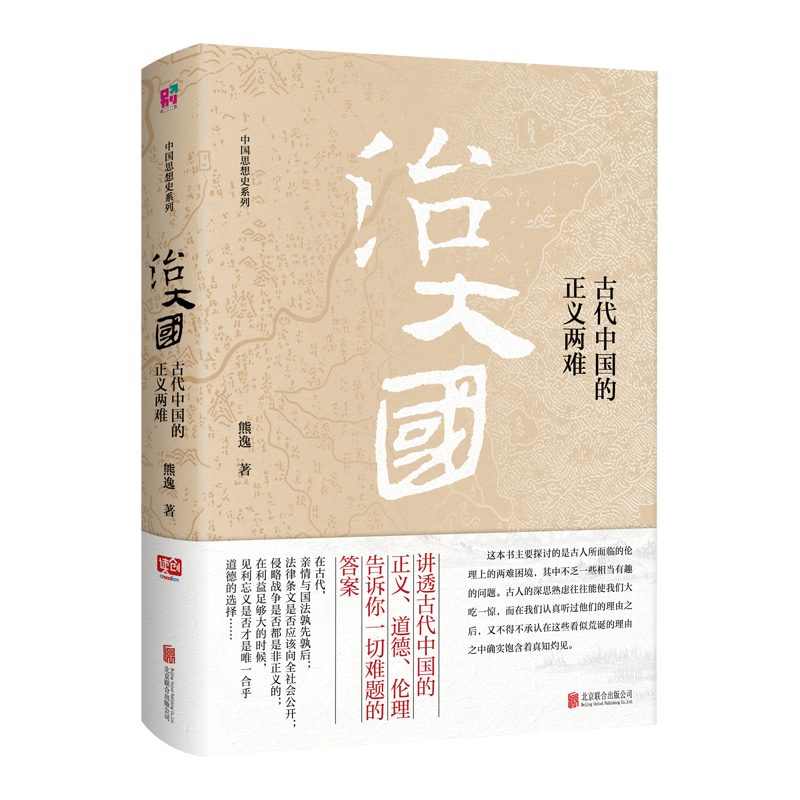
"熊逸 中国当代一位重要的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
\"第一章 圣天子的违法逃亡 1 苏轼讲过,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起自孟子。孟子以性善立论,仿佛变成了一只靶子,不管谁看见他都想拉弓射上一箭。(《子思论》,《苏轼文集》卷三)当然,孟子有着和他的勇气颇相称的口才,所以不那么容易被人射中要害。 在先秦诸子当中,最善辩的人恐怕非孟子莫属了。在他迎击过的所有箭矢里边,我以为最刁钻的一支并非出自任何一名论敌之手,却是他的学生桃应射过来的。 桃应的箭矢是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儒家传统里,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理想型的坏分子。瞽瞍和那个同样卑鄙恶劣却占有自己的全部父爱的小儿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安排毒计,大有不把舜害死誓不罢休的势头。尽管瞽瞍是一个坏到令人发指且坏得完全不可思议的父亲,舜却始终是一个无怨无艾、一心尽孝的好儿子。那么,对桃应的问题我们便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坏父亲杀了人,应该怎样处理才是对的? 对这个貌似需要长篇大论来反复论证的问题,孟子只给了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回答:“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仿佛在孟子看来,桃应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在孟子的直截简略面前,桃应不免错愕,于是追问道:“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这个追问看来正在孟子的意料之中,而孟子继续给出了一个直截简略得近乎过分的回答:“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更加困惑了:“难道舜就这样任由父亲被捕不成?”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儒家认为国家法理是家族伦理的自然拓展,孝道处于毋庸置疑的核心位置。桃应的问题便关乎法理,其言下之意是,舜如果听任父亲被捕服法,作为儿子显然有违孝道,那么以儒家的标准来看就很不合适了。 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言之,对于此时的大舜而言,天子的身份与儿子的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桃应问题的刁钻之处正在于此,而孟子自然晓得其中的关键,所以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天下。”1 2 我们有必要把孟子的意见做一番粗略的整理:天子的父亲杀人,在这件事上,完美法官和完美天子分别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法官的行为标准是正常执法,绝不因违法者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天子的行为标准则有两条: (1)作为天子,履行天子职责,不去阻挠正常执法,听任父亲接受最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裁。 (2)作为儿子,偷偷把父亲救走,一同逃离国境,在避世隐居中尽孝道以享天伦之乐。 “逃离国境”在这里是有显著意义的,它既意味着主动放弃天子的职务,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子民的身份。于是,大舜对于他原先治理过的天下而言,既无天子之责,亦无臣民之义,而唯一余下的责任关系就是父子之道。这也就意味着,在孟子的理想规范里,血缘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家庭亲情优先于社会责任。明代学者马明衡言简意赅地归结过这个道理:“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尚书疑义》卷一) 孟子的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条主要原则: (1)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 (2)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孟子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么,假如在瞽瞍杀人案中,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孟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应付裕如呢? 3 《搜神记》是一部奇特的书,书中的内容尽管充斥着看似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作者干宝却显然是以严肃的史家姿态加以撰述的。在他看来,书中的这些事情哪怕再如何离奇古怪,读者都不应该以奇谈视之。所以,对于以下这则超乎常理的故事,至少干宝本人是笃信不疑的: 嘉兴有一个叫徐泰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叔父徐隗将他抚养成人,待他比待亲生儿子还好。后来叔父生了病,徐泰很尽心地照料他。一天晚上,徐泰梦见两个人乘船而来,走上自己的床头,然后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本簿子对自己说:“你叔父的死期到了。”徐泰在梦里连连向这两人叩头哀求,后者终于心生恻隐,便问他道:“这县里面还有没有和你叔父同名同姓的人?”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自然知道这两个人要做什么:徐隗固然难逃一死,但可以找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代他死。也就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将一个名叫徐隗的人带到阴司,至于这个人究竟是此徐隗抑或彼徐隗,那倒完全可以通融。这就等于抛给了徐泰一个道德难题:叔父当然是最亲的亲人,但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来挽救叔父,可以这样做吗? 最后亲情战胜了一切。故事的后文是,徐泰确实想找这样一个替死鬼出来,却实在想不出本县还有谁和叔父同名同姓,搜肠刮肚之下,只想到有一个叫张隗的,与叔父同名而不同姓。那两个人答道:“这也可以,姓名差不多就行。念在你苦心侍奉叔父的分上,我们就成全你的孝心。”言讫,两人消失不见,待徐泰醒来,叔父的疾病果然痊愈了。(《搜神记》卷十) 从故事讲述者的态度来看,徐隗、徐泰这两叔侄的感情是最令人动容的。他们虽然不是父子关系,但徐隗待徐泰如亲子,徐泰也事徐隗如生父。故事的讲述者显然相当赞同这种伦理关系,对孝道的认同超越了血缘局限。于是,讲述者的难题就是怎样处理那个张隗的结局——如果在表彰徐泰之孝道的同时加给他一个枉杀无辜的罪名,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索性就避而不谈好了。读者当然晓得张隗肯定是做了徐隗的替死鬼,但故事毕竟不曾明白地交代这一点。看来,在故事讲述者的道德权衡里,虽然认为徐泰枉杀张隗的做法不甚妥当,但终于还是褒扬其大体而不去深究细节了。 倘若我们给这则故事增添一点内容:假设张隗也有一个事亲至孝的儿子,其人还清楚知道了父亲的死因,他又该何去何从呢?——遗憾的是,在瞽瞍案件中被孟子回避的那个问题在《搜神记》里同样地被回避了。\" \"中国当代思想隐士 熊逸 中国思想史系列 罗辑思维创始人 罗振宇赞赏推荐 讲透古代中国的正义、道德、伦理 告诉你一切难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