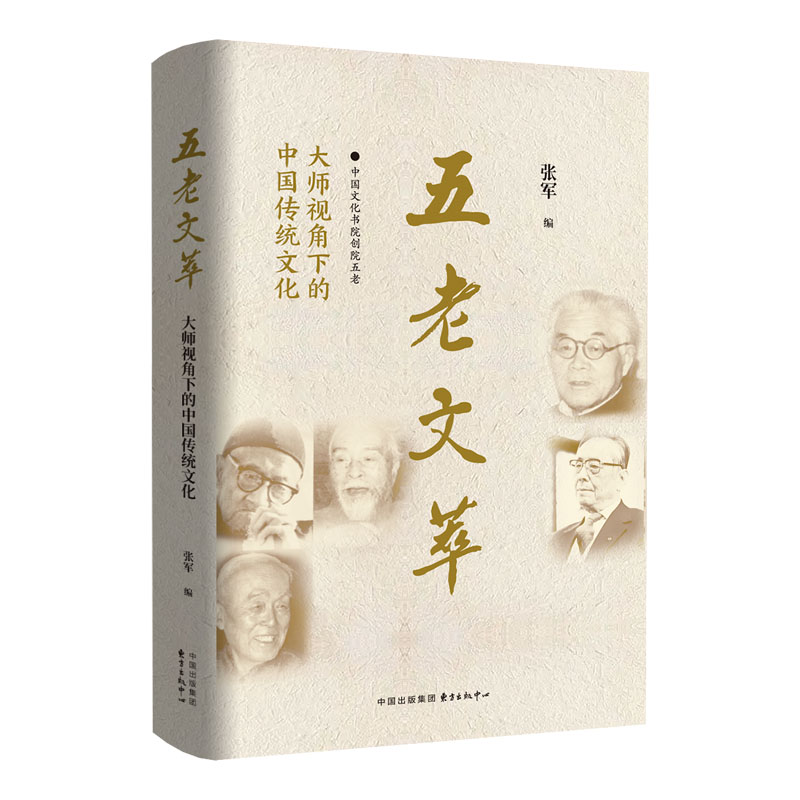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120.00
折扣价: 82.58
折扣购买: 五老文萃
ISBN: 9787547326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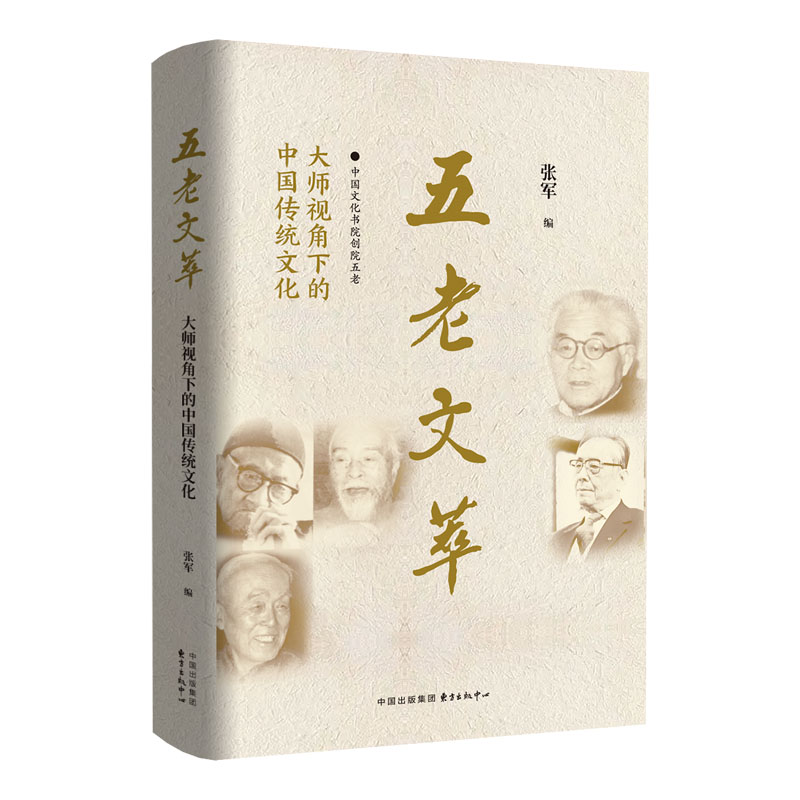
张军,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先后任职于世行图书贷款办、教育部图书转款办、北大图书馆文献部等,2001年至今先后任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
导语? 一生不忘——读梁漱溟先生 王守常 中国文化书院于 1984 年 10 月在北京成立,至今四十年了。各位同仁一致赞成对中国文化书院这四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或走过的弯路进行认真的思考,以便让中国文化书院不负前辈学者的嘱托: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所作出的贡献,在此我对梁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微言隐义,刚介直言。他思考不拘一格,既传统且现代。他行走于官僚政客间,不为献媚,而为农村建设与教育。 我以梁先生《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乡村建设理论》等五本著作为核心,重点选取了梁先生佛学、儒学、乡村建设理论以及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方面的文章。因篇幅有限,所选文章可能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有识之士如有所需,可从《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中读到更完整的内容,从而对梁先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梁漱溟先生于 1893 年生于北京,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清光绪十九年。1942 年,梁漱溟先生应桂林《自学》月刊之约,开始写他的《我的自学小史》之前部分。他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大的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这一次中日大战就是指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抗日战争。其实,影响梁漱溟先生前半生思想轨迹的除了两场战争,还有先生早年受其父梁济的言行举止之影响很大。他曾描述过:父亲和母亲一样天生忠厚,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苦寒生活之中。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先生还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还有父亲“不主张儿童读经”,这在当时是一破例的事。梁济先生这样教育儿子是有他对世界的理解的。他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在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1860 年(咸丰十年),英法入侵天津,清帝避走热河。1884 年(光绪十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占领青岛。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国外列强凌辱,国内清廷衰败,一幅山河破碎的景象。这让梁济先生倾向变法维新,他在日记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梁济先生向西学求法维新,也要求年幼的梁漱溟求学西方,自学成人。我们从梁济先生日记中的言语可以知道,梁漱溟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与生活中的价值趋向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 1918 年农历十月初七,梁济先生选择投湖自尽,留下万言遗书。他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当时有人评述,说他认为清王朝将亡,是所殉的殇文化说。这一说法显然浅析之说,只看到表面之现象,完全没有理解梁济先生作为“士君子”的追求。立节操才是“士君子”所为! 1981 年,梁漱溟先生在《王国维先生当年为何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实情》一文中说:“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梁漱溟先生说的是,其父与静安先生都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却又处这无道之世,改变这一风雨飘摇的世界则又不能,唯有坚持“士君子”之操也。 哪里可以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与方法?梁漱溟先生从小学到中学那段时间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他曾经回忆道,先父有他自己的思想,以为这样是对,那样则是不对。有些实用主义趋向,但他倾向维新者,实则他感情真挚,关切国事。梁漱溟先生认为自己的性情与脾气颇多相似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 梁漱溟先生说他在 20 岁以后变化极大,俨若两人。这在他当初实不及料。先生之说,我以为还有另一番隐语。这是他受其先父性格之影响,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的意愿,只要他自己认真思考过,且努力实践过,那么他认为可行的事情,就会“固执”地坚持。先生后半生,50 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不就是这样度过的吗?具体可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953 年至 1988 年散篇论述)和《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记录整理的,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 2015 年出版。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论说,都不尽相同。先生于 1988 年过世,也有近半个世纪了。我记得 1985 年 4、5 月间,中国文化书院还在筹备期间,汤一介先生就邀请梁漱溟先生加入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那时候我不到 40 岁,任副主席。书院平时的工作由我负责,重要的事情要向梁漱溟先生汇报。当然,也要向院长汤一介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报告。我第一次见梁先生时,他和我读其书时的印象完全一致。不苟言笑,有点木讷。有本书说:木讷者,及当大事,毅然执持,人不能夺。先生坚持不已,不仅是其外在的表现,更是他内在信念、价值观的持续追求与坚守。梁先生有一张照片,后来很多出版社的书籍及刊物的封面都用这张照片,我每每看这张照片都莫名感动!梁漱溟先生那专注的眼神和紧闭的嘴唇不是愤怒,也不是怜悯,而是他内心的坚毅和永不放弃的精神表达!我曾说过,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能找到回家路的“大先生”! 梁漱溟先生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会愈加深刻地认识与理解他。殊不知,在不同历史时间中,社会似乎“发生的变化和以前历史思想的遗迹”应该“有些不一样的理解了”。我在上面这段话中两次用了引号。梁漱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是用类似语气词及符号表达他的思想。如“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梁漱溟先生还有类似的表达,“我的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也把它贡献给别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在思想的浩瀚星空中,梁漱溟以对社会文化的深刻省思,带您探寻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路径;冯友兰用其清晰的哲学思辨,为您开启中国古典智慧的神秘大门;张岱年凭借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梳理,展现民族精神的丰富宝藏;季羡林以跨文化的多彩经历,编织出一幅绚丽的人文画卷;任继愈则通过对宗教与哲学等领域的深度解读,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幽微角落。本书汇聚这五位大师的经典选文,文字深入浅出,如涓涓细流润泽心灵。无论您是渴望提升文化素养的求知者,还是对人生哲理有所追寻的思索者,都能在这些文字中领略大师风采,汲取无尽的智慧养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启迪心智的文化之旅,感受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