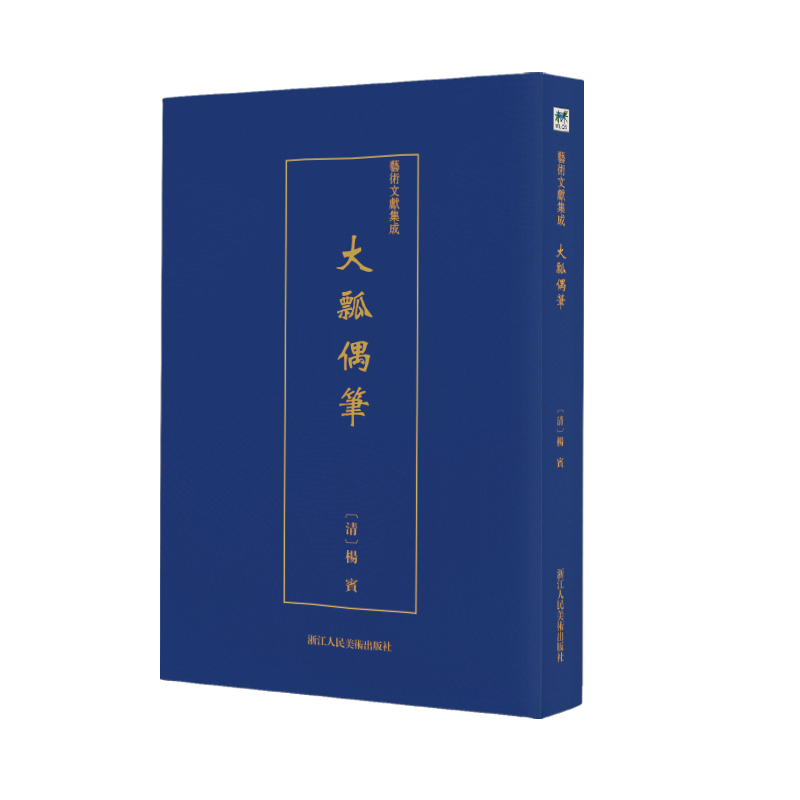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美
原售价: 59.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大瓢偶笔/艺术文献集成
ISBN: 9787534074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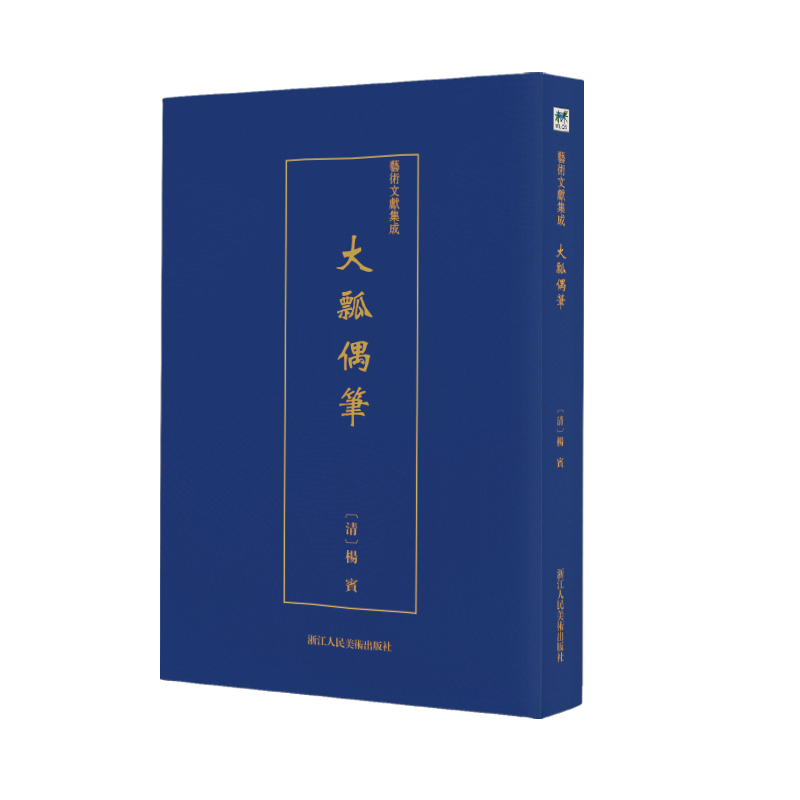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大瓢、耕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顺治七年,卒于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十七年(1678)侨寓吴门,巡抚举应“博学鸿儒”科,力辞去。杨宾侍父戍所时,习其地理沿革,出川道里、风土人情,著《柳边纪略》,为世所称。另著有《塞外诗》三卷、《大瓢偶笔》八卷、《杂文》一卷及《力耕堂诗稿》等。
大瓢偶笔自序 尝闻欧阳率*好书古事,永叔好书今事,黄山谷好书禅伯句,秦少游好书山鬼句,东坡与高宗好书佛经。今世则大抵书古人诗。 余独不然,往往书金石事。譬诸织者以布帛衣,不必别求旃裘也;耕者以稻粱食,不必别求鱼肉也;陶者以土甑爨,以瓦盆饮,不必别求金与玉也。所谓取诸宫中而用之,可乎,不可乎? 夫古事与今事,书之可也。佛经也,僧诗也,鬼诗也,而书之,不几舍布帛而衣牛衣,舍稻粱而食藜藿乎! 虽然,传不传在书,而不在其所书。衣牛衣,衣布帛,等衣耳,煖而已;食藜藿,食稻粱,等食耳,饱而已。然则余之书金石者,犹之书古事,书今事,书佛经与僧鬼诗也。取诸宫中而用之者,偶然耳。 积之既久,子侄辈録而存之,得若干卷,名之曰《偶笔》,而书于其端。 康熙四十七年八月 大瓢偶笔卷一夏周秦汉三国六朝碑帖 大禹岣嵝碑 大禹《岣嵝碑》,在衡山岣嵝峰。岳麓所刻者,宋嘉定间何致子一所摹,在岳麓山巅石壁间,有亭覆之。石东北向,高七尺,广两之,若屏然,而亚其两角,刻文于中,空其前后。拓墨处独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实则一石也。余于康熙戊子春,从岳麓书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庸、极高明亭往观之。亭外西北隅有磨厓古刻三行,大如斗,类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书二行,俱不可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书,不足观也。 会稽山禹陵窆石 会稽山禹陵窆石,本无字。汉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题字于石,石在禹庙东南小阜。高五尺许,下大可合抱,而上微鋭,鋭处有一孔,形若秤锤,故土人呼之爲石秤锤。予幼时,见其孔若断而复续者。朱竹垞曰:‘相传千夫不能撼。岁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石中断,部下健儿迭相助,及拔,陷地纔数寸尔。土人涂以漆,仍立故处,覆以亭。’ 杨霈按:《曝书亭集》云:‘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盖在用碑之前,碑有铭而窆无铭。验其文,乃东汉遗字。’王复斋《碑録》定爲汉刻,是矣。赵氏《金石録目》曰‘窆石铭’,误。 连江石鼓文 连江《石鼓文》,明时吴襄惠公文华,得拓本于杨用修,用修得之李西涯,相传爲苏子瞻藏本。康熙初,襄惠后人吴子钧,属李登、陈延之、欧阳惟礼篆而刻之木,与国学陈仓本不同。竹垞云西涯僞作。 杨霈按:韩文公《石鼓歌》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杜少陵云:‘陈仓石鼓久已讹。’韦苏州云:‘风雨缺讹苔藓。’则石鼓唐时已无全文。《集古録》:‘欧阳公所见,止四百六十五字。’近时阮芸台相国,取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重刻于杭州府学,亦止四百六十二字。元人吾子行自谓,以《甲秀堂谱图》随鼓形补缺字,列钱爲文,以求章句。又参以薛尚功诸作,亦仅得四百三十余字。而升庵所拓,乃至七百有二字之多,朱竹垞辨其妄自改增,可无疑矣。据升庵,谓得之李西涯,传之苏子瞻。竹垞谓:果尔,则子瞻应先见其全,子由亦得纵观。何以子瞻之诗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糊模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字形汗漫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是子瞻、子由均不应有是言。又西涯《石鼓歌》云:‘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盈握。拾残补缺能几何,以一涓埃禆海岳。’夫以欧阳、薛、胡诸家所见,止四百余字,若宾之本有七百余字,拾残补缺,亦已多矣,宾之亦不应爲是言也。观此,则竹垞非疑西涯僞作,直指升庵僞作耳。间考李文正《怀麓堂集》,絶不道及,其爲升庵僞作可知。 《日下旧闻》载:赋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温、李丙奎。作诗歌者二十人,曰韦应物、韩愈、张耒、洪适、梅尧臣、苏轼、苏辙、张养浩、揭傒斯、宋褧、吴莱、顾文昭、卢原质、唐之淳、程敏政、李东阳、何景明、王家屏、朱国祚、郭天中。 会稽山碑 《会稽山碑》,旧传李斯篆,在鹅鼻山。近见明南逢吉《会稽三赋注》云:‘宋升明,本县民家儿,袭祖行猎。见山上有文三处,苔生其上,刮而视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云:“黄天皇肃字道成得贤师天下。”’似与秦碑不同。 杨霈按:孙渊如《寰宇访碑録》:‘会稽石刻,二世元年李斯篆书,在浙江会稽。’元申屠駉摹本,近时所刻。又范氏《天一阁书目·史部》:‘《会稽三赋》一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嘉靖二年南大吉序,原钞本,误作《会稽山赋》。’ 秦东门三字 ‘秦东门’三字,相传丞相斯书,刻海州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数年不得,亡弟楚萍于无意中忽见之,明日再往,复失所在。 汉荆州刺史度尚碑 《汉荆州刺史度尚碑》,相传初在北陵东郊,缺裂仆地,大水至,冲入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徙于使星亭,不知何时徙沛县湖陵城牐下。明顾崇善工部出理漕渠,徙置徐州官廨。吴文定公云:‘残缺已甚,独额完,有宋人题识。’ 杨霈按:娄彦发《汉隶字源·碑目》第六十三:‘《荆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立,在徐州湖陵荒野。政和壬辰,巡检王当世迁于官廨,刘宗仪立之使星亭。’所记与此不同。 介休郭有道碑 介休《郭有道碑》,中郎隶书,旧石相传爲一秀才盗去。介休令重刻,以应求者。赵子函曰:‘盩厔王正己再刻。’王阮亭《秦蜀后记》又云:‘万历中,郭青螺钩摹重刻。’夫子函,正万历时人。如果青螺重刻,《石墨镌华》何以不言?青螺而言正己,岂刻者正己,而青螺爲之主耶?抑子函、阮亭所传,有一误耶?或又云:墓前今有二碑,一爲明人翻刻,一爲康熙初白门郑谷口所临。余足迹所未至,无从考证。敢问世之往来于介休者。 杨霈按:范氏《天一阁碑目》载:‘《郭有道碑》,康熙三十一年介休令王直重摹,郭青螺重刻。’《郭林宗碑》自跋云:‘介休王尹正己访于汾故家,得旧碑示予,予近过许昌,摹魏《受禅文》,参之斯碑,字体画一,其出蔡手无疑。王乃命工镌之贞珉。’据此,则刻者正己,而主之者青螺,王、赵所传,均无误也。周武帝时,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诏特留。乃此碑自宋以来,着録家皆未之及,知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林宗墓前二碑:一爲明人傅山刻,字迹丑恶,殊昧古意。原跋称,碑在南渡前已不可见。吾从汾阳曹孝廉伟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补书,陋甚。其一爲国初郑簠所书,皆不足观。翁覃谿云:‘家藏别有姜任修本,较傅、郑二刻颇有根据。’姜自识云:‘予从寒山赵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孙氏所藏《石经》残碑,得中郎笔法,以吴炳补《桐柏碑》之例重补此碑。或比近人傅、郑二家杜撰者差胜云。’ 蔡中郎隶书圣主得贤臣颂 陶丘谓余曰:‘汉阳故相吴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隶书《圣主得贤臣颂》四十余字,书网纸上。后皆帝王跋,自吴大帝,至晋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于宋徽宗。’此奇宝也,予又乌从见之。 本书多是论书法之文,兼有评议,笔墨简练,趣味盎然,乃是书法艺术之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