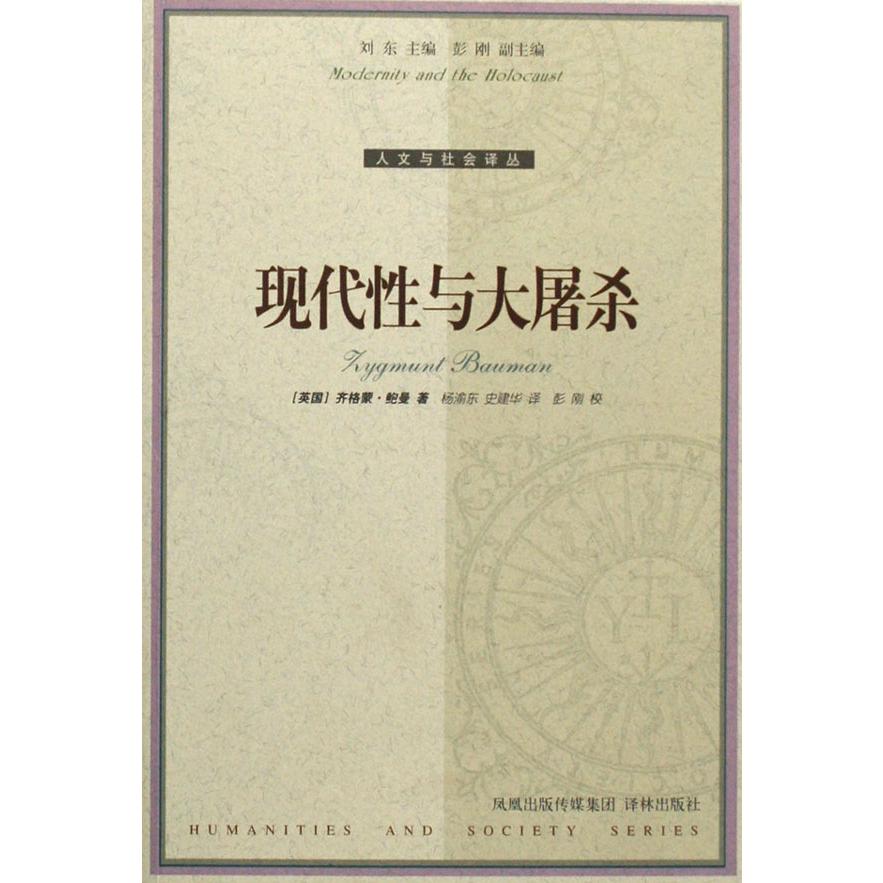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17.00
折扣价: 13.00
折扣购买: 现代性与大屠杀/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7806573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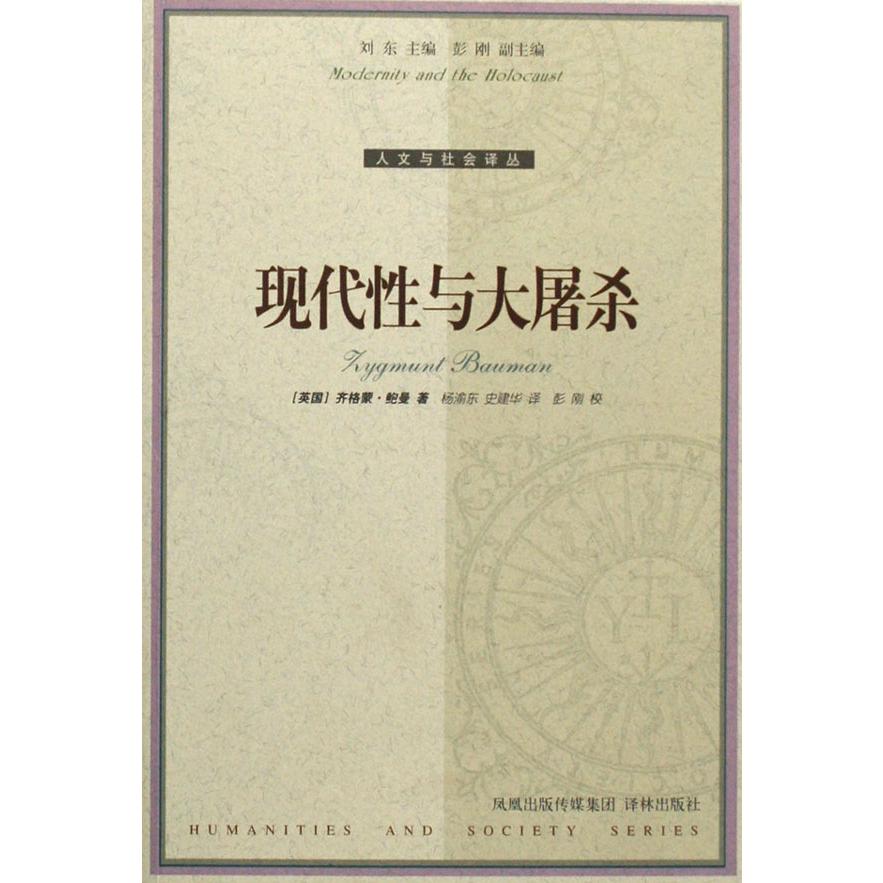
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78)、《阶级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及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尽管文明化进程的其他社会学形象也触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广泛认 可)的还是这样一种观点:它的两个核心是对非理性以及本质上反社会的驱 力的压制,和从社会生活中逐渐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在 国家的控制之下将暴力集中。在国家当中暴力就被用来守护民族共同体的边 界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将两个中心点糅合成一点的就是文明社会观— —至少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和现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会看做一 种道德力量,看做一种在施加规范性秩序和法制当中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 制度体系,而秩序和法制维护了社会和平与个人安全的状况,在前文明化的 环境中它们受到的保护是很糟糕的。 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产生误导,但对大屠杀来说,它必然只能看到一个 方面。当它想要仔细审视近代历史的重要趋势时,却早早地关上了讨论同样 关键的倾向的大门。它把目光集中于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武断地在正常与 异常之间划出界限。它通过废除文明中一些具有回复性的因素,错误地认为 它们是偶然的和转瞬即逝的,这也就同时掩盖了这些因素的特质中最显著的 方面与现代性的规范性假设所具有的惊人的共鸣之处。换句话来说,它使人 们不再注意文明化进程另一面的、具有破坏性的潜能的展示,并且有效地把 那些坚持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双面性的批评家推向了沉默和边缘。 我认为,大屠杀的主要教训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 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 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 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 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 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 ,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 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置身事后,我们再读韦伯时就会发现韦伯对于理性化的条件和机制的阐 述揭示了那些重要却被远远低估了的联系。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商业 理性行为的条件——比如像人所皆知的家庭和企业的分离,或私人收入和公 共财产的分离——共同作为有力的因素在使目的取向的理性行为避免与受其 他(根据定义是非理性的)规范控制的过程发生交换中发挥功用,进而使理性 行为不受一些在非商业形式中站得住脚的互相帮助、团结、相互尊重等假设 的束缚性作用的影响。在现代官僚体系里,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 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做一次回顾性的重新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使 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主要的关怀;准确一点,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 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当它追求以完美的理性方式来解决日常问题的 时候,也显示出能够产生大屠杀式解决方式的能力。 沿着上述线索对文明化进程理论的任何重写都必定会包括社会学本身的 某种变化。社会学的特性和风格已经被调试得和被它理论化、被它研究的现 代社会本身一模一样;社会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致力于与它的研究对象保持 一种模仿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对象的形象保持模仿的关系, 它把这副形象建构和接受为使它的话语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社会学把被想 像为其研究对象构成成分的理性行动原则提升为说明自身合理性的标准。它 也将不能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道德问题提升为自身话语的限定性规则,当然 除了那些在公共享有的意识形态中出现的、并由此与社会学的(科学的、理 性的)话语不相融的道德问题。诸如“人类生活的圣洁”或者“道德责任” 之类的话在社会学研讨会上听起来很怪异,如同它们出现在一个无烟的、经 过卫生处理的官僚机构办公室里一样。 P37-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