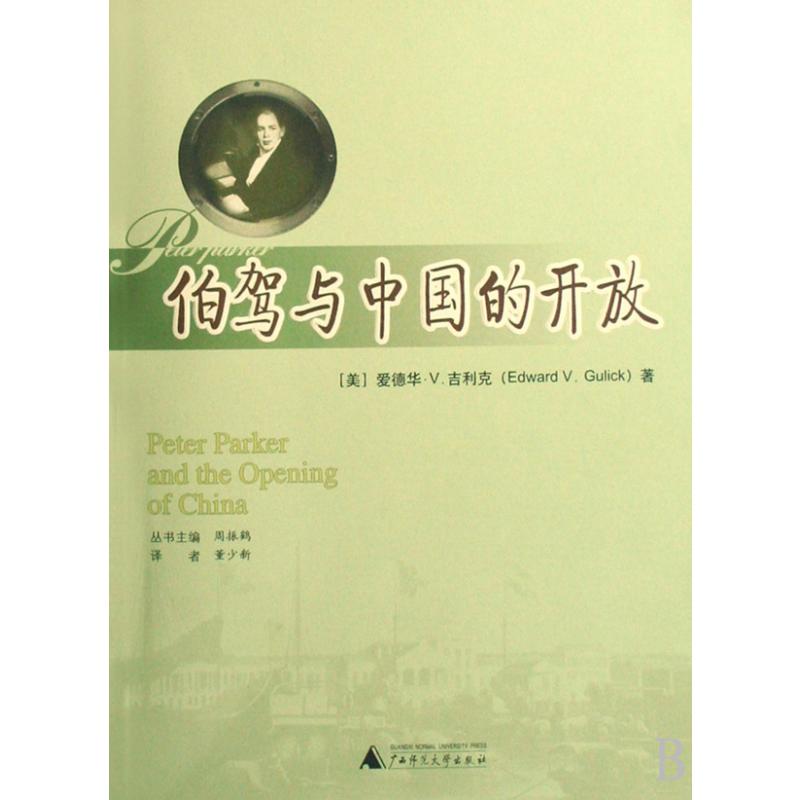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伯驾与中国的开放/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
ISBN: 9787563377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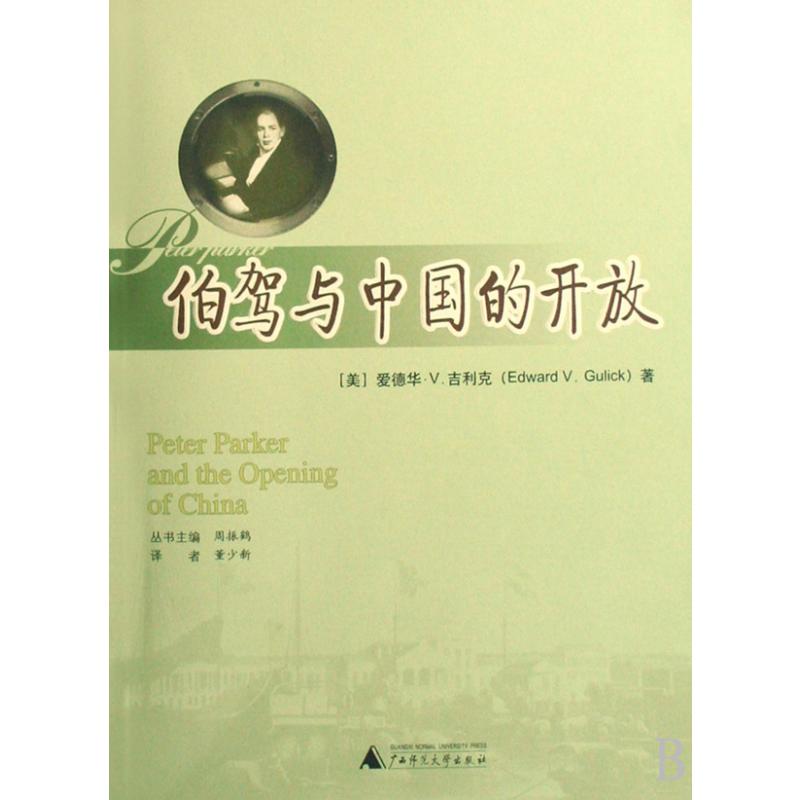
爱德华·吉利克,韦尔兹利学院教授、历史学家,曾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任教,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独到的研究。 董少新,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2001—2003年游学于葡萄牙里斯本,2004年获得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随后曾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2005—2007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任职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目前正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做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主要为16—19世纪东西方交往史,已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周振鹤,生于1941年,福建厦门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等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11月初,裨治文带伯驾参观了种痘局。中国痘师彬彬有礼且专心致志 。那里聚集着100多位中国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其中有两打以上的孩子 是来接种的,而其他孩子则是来提供痘苗的。种牛痘的工作是东印度公司 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于1805年在澳门开始开展的,而广州这个 种痘局是皮尔逊医生种痘事业的一部分。伯驾被告知,中国官员通过给接 种成功者提供奖金的方式来支持此项工作。他观察到,对前来接种者,该 局进行系统的登记,局中约有12名痘师正在采苗和为人接种。 尽管伯驾以前曾经治疗过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瑞典人、果阿人、孟 买人及马六甲人,也给一位在美国馆做工的中国人诊断过、开过药方,但 是直到11月中旬,伯驾才第一次为一名与广州外国社群毫无干系的中国人 治病——一名10岁的男孩由其父亲带到了伯驾面前,裨治文和他的一个学 生充当翻译,伯驾给男孩做了检查和诊断,并开了药方。他还治疗了美国 馆的一个买办,后来又间接地治疗了一名妇女;给这位妇女治病时,他不 得不在没有见到她的情况下为其开药方。 伯驾很快便过上了这种一边学习语言一边进行少量医疗活动的愉快生 活,而且这样的生活本可以持续整个冬天并有可能延续下去,但是挑剔的 、使人不安的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博士的出现打破 了这一切。在1834年,郭士立是中国沿海经验最为丰富的新教传教士。他 出生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是一个好斗的业余语言学家,也是一个闻 名一时的职业传教士。1824年他曾受荷兰传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的派遣前往暹罗传教。他掌握了福建话后,便离开了那里,乘船 在中国沿海进行了一系列旅行。他将澳门作为基地,偶尔也前来广州。他 这次来到广州时,遇到了伯驾。郭士立视中国人为半野蛮的偶像崇拜者; 而中国人则视他为恃强凌弱的野蛮人。在伯驾看来,郭士立性格怪僻,我 行我素,常让人莫名其妙,且有些不正常。 郭士立一见伯驾,便立刻建议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命令他前往新加 坡,在那里他可以与一个福建人社群接触,他可以自由地混迹于其中,学 习福建方言,为即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开辟的传教事业进行语言方面的必要 准备。作为传教区域,广州在当时是最没有前途的;裨治文在那里已经五 年了,也没见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皈依了上帝。 11月末,伯驾患了一次严重的痢疾,这种疾病每年都会定期在那里的 外国人中流行。疾病之苦加上郭士立的鼓动,伯驾有些动摇了。如果继续 留在广州,他可以学习官话,并开一间眼科诊疗所,但新加坡正需要医务 人员,而且在那里可以自由传教。在伯驾、裨治文、卫三畏和奥立芬都参 加了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伯驾前往新加坡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精 心的权衡。 语言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官方文书用文言文(与我们难懂的古英语类似 )书写。广州的方言是广东话,但若其他省份向传教开放后,即便学会了广 东话在那些省份也派不上用场。从东至东北方向的沿海地区在不久的将来 基督教最有可能渗透进去,可这些地区的人民相互之间都无法用本地语言 交流,那些方言在中央帝国的任何其他较大的区域都无法使用。要想与大 多数中国人进行交流,就只能掌握官话。但按照1834年的传教观点来看, 官话适用于中国中部、华北平原地区和北京,而在当时能够预见的未来中 ,基督教还无法渗透到那里去。在广州保障一名汉语老师的安全都是一个 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官府禁止中国人给外国人当老师;此外,在广州找 个中国人练习说中国话都不容易。而且,在广州到底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医 务工作上,这一问题仍困扰着伯驾。经过一番痛苦的重新考虑,他们决定 接受郭士立的提议,让伯驾于1834年12月6日乘船赴新加坡,并计划于4月 或5月返回广州。 起先,新加坡似乎非常吸引伯驾。他于圣诞节的前一天到达那里,花 园中充满了花香,庄重的建筑物上英国国旗在随风飘扬,马车在宽敞的大 街上穿行。伯驾先在美部会传教士特雷西(Ira Tracy)的住处安顿下来,不 久又搬进了以“马礼逊屋”(Morrison House)为名的建筑中。这是马礼逊 博士后继者们的房子,地处华人社区的中心,而远离任何欧洲人的社区。 就像伯驾所期望的那样,一来到这里他就忙于参加各种教会工作、各 类集会和祷告会,并在其中的一些聚会上布道。伯驾有时也到主教座堂服 务,但主要精力用在参加特雷西先生的一个中国教徒群体的活动,该教徒 组织对他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的教会组织在广州那样隔离的条件下是不 可能存在的。 在向中国人传教方面,伯驾的能力尚有所欠缺。因此,语言学习须要 立刻进行,他请了私人老师兼翻译,每月10美金。开始时他每天学习的是 福建话——一种福建移民社区的语言。由于这位老师不会书写,所以伯驾 的语言学习仅限于汉语口语。 伯驾也开始接待病人了,并希望每天的行医活动限制在一个可以掌控 的小范围内。每天刚出太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给病人看病。他也 将一些病人带到家中,以便提供不间断的照料。他的行医活动逐渐多起来 ,每天黎明时分病人便聚集到他的门前,伯驾医生给他们看病,通常要一 直忙到中午,有时连早餐和做早礼拜的时问都没有。晚上的时候,他也经 常被叫去给病人看病。伯驾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很受病人的欢迎。他也 很坦诚地记录了几个病人病死的事情。医疗工作占用着他越来越多的时间 ,他逐渐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语言了,这使他有些焦虑不安。P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