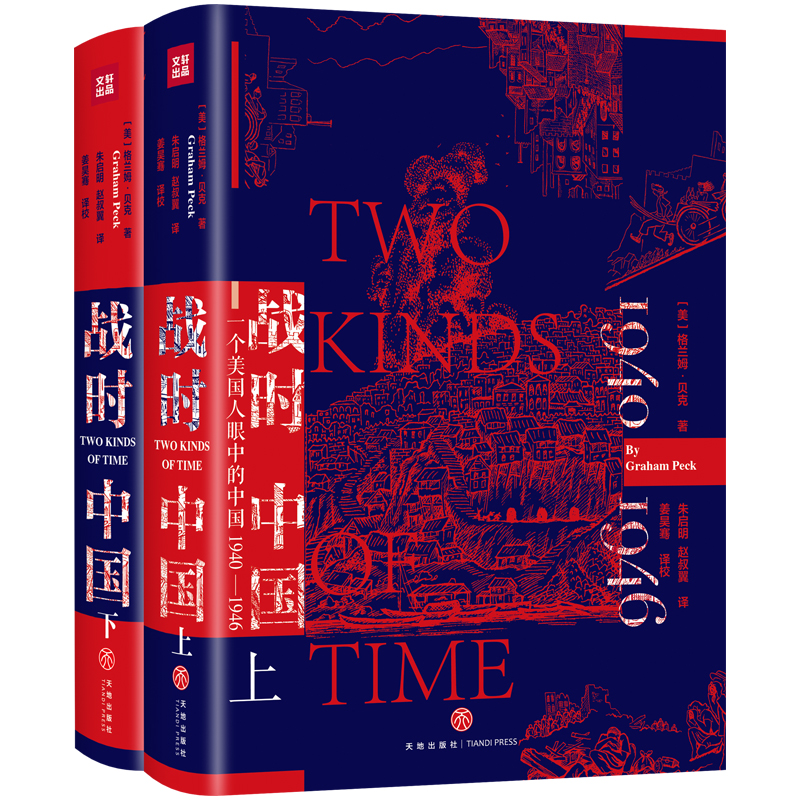
出版社: 天地
原售价: 158.00
折扣价: 93.30
折扣购买: 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上下)(精)
ISBN: 9787545550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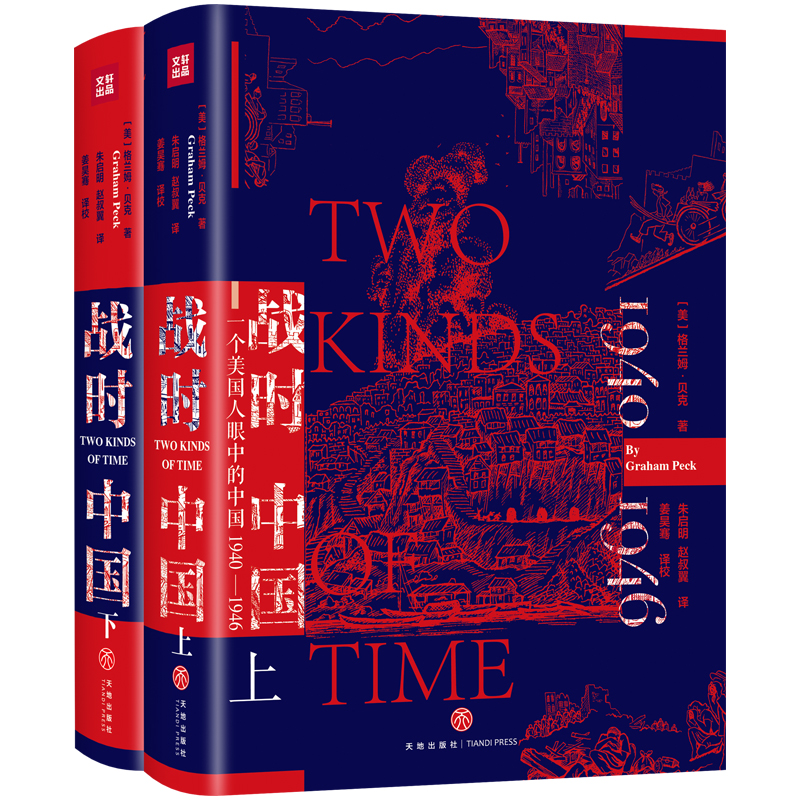
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战争情报局(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1935 年,格兰姆·贝克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被中国深深吸引了,随即将两周旅行计划延长至两年,回到美国后撰写并出版了《穿越中国长城》(Through China’s Wall)。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抱着毕生研究中国的决心,再次周游中国,并进行广泛采访与调查,详细记录所接触到的一切事与人,从军政要人、外国记者到底层老百姓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1950年,格兰姆·贝克将这段经历整理后以《战时中国》(Two Kinds of Time)之名出版,此书一上市就受到美国全社会尤其是军政两界的高度关注。
两种时间观中国人对时间有种观念。他们认为:光阴如流水,人在时间中犹如静坐河边,面朝下游。背后的上游波涛象征未来,是看不见的,只有等它经过身边流向下游,成为过去时,才能被观察到。 据说,中国古代太平时期,有许多优美的园林就是按这种理念设计的。这些园林坐落在山坡上,有萦回的清流激湍而过,岸边开出几个开口,让水流到里面,每个开口旁布置一处舒适的座席。酒杯顺流而下, 雅士静坐其边,随手取之。水流不可测,杯酒亦不可测,但他们只是面对下游美景,对未来不屑一顾,一味地沉浸在过去之中,直到夜幕降临,酩酊大醉。 1940 年春,我来到中国时,原也是想以这种态度对待人生的,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原委还得从头说起。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 1935 年秋天,当时我正准备环游世界,但手头只有在大学念书时靠卖画赚得的一点钱,因此,只打算在中国逗留两周就到别处去。可是这儿的异国情调却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不仅生活舒适,而且物价便宜,于是原定的两周不知不觉就延长到了两年。在机缘巧合下,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学会了汉语,熟悉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身处异乡却无离群之虞。1937年末,日本大举侵华 a,我带着要以研究中国为毕生事业的决心,暂时回到了美国。 1938 年至 1939 年,我希望回中国去,把我当年见过的西南山民生活用图画记录下来。因为我相信,战事一起,大量外地人涌入,遥远的山区必定会迅速移风易俗。但我也明白,他们还会在那里,一时半刻不会消失。 1940 年初,我再度踏上中国国土,当时我对国民党的认识深受美国新闻界正面报道的影响。所以我当时想进入宣传部门或者慈善机构工作,那里欢迎外国人加入。当时,我已写了一部有关上次中国之行的书,挣到的钱足够我再旅游两年,再写本书。我的主要目标是坐在中国的“时间之河”侧旁,观察从身后漂浮而来的人,把掠过我身边的任何有趣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与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截然相反的时间观、人生观。他们认为,人应该昂首面向未来,对过去则可以听任其消逝在身后。而且,还不应满足于静观未来。就我们富有野心的西方传统来说,人是可以主动开拓未来,或可让未来因自己而动的。我们不像一位滨河静坐的看客,而像是飞行员。 看客或许会对飞行员提出异议:过去可知,未来难料,舍可知而求难料,航程便不免盲目而危险。我同意这个观点。 后来那几年,我在中国逗留时,美国已被卷入太平洋战争。局势已经明朗化,不管是否情愿,谁也无法再把自己看成滨河静坐的看客了。珍珠港事件时,我侥幸身处非敌占区,不久又在美国战争情报局获得了职位。由于我的工作是观察与报道,这就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搜集材料的机会,能够比较方便地去了解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到底遭遇了什么, 美国对中国又到底做了些什么。 原子弹爆炸了,太平洋战争结束了。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侵华日军退去,但中国人的内战却箭在弦上。美国与苏联很可能会因此而被卷入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那很有可能是毁灭人类的最后战争。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卸下重庆的战时工作,再次去往中国沿海。1946 年我定居在北平写作此书,以期把这项拖了很久的工作做完,可是不久便下笔涩滞。这不仅是由于我所要写的内容其时间跨度已由原定的两年变成了 6 年,更重要的是,我的笔记上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滨河而坐的看客眼中纤毫毕现的观察材料;另一类则是身居时间机器之中,随时有坠毁的危险,底下却是劫数难逃的河川江山的主观感受。 在北平度过了俗务缠身的一年后,我把一捆手稿带回美国,于 1947 年初开始加工。当此书将近脱稿时,中国内战已转趋激烈。在此情况下,我手头的两种材料就更难处理了。耸人听闻的重磅消息不断从中国传来,此时要把几年前观察的细节网罗进打字机里去,就越来越难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历史的发展终于理清了我的思路,使我认识到既看过去,又看未来,这种撕裂终究并非坏事。于是,我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国的内战接近尾声。形势越发明朗:10 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20 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管中国共产党人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于世界,也不管他们对美苏冷战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能取得政权毕竟得益于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发生在一个有 5000 年悠久历史、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 这场新的革命对未来历史的影响势必如美、法、俄三国的革命一样,甚至比这三国革命的影响更加深刻。之所以做出如此论断,除中国本身的重要性,还由于这是亚洲第一次取得成功的现代化革命,而亚洲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 现在看来,我在中国居住的那几年正值变革成熟的关键时刻,旧社会已腐朽得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鉴于在这样一个混乱与变革时期中,发生在老百姓中的那些小事情可能比官方史书中的大事件更为重要,于是,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我认为,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千百万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缔造者。 我要声明一点:为保护朋友的隐私,也免得有人告我诽谤,本书有几章的姓名、日期、地点都做了改动,甚至连事件本身也可能有所微调。此外,在不致给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前提下,为使行文更加流畅,我对作为看客获知的一些材料也做了调整安排,而不是像写日记那样记流水账。 本书中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都是完全真实的,我都是如实做的记录,尽管有很多真实的细节经过了一番安排,但为了使意思清楚,我还把在若干年内断断续续经历的事情连贯了起来。总的说来,我如实记录了自己的大致经历,并无杜撰。我相信,其真实程度,在今后对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是经得起检验的。 在我叙述自己的经历之前,我想说明: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估计得非常不足。 许多人正在大声疾呼,警告人们要重视共产党和苏联的作用。他们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说成是莫斯科直接策划的阴谋,说这场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得到了苏联在军火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他们责备说:美国之所以未能防止中国倒向共产党是由于美国有一小撮所谓共产党的同路人—某些战地记者和政府官员。据说,是这些人欺骗了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想搞土改,因此值得美国人援助。这些警告者们断言,现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都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 我认为,这些警告者过分自以为是了。 统观中国这场变革所受外国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成功,一如美国和民主主义的失败,都不是关键因素。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当俄国还由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时候,中国就已沉沦到了革命前夕的可悲状态。当时,美国本有机会对中国必然发生的革命施加影响,但我们却不屑于一试。 最后,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了。他们确实在必要时使用了颠覆政权和暴力武装的手段。但这个国家之所以倒向共产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支能够与它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过一种可以代替共产主义又为人民所接受的东西,从来没有过。若是警告中国人说,不能走苏联道路,人家会觉得那都是空话,因为当时中国人本身的生活早已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境地。于是,一个个城市,一支支军队,甚至一个个省份,都不经战斗就投向了共产党。同时,共产党却懂得应该如何减轻阻力,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政治、经济变革,以免引起公众的反感。 在国共内战中的最近几年,美国支援反共力量—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力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当然,一个强大的、与之接壤的共产党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支援,至少能够给那些主张更积极干涉的美国人某种压力,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支援。一直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苏联在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给过中国共产党以重大物资援助。例外的只是那么一点消极援助,即对共产党在东北接管战略要地和物资未予以制止。这些战略要地和物资原是太平洋战争末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没收日本军队的,其中的物资是在冬末初春撤军时没有带走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的援助,苏联人也不会给。我只是要强调一下,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苏联那么一点援助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相比之下,日本刚投降,美国就开始十分积极地援助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是用美国的飞机和船只运出西南的。美国还从太平洋地区调拨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抢占东北南部战略要地、接收日军装备。美国给国民党的便利至少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得到的便利。此外,日本投降之前和之后,美国不仅给了国民党价值近 1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他们训练军队,还给予经济援助,并在国际政治方面大力支持。连一提到共产党就惊慌失措的人也没说过苏联曾给他们的中国伙伴以同样的援助。 有人给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戴帽子,指责他们要对美国一手炮制的抢救国民党的计划的失败负责。我想,本书将可说明,这顶帽子恰好应该回敬给指责者自己。凡同意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所谓左翼政策的人都看到过,革命前夕的国民党已经腐朽透顶,再不采取激进措施,国民党政府必将土崩瓦解。他们还看产党已强大到了如此程度,任何民族抗战或民族和平的计划都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如不得不用联合的方式代替军事冲突—所以只要战端开启,结局只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 过去 10 年中,这种意见仅在 1944 年至 1946 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对美国产生影响。其余时间,美国对华政策则由保守派左右。由于他们的计划的基础是帮助中国那个最腐败、最守旧、最不得人心的集团,结果他们恰恰让一个不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前景更快地破灭了。美国对国民党中央亲信集团给予援助,使他们得以在一个时期内延续了统治。在此期间,它打压一切舆论批评,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除共产党的其他民主党派,并断然拒绝一切有望收拾人心、重获生机的措施。从我了解了国民党的统治机器那天起,我就极端厌恶它。但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我都承认它毕竟是中国仅存的一支所谓的“正规武装”力量。上层如果能输入正派的新血液,或许能够自救,可以在联合政府中与共产党抗衡,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党政治革命的最大希望,也能让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有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中国。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十分微小—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出民主的第三势力。可是,就连这种十分微小的可能性也被美国援助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扼杀了。 尽管如此,我想,将美国的错误归咎于少数身居高位的保守主义者是愚蠢的,正如将其归咎于政治光谱中的任何其他少数派一样。从我在中国旅行和生活的经验来看,美国很难真正顺应另一个国家中的星火燎原,原因正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由国民性、媒体、外交机构、企业界、军队、联邦政府和国务院所共同塑造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中国正潜伏着一场不待引火便可自燃的革命。中国农民性情坚忍,因此革命之火燃烧得很慢,但一旦烧起来就无法扑灭。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就爆发过这样的革命。我们不情愿了解它,因而无助于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当这场革命真正由共产党点燃,并确已成燎原之势时,我们却惊慌失措地想一口气把它吹灭,那无异于助长火势。我们的干涉,特别是把杀人武器送给国民党,也使中国人民更加恼火。与共产党的宣传相比,这些举措对“反美空气”形成的作用反而要大得多。 这段历史的全部关键在于:除非冷战确实演化为核战争,否则我们美国人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在中国发生过的那种问题。在亚洲大多数国家,也许还有非洲、南美洲,甚至西欧国家,完全内源性的革命将会发展壮大。这样的时刻无疑会到来。革命将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还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个抉择终将呈现在革命者面前。 那时,我们惨败于中国的故事或许就值得一读了。 1 美国作家、画家格兰姆·贝克匠心独运的精彩之作!2 作者于1940年第二次来到中国,用6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用客观、理性理想的文字和图画记录下真实的中国社会百态与中国人民的精神品质。 3 战争持续、政治混乱、经济濒危、社会动荡……抗日战争证明了中国人民坚强隐忍、乐观向上、不屈服、不放弃的民族精神。 4 用冷静、真实、平和的方式记录亲身经历的一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和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伟大选择的诞生过程。 5 以世界发展的眼光,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深度剖析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叶是如何误读了中国。 6 欧美世界深入、仔细观察中国的经典作品,告诉世界只有看懂中国的社会与中国人的生活,才能看懂中国的发展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