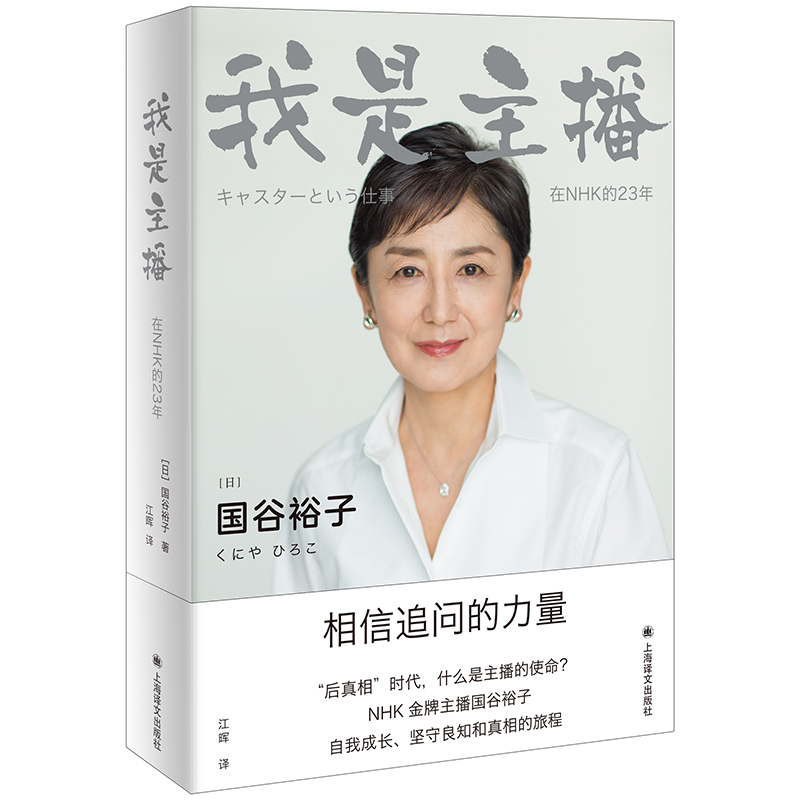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2.30
折扣购买: 我是主播
ISBN: 9787532786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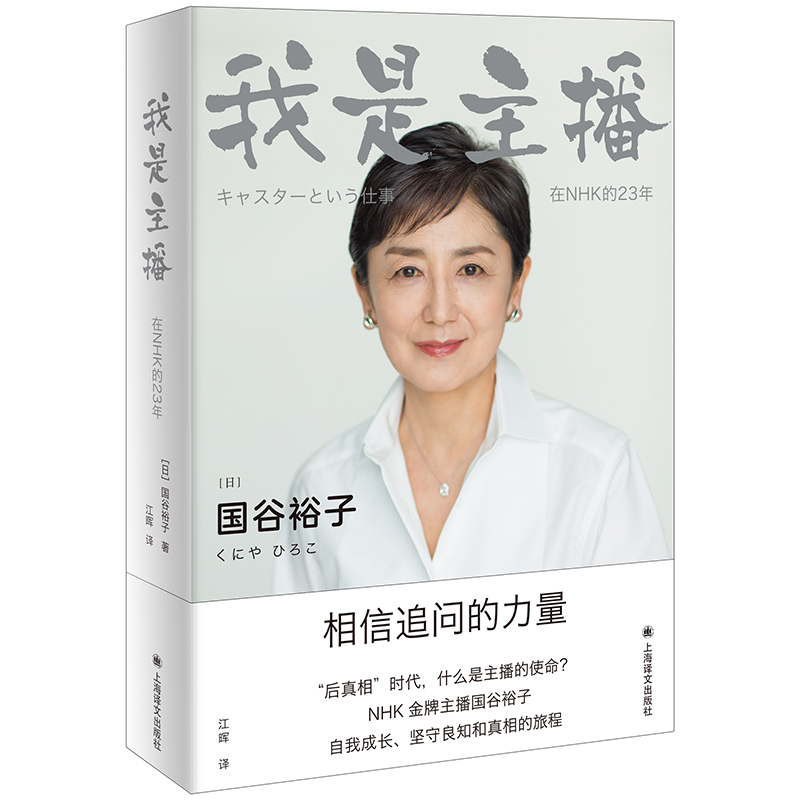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国谷裕子 NHK著名电视主播,在日本拥有很高的出镜率和影响力。 1957年出生于大阪。1979年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1981年担任NHK综合频道《7点新闻》英语播报的翻译和播音员。1987年开始担任NHK?BS《环球新闻》和《阅读世界》等节目的主播。1993年至2016年担任NHK综合频道《聚焦现代》主播。1998年获“放送女性大奖”,2002年获菊池宽奖,2011年获日本记者俱乐部大奖,2016年获“日本银河奖”特别奖。 \\\\\\\\\\\\\\\\\\\\\\\\\\\\\\\\\\\\\\\\\\\\\\\\\\\\\\\\\\\\\\\\\\\\\\\\\\\\\\\\\\\\\\\\\\\\\\\\\\\\\\\\\\\\\\\\\\\\\\\\\\\\\\\"
\\\\\\\\\\\\\\\\\\\\\\\\\\\\\\\\\\\\\\\\\\\\\\\\\\\\\\\\\\\\\\\\\\\\\\\\\\\\\\\\\\\\\\\\\\\\\\\\\\\\\\\\\\\\\\\\\\\\\\\\\\\\\\\"【精彩书摘】: 十七秒的沉默 2001年5月17日播出的节目名为“高仓健:真实心声”。高仓健先生已迈入古稀之年,电影产量也控制在几年一部,如今的他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来看待电影演员这份职业的呢,节目对于这次采访的主题设置相对宽泛。因为高仓先生向来很少接受采访,这一次竟然同意接受我们的电视采访,为此节目组的制作人员们都兴奋不已。可是于我而言,兴奋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压力。 主播作为提问方,事先是否为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想被采访对象在见面后的几分钟内就能察觉出来。如果被对方发现你没有认真准备,那么估计对方也不会太深入地回答你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缺少必要的准备步骤,你自己也会心慌不安,还未与对方展开平等自由的对话,采访就匆匆结束了。 所以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也是着实下了一番工夫。高仓先生一共出演了二百零三部电影。在他凭借任侠电影红遍日本的时候,我因为在国外生活,没能同时期看到这些电影。为了这次采访,我开始埋头看电影,并且找来与高仓先生相关的杂志、报纸、他本人出版的散文集和采访记录等大量资料。 然而在采访正式开始后,任凭我怎么提问,高仓先生只是用非常简短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生硬的语言回答我。对话完全进行不下去。我一边坚持提问,心里却是焦急不已。 于是我试着这样给自己打气:“今天是几乎不接受采访的高仓先生给我们的宝贵机会,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有耐心去等。”所以当他停下话头的时候我也不去催促,只是静静地等待。最初高仓先生也跟着我一起沉默,而此刻的沉默显得分外漫长。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不去发问,终于高仓先生打破了这份沉默,开始交谈。 高仓:“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做到给自己放假去世界上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住高级宾馆,到高级餐厅吃饭,也不用去看菜单上的价格。坐飞机是头等舱,住宾馆是高级套房,这些好像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沉默) “但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收获并不是在于上面这些事情,而是在观众深受感动的瞬间,我会对自己说,啊,太好了。” 国谷:“您刚刚结束了《萤火虫》的拍摄,接下来想参演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高仓:“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即使再不愿意,首映的日子也还是会如期到来,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就想走到一个地方吹吹风。” 国谷:“吹吹风?” 高仓:“是的,吹吹风。如果是非常猛烈的风,可能会让你失去温柔的心。所以想要恰到好处的风,只有你主动地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带到那个有好风的地方。你一直在原地等是等不来风的,这一点是我到这个年纪才明白过来的。” 在对高仓先生的这一段采访里,事后计算发现沉默的时间一共是十七秒。或许你会觉得不过十七秒而已,但是对于一个采访人来说,十七秒已经是相当漫长的时间了。采访中的沉默,在采访人看来是近乎恐怖的东西。所幸这一次采访是安排在一家料理店的室外走廊上,对面是庭院,能听到鸟鸣、池子里的流水声,甚至还有庭院外面道路上开过的救护车的声音。如果是在完全静音的演播室录制节目,这十七秒的沉默恐怕是我无法承受的吧。 然而对于高仓先生来说,这沉默的十七秒钟是他需要用来组织语言必不可少的时间吧。通过这次采访,我认识到“等待”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因为担心出现空白就一个紧接一个地抛出问题,反而容易错失提问的良机。 “等待”也是为了“听见”。在采访高仓先生的时候,我能够按捺住内心的焦急让自己等下去,或许是得益于内田义彦先生的那一句“一心聆听,直至听见”吧。 高仓先生在收看节目之后给我们发来消息,对我们在节目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那沉默的十七秒钟表示感谢。这是后话。 而我,对于处理采访中的对话也变得更加游刃有余了。 “听见”与“聆听” 经济学家内田义彦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听见与聆听”的随笔(收录于藤原书店出版的《活着,学着》)。用英文说就是“hear”与“listen”。内田先生在这篇随笔里写道:“重要的是为了‘听见’而去‘聆听’。”即为了“hear”去“listen”。他还写道:“一心聆听,直至听见。”也就是一边“listen”一边等待“hear”的意思。换句话说,内田先生想要强调的是,认真仔细地去听对方的每一句话,也就是“listen”的能力固然重要,能够领会对方想要表达的全部意思,即“hear”的能力也万万不可忽视。 “如果在聆听的时候不能做到聚精会神,或者没有事先准备好要点提示,人们很难真正‘听见’别人说的话。话虽如此,如果仅仅是盲目地执着于聆听的形式,也会造成听了却没有‘听见’,不,准确地说是越听反而距离‘听见’越发遥远的结果,即便理解了说话人特别提示的要点,但也仅限于此,仍然无法实现对事物整体的把握。”“一心聆听,直至听见。” 重要的是为了“听见”而去“聆听”。可见,采访中所必需的“倾听力”对于观察力和想象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内田先生在这篇随笔中提出的观点,我个人非常认同,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那还是我在卫星频道担任主播的时候,有机会采访到日本访问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在采访正式开始之前,我向对方说明今天的采访内容将主要围绕欧洲整合的问题,不想施密特先生对我说:“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得到的仍然是同样的回答。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为了缓解这份尴尬,我只得转换话题,问道:“我们准备了咖啡、红茶、橙汁,还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吗?”回答是“COKE”。这回轮到我听不懂了,呆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施密特先生放慢语速又说了一遍:“Coca-Cola。”这位年逾古稀的德国老牌政治家说要喝“可乐”,虽然我也有疏忽之处,但是这个回答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没能迅速反应过来。 接着施密特先生又缓缓地说道:“我的右耳不太好。”而我正坐在他的右侧,他根本听不清我说的话,于是数次对我说“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而我一心只想着向对方说明情况,丝毫没有捕捉到他可能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的耳朵听不见的信息。这正是只顾“聆听”却未能“听见”,少了那份“倾听力”。采访并不是只要提问,然后听对方的回答这么简单,观察力和想象力也缺一不可,这是我通过切身体会得到的经验。 或许就是在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采访方式,从以往只重视提问的问题变为在“聆听”的同时注意“听见”的效果。有人将我的提问方式称为“切入型”,的确,因为现场直播的时间有限,很多时候我只得采取接连发问的方式。但是为了不错过发问的好时机,我同时还需要认真地倾听对方的回答。并且我逐渐领悟到,在这个时候,除了要仔细听取话语中的每一个细节,去“听见”、去感受对方整体透露出来的讯息也至关重要。“为了‘听见’而去‘聆听’”,内田先生的这句话我珍视至今。 电视报道的三大陷阱 在担任《聚焦现代》主播的这二十三年里,我也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制作电视报道节目的不易。提到其中的难,首先得讲讲这些年我时常感受到的电视报道所具有的危险性。 我进行了一下整理,总结出电视报道的三大“陷阱”: 其一,削弱事实的丰富性。 其二,煽动观众的情感共鸣。 其三,附和舆论的风向。 主播的工作完成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地避开这三大陷阱。 其中第一点“削弱事实的丰富性”这个陷阱该如何避开呢?这其实是最有难度的。虽然制作电视节目的本意在于让观众理解节目的全部内容,但是稍有差池,又会掉入另一个陷阱,成为“仅追求简单易懂的节目制作”。如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节目传达的信息越简单收视率越高,这背后就隐藏着一种危险,即为了追求“简单易懂”,而削弱了事件真相的深度、复杂性和多面性,也就是事实的丰富性。尤其对于报道类节目而言,这一点可以说是致命的危险。 评论家兼作家辺见庸先生根据自身参与电视节目制作的经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做的事情基本就是寻找易懂的内容、将事物简单化”。这是极其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转身将这种被批评的痛苦置之脑后,那也就没有资格作为一名电视报道从业人员了吧。就我自身而言,一直在努力摸索如何在追求电视报道“简单易懂”的同时又保留事实的丰富性,如何尽可能地将真相的深度和全面性展现给观众,而非将事物简单化处理到仅剩下易懂的内容。当然,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听其他工作人员说,NHK在新员工培训时就强调,要求写出的新闻稿或制作的电视节目连中学生都能看懂。相信每天收看NHK节目的观众应该能够理解,从理论到实践显然是极具难度的。但是在时下“简单易懂才是电视”这种声音高昂的风潮中,还是难免让人忧心。 最近的电视报道为了追求“简单易懂”,通过图片、模型、漫画甚至重现视频等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样的节目制作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模式:将事物简单化,只为求得Yes或No的结论。其实最危险的是,一旦习惯了这种报道方式,观众将只对“简单易懂”的内容产生兴趣。 当然,希望节目内容简单易懂这种要求原本来自观众。如果无视这种要求、不管观众理解与否,节目制作方一定会被批评为仅仅是为了自我满足吧。然而如果真如观众所期待的那样“简单易懂”地报道,对观众来说是一件好事吗?对于复杂的问题,难道没有必要让观众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吗?因为人一旦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在那个瞬间就会立即停止思考。 数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电影导演兼电视纪录片作家是枝裕和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电视的文章。 “并非是将难懂的事情变得易懂,而是要描绘出大家都认为易懂的事情背后隐藏的难懂,这样才能让智慧生根发芽。” 这不正是《聚焦现代》所追求的、也是作为主播的我一路为之苦苦追寻的目标吗?读到是枝先生的这篇文章时,我立刻产生了如下的想法,那就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将事情“简单易懂”地传达给观众,而是要把看起来“简单易懂”的事情背后的复杂性、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告知观众。我想这也正是《聚焦现代》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希望观众能够尽可能地和我一起经历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所经历的多角度的思考过程,间接体验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讨论解决方案等一系列流程,而非只为快速求得一个结论。一直以来,我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去对待节目以及观众的。 然而这种想法或许会给观众造成一种“不快感”。但我认为即使这样也没关系。或许是我的美好愿望吧,我相信每一位观众一定都拥有消化这种“不快感”的能力。在前文引用的辺见庸先生的文章中,他紧接着给电视行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可以让人们反复去思考的环境?” NHK与其他民营电视台都设有“放送节目审议会”,这是根据日本《放送法》设置的,可以对放送节目提意见的唯一组织。我在NHK主页上公布的“中央放送节目审议会”的会议记录里,看到有一名委员针对NHK新闻的报道方式,以及为了保持中立而采取的并列式报道,提出了如下质疑: 几乎所有的问题,即使通过单纯的二元对立方式来描写,想要接近它的核心部分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在赞成与反对之间都存在着无边的中间地带。并且大部分的观众也是在这个中间地带徘徊,来回变换自己的想法。而这种将看待问题的角度两极化的处理方式,与其说是为了寻找解决方案而进行深度讨论,不如说是强制观众加入相距遥远的两个小组,参与“赞成—反对”的分组站队游戏……但是这样做并不一定能使讨论更加丰富多彩,进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那么如何才能杜绝非白即黑的简化处理模式呢?对于电视报道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风向原则 至于第二点“煽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第三点“附和舆论的风向”,这两点其实存在内外呼应的关系。 电视拥有的图像传达能力、同时性和及时性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例如“9?11”事件中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遇袭击的影像,以及“3?11”日本东北地区遭遇海啸的影像,这些图像能够在一瞬间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极为情绪化的情感共鸣。另外如体育比赛转播,尤其是日本代表队的胜负争夺等相关播放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接下来,媒体开始想方设法地去附和这种由图像煽动起来的观众的情感共鸣。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民中有不少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袭击”。纽约本就是一座各色人种聚集的城市,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这里拥有能够产生多样化视角的土壤。《聚焦现代》也于11月在当地制作了连续四期的系列节目,其中有对作家保罗?奥斯特和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采访,他们都主动谈到了“为何我们会成为如此被憎恨的对象”这个问题。奥斯特说:“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纽约人开始了关于自身的思考,例如为什么我们会被袭击,我们可以依靠什么。然后环顾四周,这里是世界上最为纷杂的大都市,而我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的纽约。于是人们变得更加亲切,不相识的人们也开始尝试交往。”斯科塞斯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人们正在试图去了解以前并不熟悉的文化,对伊斯兰教毫无认知的人如今开始学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只有无知才会产生恐惧,恐惧继而演变为愤怒,而这种愤怒终将转化为杀意。”这是2001年11月23日播出的“系列节目纽约播报:美国何去何从④——凝视纽约”中的采访。 然而,在世贸中心被袭以及满街飘扬的星条旗的相关图像被反复循环播放的过程中,美国转瞬间变成了斯科塞斯导演口中那个因为无知而被憎恨与复仇情绪冲昏头脑的国家。 “9?11”事件的相关影像就是如此先将美国国民推向恐的深渊,其后又进一步促国民生情感共鸣,让人们因为燃烧的憎恨与复仇情绪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最终剥夺了人们冷静的判断能力。并且福克斯电视台因为这种附和观众情感的报道方式迅速提高了收视率,于是其他电视台也都紧随其后,纷纷采取了类似的报道方式。 让人快速获知世界时事也是电视作为媒体发挥的作用之一,并且满足了观众希望通过收看电视来了解他人动向的需求。因此电视天然就拥有将社会均质化的功能。同时另一方面,电视的制作方为了获得更多观众,不得不密切关注观众的动向。由此产生的观众与制作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比强大的。电视煽动着观众的情感共鸣,导致的结果是,随着这种情感共鸣的日益高涨,电视又转过头来开始附和观众的情感。 如此相互作用加速了多数派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排除少数派、排除异质的情况。剧作家井上厦将这种现象称为“风向原则”,即舆论风向在被媒体宣传扩大的过程中,其力度也愈渐加强,而当这股风力增强到无人能抗衡的地步,就会发展成“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所谓“风向原则”的威力。 电视往往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来展示它的强大力量。那种促进观众的情感共鸣、形成强烈的命运共同感的力量当然也包括在其中。诸多媒体当中,尤属电视最为擅长触动人的感性、情感。也正因如此,为了获取更多的观众,电视制作方总是尽最大可能把电视的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然而当由此形成的命运共同感处于统治地位时,再想要宣传少数派或者反对派的意见便会难上加难。尤其当众人意见一致时,一旦有人提出质疑,很多时候会受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如此一来,在媒体内部也会发生“风向原则”。 这就是借助简单易懂的表现形式来附和观众的情绪,最终被观众的“情感共同体”同化的危险。媒体,特别是电视尤为容易踏入这个“陷阱”。因此,即使冒着会被反击的风险,也应该一丝不苟且持之以恒地去质疑、去求解。为了避免简单化、一元化的处理,需要从多样的、不同的视角去质疑。我认为只有坚持质疑,才能避免踏入“煽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和“附和舆论的风向”的陷阱。 \\\\\\\\\\\\\\\\\\\\\\\\\\\\\\\\\\\\\\\\\\\\\\\\\\\\\\\\\\\\\\\\\\\\\\\\\\\\\\\\\\\\\\\\\\\\\\\\\\\\\\\\\\\\\\\\\\\\\\\\\\\\\\\" \\\\\\\\\\\\\\\\\\\\\\\\\\\\\\\\\\\\\\\\\\\\\\\\\\\\\\\\\\\\\\\\\\\\\\\\\\\\\\\\\\\\\\\\\\\\\\\\\\\\\\\\\\\\\\\\\\\\\\\\\\\\\\\"【编辑推荐】: “相信追问的力量。” ★ NHK金牌主播的23年职场故事 ★ 一段自我成长、坚守良知和真相的旅程 ★ 写给“后真相”时代的每一位媒体人 “不是将难懂的事情变得易懂,而是要描绘出大家都认为易懂的事情背后隐藏的难懂,才能让智慧生根发芽。”——是枝裕和 世界已经步入了“后真相(post-truth)”时代: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浮于表面的语言,肆意泛滥的虚假信息…… 而媒体,正在日渐失去应有的影响力。 在“碎片化”、“娱乐化”的时代,怎样报道,才能让观众认真思考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承受着“众人一致的压力”时,媒体还能公平地报道新闻,而不是附和社会风向吗? 从1993年到2016年,国谷裕子和NHK王牌节目《聚焦现代》一同见证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 在这个自媒体、播客、视频大行其道的时代,国谷裕子用她的职业经历提醒所有的新媒体人: “相信追问的力量”,是主播永远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