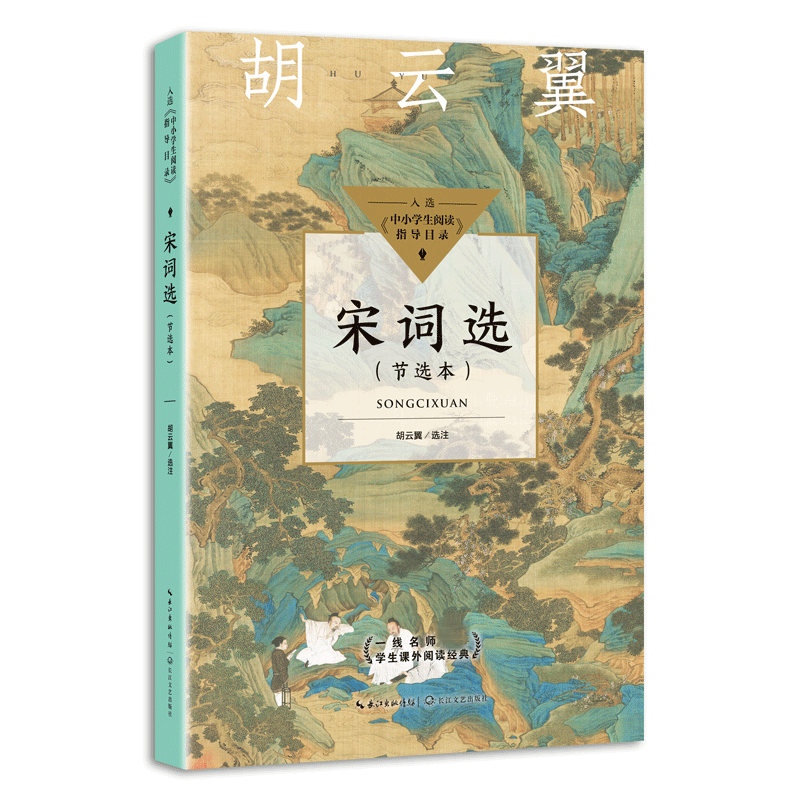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19.80
折扣购买: 宋词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高中)
ISBN: 9787570223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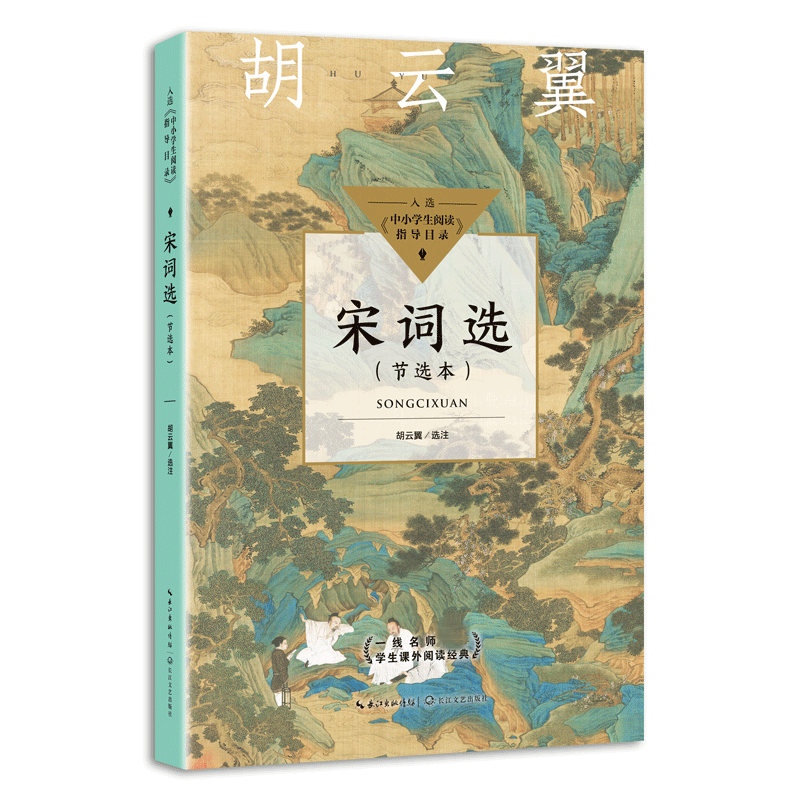
胡云翼(1906—1965),湖南桂东人,原名耀华,词学家。著有《宋词研究》《宋诗研究》《唐诗研究》等。
前言 一 词是唐朝兴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的兴起跟音乐的发展密切地结合着,和乐府诗的性质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前人探讨词的起源往往溯源于古代的乐府。从形式上看,南朝乐府里某些长短句的歌辞,如萧衍、萧统、沈约写的《江南弄》十四首,一律都是七言和三言相杂的定句、定字;隋朝杨广、王胄写的《纪辽东》四首,更接近词的形式格律。但是我们认为,词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兴的文体,还是有它自己发生、发展的一条历史线索,和乐府诗混同起来讲,不能说明问题。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这里所谓“曲子”就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即宴乐),那是代表西北民族刚健风格的新音乐,和中国原有的清乐有所不同。这两种体系和性质不同的音乐配合着不同的歌辞形式。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燕乐的。词,是这种新兴的曲子词的简称。 曲子词首先盛行于民间。根据敦煌词的有关资料,证明无名氏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是盛唐时期或者还早于盛唐时期的作品,而且是地道的民间词。这决不能是孤立的现象,如果不是当时的民间词十分兴旺,那末当时比较偏僻的敦煌地区会有盛唐词的抄本保存下来便成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至于文人的词作,相传以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为最早。黄昇《花庵词选》称为“百代词曲之祖”。但是后世有些词论家疑为伪作。从词发展的因果关系来看,丝毫找不出这两首号称李白的词对盛唐、中唐文人有何影响。中唐文人所熟悉的长短句词调一般是比《菩萨蛮》《忆秦娥》更为简短的小令,如《长相思》《调笑》《渔父》等。其语言风格都具有民间气息。十分明显,这时候民间词已经广泛流行着,引起了爱好民歌的文人的兴趣。白居易、刘禹锡他们“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便是有意识地模仿民间的曲子词。据《尊前集》所载,白居易词二十六首、刘禹锡词三十八首,还有韦应物、张志和、王建等文人的作品。这种事实表明:从中唐开始,填词的风气已从民间传播到文人社会里来。 晚唐、五代,文人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致力于词的文人逐渐加多,西蜀和南唐形成两个词坛,词风都很盛,不像中唐文人那样只是偶尔填词了。《花间集》所录晚唐、五代词人,不包括南唐在内,有十八家,词四百九十七首。其次是采用的词调加多,不再局限于几个简短的小令(如冯延巳的《阳春集》采用了三十九个词调);长调也有出现,形式格律渐趋复杂。一些著名词人如温庭筠、韦庄、李煜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此外,必须指出的,文人词和民间词的分道扬镳这时已很明显。民间词不限于写闺情,它体现了市民阶层比较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其中某些词反映出当代动乱不堪和民族矛盾的现实。贵族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竭力逃避现实,词便成为他们歌筵舞榭、茶馀酒后的消遣工具。作为晚唐、五代词人代表作的《花间集》,几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写绮靡生活中的艳事闲愁,在他们的词里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 二 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了宋词空前的繁荣、发展与提高。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年变乱相寻的局面,成为一统。随着出现一个宋朝统治阶级自夸为“百年无事”的承平时期。邵雍在一首《插花吟》里这样歌颂着:“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实际情形当然不如邵雍所粉饰的那样。这百年中决不是真正太平无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一再挫败,屈辱求和;国内屡次爆发具有相当规模的人民起义(虽然都未能持久),不论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都表现得很尖锐。即使在繁华的京畿地区,也说不上“全盛”。据《宋史·吕蒙正传》记载,宋太宗赵光义在元宵节宴赏大臣时,极力吹嘘“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但吕蒙正却给他指出:“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于此可见在“全盛”的旗帜底下掩盖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现实。 虽然这样说,我们还是承认北宋王朝保持着比较长期的国内稳定的局势,在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工商业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城市人口日益集中。作为市民主要文娱节目之一的音乐,其需要就日益扩大。汴京是北宋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地方,集中了天下的财富,秦楼楚馆,竞赌新声。歌词随着市民这种需要的扩大也就更加兴盛起来。 关于北宋前期的词坛,我们首先要提到较早的上层文人的词。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文人词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如晏殊的《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欧阳修的《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 他们这一派的词几乎没有保留地承袭晚唐、五代的词风,局限于抒写离别、相思之情,风格仍旧柔靡无力。他们主要不是步趋温、韦,既不同于温庭筠、欧阳炯、张泌一派无行文人的词那样轻浮、侧艳,也不同于韦庄伤乱和李煜亡国的哀吟,在五代词人中,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开北宋一代风气”的是冯延巳,他对晏、欧的影响最深。这是不难理解的:陈世修《阳春集序》说冯延巳处于“金陵盛时,内外无事”,他写词只是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的风格又是那么典雅雍容。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胃口。北宋前期达官贵人的词一般也都用来娱宾遣兴的,如晏殊在宴饮歌乐之余的“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欧阳修“聊陈薄技,用佐清欢”的新声(欧词《采桑子》题序),可见金尊檀板和词作简直是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作品的内容必然庸俗无聊,空虚无物。这正和当时风靡一时的《西昆》诗一样,必然为人所厌弃。晏、欧词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善于写即景抒情的小词,善于用清丽而不浓艳的词语,构成情景相符的画面,表达得较为含蓄而有韵致。如果说他们在承袭五代词风的同时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大概就在这比较细微的区别上了。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发展了长调的体制,善于用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用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是柳永词不同于晏、欧一派局限于知识分子自我欣赏的狭隘范围的特征,也就是柳词受到一般市民欢迎而风行一时的主要原因。 宋初词人所用的词调还是限于比较简短的。晏殊的《珠玉词》、欧阳修的《六一词》里用得最多的词调是《浣溪沙》《玉楼春》《渔家傲》《蝶恋花》《采桑子》等。晏几道的《小山词》也是如此。其中有的是整齐的七言,有的是以七言为主的长短句。这可见他们还只是习惯于选择近乎诗体的词调来填词。但是,当时社会早已形成了“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的风气,民间流行的新乐曲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复。柳永是一个精通音律、爱好民间音乐的词人,他和乐工们合作,创制了大量以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为其特色的慢词。如顾敻的《甘州子》只有三十三字,柳永的《甘州令》增为七十八字体;牛峤的《女冠子》只有四十一字,柳永的《女冠子》增为一百十一字和一百十四字两体;冯延巳的《抛球乐》只有四十四字,柳永的《抛球乐》增为一百八十七字体;李煜的《浪淘沙》只有五十四字,柳永的《浪淘沙慢》增为一百三十三字体;晏殊的《雨中花》只有五十字,柳永的《雨中花慢》增为一百字体。这都可以看出词体随着乐曲繁衍而为长篇的趋势。长调本不始于柳永。敦煌所保存的唐朝民间词里,《内家娇》和《倾杯乐》两个词调都在一百字以上。还有题名杜牧的《八六子》八十九字,题名后唐庄宗的《歌头》长达一百三十六字。但是,长调的得到发展,蔚然成为一代的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他的《乐章集》所用的一百多个词调中,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或者是借用旧曲制成新体的,有分为三叠长达两百字以上的(如《戚氏》)。词的体式至此便相当完备了。 柳永的语言风格不同于晏、欧一派,受晚唐、五代文人词的影响不大。他善于向民间词吸取营养,从许多优秀的民间词里学会了怎样写闺怨,怎样使用俚俗语言,怎样运用铺叙的手法。他成功地运用铺叙的手法,为北宋文人写长调开辟了道路。作为一首长调,必须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因此,如何铺叙便成为关键性的课题。柳永铺叙的特征主要是尽情描绘,不再讲究含蓄;他把写景、叙事、抒情打成一片,而在结构上却又有一定的层次,前后呼应,段落分明。夏敬观《手评乐章集》称他的词:“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这话是符合实际的。与柳永同时的词人张先、晏幾道都有长调的制作,但都不以铺叙见长(李清照《词论》说“晏苦无铺叙”),缺乏组织长篇的才力,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都不能和柳永相比。 北宋文人词里有俚、雅之分,始于柳永。他完全不顾士大夫的轻视和排斥,使用极其生动的俚俗语言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一手建立了俚词阵地,和传统的雅词分庭抗礼。加以作者写作技巧的纯熟,善于“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因而受到大众的喜爱,享有任何词人都不曾获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声誉。可是我们这里必须指出,柳词的风靡一时,决不是由于他所组织的主题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他着重写妓女和浪子,即使在市民社会里也只是病态的一角,没有多少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他也以同情的态度写妓女,可没有塑造出受损害、受侮辱的妓女形象。试以敦煌保存的民间词作为范例,如《望江南》里的“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又如《抛球乐》里的“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仅仅三言两语,便道出了极其沉痛的心情。与此不同,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实际上是安于被人狎玩的形象,她们没有不满和反抗,甚至某些写妓情的词还有着色情描写,即使五代文人的艳词也没有达到如此淫秽的程度。这种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词作,不但给读者带来许多毒素,同时也说明柳永学习民间创作,只着重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真正的人民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对他的俚词,也不应作过高的估价。此外,柳永还有一些歌颂圣德、追求利禄的庸俗作品,也是应予批判的。 北宋前期的词,不论晏殊、欧阳修、柳永或其他词人,不论雅词或俚词,不论所反映的是士大夫或是市民的精神面貌,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内容仍旧局限于男女相思离别之情,“靡靡之音”充塞了整个词坛,风格始终是柔弱无力,极少例外。苏轼的贡献首先是打破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开拓词的内容,提高词的意境。胡寅在《酒边词》的序文里有一段介绍苏词极精辟的话: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建立这种新的豪放风格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欧阳修对于诗文都有所革新,对于词则原封不动,可见词的传统观念的牢不可破。苏轼“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而且把词看作和诗具有同样的言志咏怀的作用,这样,就解放了词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较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王灼《碧鸡漫志》说: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艺术巅峰,几百年来一直以丰富的情思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宋词选》打破了《宋词三百首》等书注重音律词藻的选词传统,更重视词作的思想内涵。同时,该作注释详尽,评述精辟、清晰,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领略宋词的迷人风采,还能使读者得到更多的人生体验和美的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