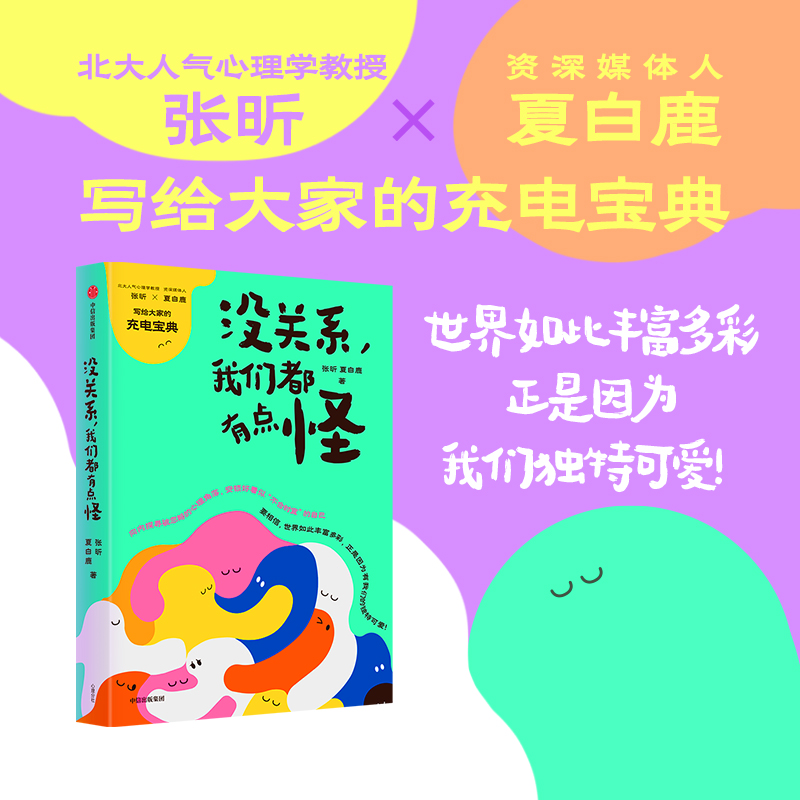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没关系,我们都有点怪
ISBN: 9787521752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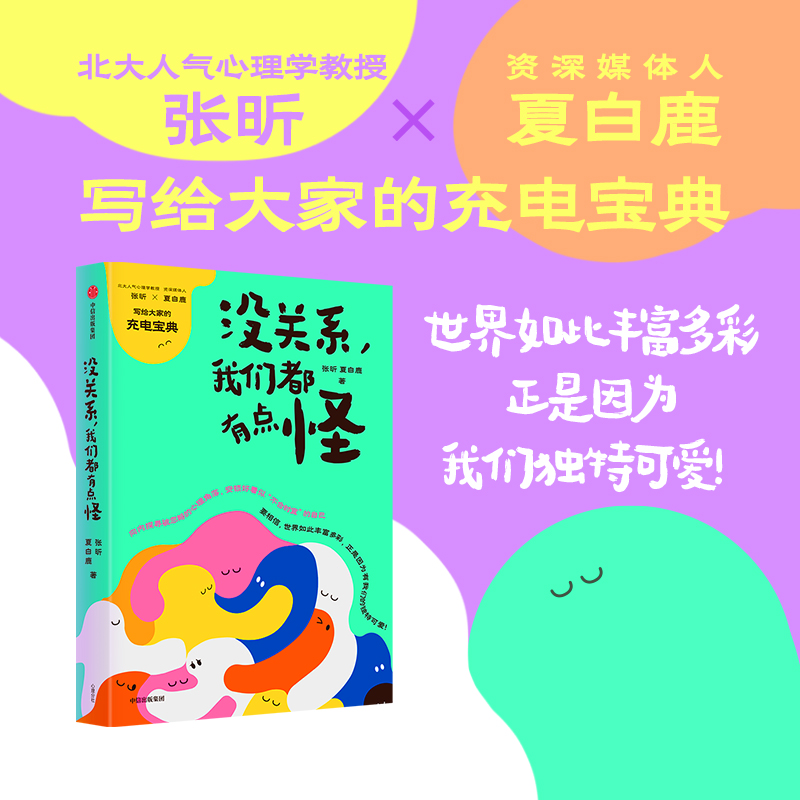
张 昕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老年学会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毕生发展心理学、情绪心理学。担任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副主编、编委;作为中国方成员参与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之“玛丽居里行动”、欧盟COST Action-LeverAge等项目。已出版作品《了不起的心理学》。 夏白鹿 资深媒体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公众号“Dr昕理学”创办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在《香港商报》任记者期间,获香港报业工会颁发“最佳新闻报道奖”。 两位作者联合创办公众号“Dr昕理学”与知乎专栏,曾分别获“北京大学2017网络新青年”、知乎“年度荣誉知友”称号,擅长以贴近生活、轻松幽默的叙事方式,向大众科普心理学知识,内容主要涉及发展心理学、情绪发展与调节、个人成长及亲密关系等。
事与愿违: 越想做好越做不好 “为什么我越想做好某件事,它就越往坏的方向发展?” 很多事情,你越是往好的方向去预期,越关注它,结果就越容易事与愿违。当你在心里自我暗示“我并没有在关注它”,反而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再比如,有学生告诉我,他高考结束之后分数出来之前, 从来不敢憧憬和幻想自己考上心仪的好大学是什么光景,生怕自己想多了,反而不会实现了。 这种心理如此普遍,对此好奇的朋友希望我能解答其中的原因。恰巧,心理学刚好可以解释。 悲观者的情绪记忆 根据一个人的归因风格,人格心理学将人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者总是能使用积极的情绪策略和归因策略,甚至只关注并放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而忽视消极因素。他们会将最大化的正面因素作为自己行为和决定的衡量标准(只要这件事情有好处,那就去做),而看不到事物坏的一面(“我觉得这些坏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悲观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只能看到并放大事情的消极面,忽略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会将最大化的负面因素作为自己逃避某个行为或决定的衡量标准(只要这件事情有坏处,那就不做。他们会无限放大这个坏处,觉得这个坏处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看不到事情好的一面(“我觉得这种好运轮不到我”)。 同时,悲观主义者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他们非常擅长调动消极的情绪记忆,自动忽略积极的情绪记忆。就拿观看奥运会来说,一个悲观主义者会自动过滤那些赢得比赛的记忆, 记住那些输掉比赛的记忆,因此形成“只要我看过的比赛就一定会输”的执念。 非常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我家:我和鹿老师看的明明是一样的比赛,但她总觉得自己一看比赛就会输,而我这样的乐观派就觉得自己看的比赛中,运动员一直在夺冠。同理,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工作期间“摸鱼”a,就会产生“只要我一偷懒,就会被老板发现”这样的“倒霉蛋思维”。而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摸鱼”的时候,总是理直气壮,觉得“老板不会发现我的”。 回到本文开头的情境中,悲观的高考考生会自我暗示“我不能想好事,我不该做美梦,想了就不灵了”,而乐观的考生则会认为“我会成功的,提前憧憬一下有何不可”。 确认偏差 确认偏差也叫作“自我求证”。这种心理主要表现为以确认个人预设的假设为前提进行的信息搜索、解释、关注以及记忆的一种趋势。 假设某社会新闻中网友坚信某人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总能找到种种蛛丝马迹来佐证他们的猜测。就算最后警方通告解除了这个人的犯罪嫌疑,大部分人也不会相信,反而去寻求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想法,或者认为“警方侦查能力有限”, 或者因此产生各种阴谋论。这就是这类人用来确认自己的预设正确的“证据”。 如果一个人预先持有了“我一想好事就会倒霉”的信念, 认为自己是个“不祥”之人,那么他就会搜罗各种各样的证据,以证实自己的“不祥”。即使“吉祥”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也会告诉自己这是假的,是幻觉。比如,那些憧憬过后实现了的美梦,他可能会解释为“偶然”“巧合”“超常发挥”, 甚至直接从记忆里过滤掉这样的事情。 自我神化 不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的自我求证,其实都是自我神化的表现之一,即我们会高估自己对事件的影响,高估自己的作用,会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种种因果,都是自己的某个举动引起的。 自我神化往往较多地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当然,中年人也会有。这是一种“所有事情皆因我而起”的心态,把别人的行为和结果都归结于自己(尤其是错误的、不好的结果), 这不仅是一种将自己神化的错误认知,也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 由此,大家可以从中照见自己平时的归因风格,可以观照一下自己的内心:平时是不是有点处事悲观,做决定畏首畏尾,总将团队的失败揽到自己身上,遇事情总往坏的方面想,不相信好运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如果有,不妨就从踏踏实实看好以后的比赛开始,做出第一步小小的改变—放心,选手拿不拿金牌,与你看不看比赛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