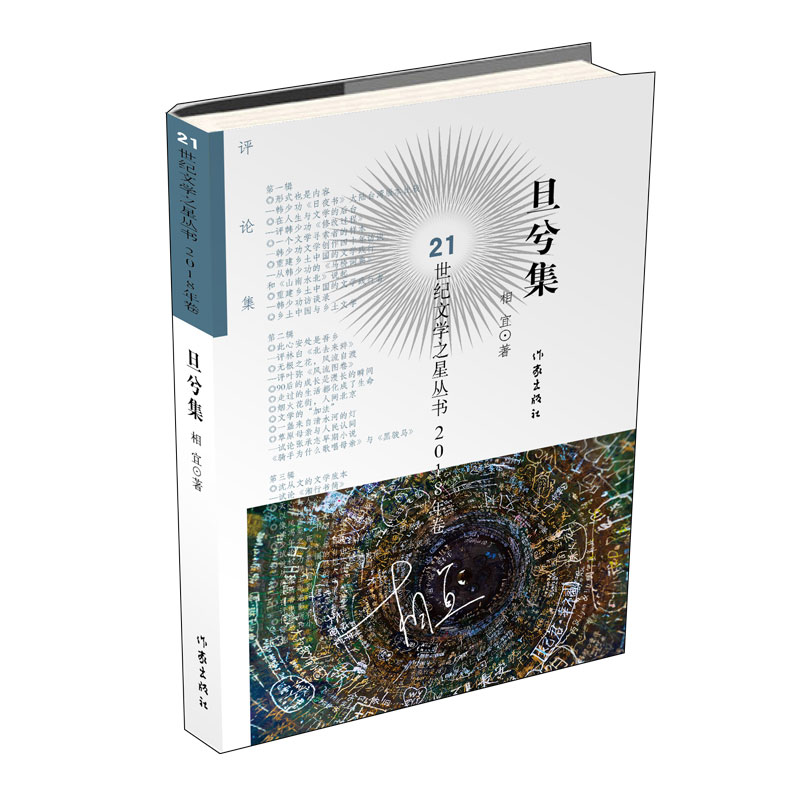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旦兮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ISBN: 9787521205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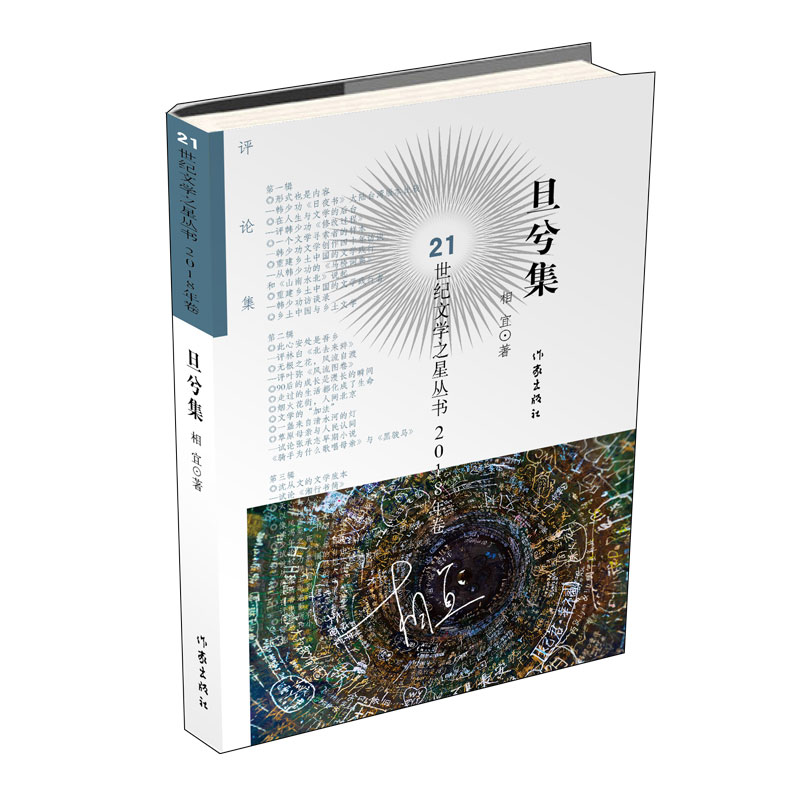
相宜,本名黄相宜,1990年生于广西南宁,壮族。2008—201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东吴学术》《文艺报》《上海文学》《天涯》《大家》等报刊发表过文学评论。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评论佳作奖,2018年度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形式也是内容 ——韩少功《日夜书》大陆台湾版本比较 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承载了韩少功从1968年至1974年的时光。时间中满溢着语词,一闭上眼,五光十色奔涌而来,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是韩少功绕不过也忘不掉的生命历程。他为此完成了代表作《马桥词典》,着力刻画马桥人的风土民情,为一个村庄立传。时隔十七年,韩少功创作《日夜书》反身关注知青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书写了白马湖茶场的知青岁月。从天井公社出发,你可以走向“马桥弓”,看到马桥人的嬉笑怒骂;也可以走向“白马湖茶场”,感受知青一腔热血和悲壮;当然,你还可以扑通一下,跃进汨罗江畔的“八溪峒”看一看画框中的山南水北。 韩少功走出天井公社已经四十年了,顺着人生往前走,却总是回到记忆中的保存关卡,萦绕在生命日夜中的是知青时代挥之不去的日日夜夜。那些记忆中的日夜在同样向前推移的时间中延展开来,两个时间维度交织交错,现实与记忆相生相应,这构成了《日夜书》的内容,也成就了书名。正如陈思和所言“《日夜书》可以看作是日日夜夜永不停息的时代之书”①。韩少功曾说过,对待两种题材自己比较慎重,一是完全不熟悉的题材,二是过于熟悉的题材。他在思考中回望,多角度审视自己,在不同的距离间辨析,直到找到最合适的距离让自己能把时光中的点滴看清,找到最适合的形式着手书写知青岁月和青春伙伴们。此时的形式,可以说是文学之外一个“大内容”,结构和文体本身也在呈现意义。 《日夜书》这个“大内容”,既保持了韩少功一贯的理性叙事风格,让我们看到原来的韩少功,又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韩少功。饱含感情又着力克制的平淡笔触,闪回和跳接,偶尔哲思的插入,人物横空出世,一以贯之的是他对文体探索的自觉坚持。但这种坚持是利是弊,同样在文坛激起各种声音:“《日夜书》虽被作者强调:是小说。但看起来仍然恍若一个大拼盘、一堆思想的碎片。”①“《日夜书》有一种接近日常生活的样貌,因果不是那么毫厘不爽,情节不是那么环环相扣,韩少功仿佛一把扯下了小说连贯性的面具,有意让生活在断续的片段中呈现出来。”②“如果从一般以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为主旨的小说叙述来要求的话,《日夜书》有很多思想随笔式的叙述会被认为是多余的,会被认为是有碍于故事情节逻辑发展的,但如果理解到韩少功在小说写作中往往会充当一位思想家的话,也就会发现《日夜书》的特殊文体蕴藏着作者的深意。”③? 其实,在我初读《日夜书》时也有同样的困惑,困惑“片断,纷杂零散,联想式的跳跃,突如其来的沉思,与理论假想敌辩论”①。这些叙述技巧并不像《马桥词典》般生机勃勃,线索满地,立体鲜活地展示一个村庄,而有一种精心设置的人为破坏感。这些如梦境般的讲述让我在阅读中积累即将奔涌的情感常常被迫切断,意犹未尽。难道讲故事的好功力真的在文体探索的路上被思想绑架了吗? 直至看到韩少功的创作谈,他提到台湾和韩国准备出版《日夜书》,“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做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越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以便境外读者更容易抓住故事发展脉络。虽与中国大陆版本的内容一样,但结构有所变化,篇幅有两三千字的削减,个别衔接性的文字也略有调整”②。于是,这就有了我手中读到的另一个版本:台湾版《日夜书》。我也在两个版本的对读中找到了解惑途径。 形式也是内容,内容也是形式,对韩少功来说,“体裁和形式只会有加法,不会有减法”③,两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应。 一、拓展小说的边界: 从《马桥词典》到《日夜书》 80年代,韩少功的创作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方式,而90年代以后的《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三部作品则是文学形式探索的重要成果,跨越时间长达十年,都采用了片断式的叙事策略,不再是传统的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情节化、线性化的叙事方式,既为文本创造了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又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体经验。韩少功的个人化的文学立场,就是哲思与叙事的杂糅、整体与片断的贯通,或者叫“在描述中展开思考,在碎片中建立关联”(《大题小作·文化透镜》)①。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到了《日夜书》表现得更有探索性,竟然采用不一样的剪接方式,创造了两个版本,他想通过两个版本,测试两种态度,一种是近距离,一种是远距离;一种是还原式,一种是拆解式;一种是“自然化”,一种是“间离化”。后一种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当然有些冒险,他还是忍不住试一试了。感性与理性,片断与整体,对韩少功而言是有机统一的。内容决定了形式,形式也是内容。采用什么形式,其实最坚实的根据还是人的生活与思维。不一样的创作意图决定了作品的表达形式,形式的差异也让作品内容在不同的表达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笔下世界便有了不同相面,立体而丰富起来。 其实,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来,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已经受到审视,也曾进入大规模的文学实践,留下一批先锋文学硕果。而今,当大多先锋作家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时,韩少功一如既往在传统与创新的临界点上探索,有效地拓展着小说的边界,并再次结出《日夜书》这枚奇异果。 也许读者会疑惑大陆版《日夜书》的文体,但没有人会怀疑台湾版《日夜书》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在大陆版本中有三个章节以词条形式表现,而台湾版本并没有独立的词条章节,而是把词条的内容融入了每个人物的叙述中,与传统的阅读经验契合。 对于韩少功来说,词条体是他在文体实验的道路上耕耘出的果实。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开始文体实验的第一部作品,作为长篇小说,它以一个个词条的形式松散而又相互连接结构了一个乡村的历史。“词典”这种形式,暗含了韩少功的态度,他放弃了那种以一己的观念去统摄一个世界的做法。他选择了词典这种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对世界的谦恭的态度。①?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②? 《马桥词典》主要通过“词典”的形式把文体实验的思想表现出来,一个个词条如散落的珍珠,被韩少功用一条高妙的线穿连,词条间的隐秘关联可以窥见,每个故事也相对完整,在结尾中,行走的故事在漫长的官路上又回到初入马桥的起点,这样打乱又形成回路的叙述,是韩少功开始明显进行文体探索的成果。之后的《暗示》更是在文坛的争议中继续将文体实验走到了文学与哲学、小说与理论的边界。韩少功在《暗示》中的散文化探索打碎了叙述的完整连续性,每篇文章独立成为对无边世界现实符号的思考,使得全书看上去就像是杂文随笔集,引发文坛种种争议,探讨此书文体何为。但是实际上,这种争议正是韩少功在创作的设定中就预料甚至所期望的,他的文体实验在谈论与争议中让人们意识到写作的多样性,正是他巧思之处。解读文本是有多种可能的,直面文本,不需要陷入评判的标准和文体定义之中,韩少功理解的各种符号背后的深意是他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理解的。也许,《暗示》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给读者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思考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这只是一个角度,而不是确切地强迫你去接受这样的世界。他在前言中提到的“文体置换”,也是希望用文学性的笔法让读者更容易地进入这个哲学、语言学命题中。在《山南水北》里,每一纸真实又奇妙的世界,给人陌生感却唤起人心最自然本真的柔软,正如那只有标题的故事——《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一页的空白,无限遐想,文体意识在韩少功的笔触下流动贯通,冲破边界,百无禁忌。 韩少功了解文体中的玄机,并一直在此努力。 大陆版《日夜书》的第11章、25章、43章分别以词条的形式,展现在历史时代中,与人密切相关的“性”“精神”与“身体”的种种特殊状态。在穿梭时空的叙述中,作者常常戛然而止,转入形而上的讨论。以词条的形式分类讨论各种生存状况,制造陌生感,给人一种新奇的角度,以此来看待生活中的不同面相,让读者思考与接近真实的生活。 郭又军之死是《日夜书》中最打动我的段落,那个光鲜亮眼憨厚的又军,在时代裂缝间生存的又军,对小安子和女儿无可奈何又关怀备至的又军,沉迷于赌博失落的又军,凝聚知青岁月的又军,他病了,也累了,却仍然选择“给这个世界一个清洁的告别式,一个不麻烦任何人的结局”。他的遗书是那么从容平静,日常的细枝末节井井有条却暗流汹涌,令人唏嘘。如果下一章节讲述的是又军组织同学会,或又军的葬礼,也许读者会潸然泪下,可是韩少功并不让这种伤感的情绪漫延。他笔锋一转引入了词条,“泄点与醉点”用理论与例子引出时代中各种各样被压抑的生理本能。作为生物的基本生理要求,当“性”在一个时代里,被压抑,被蒙蔽,被扭曲、变形,那么这个时代所遭遇的问题可想而知。当健康的生理要求得不到解决,人们只有通过其他途径来释放,词条之后的第12章转入荷尔蒙和肾上腺素交织交融的地下革命场景,就是特殊年代里人性宣泄的特殊途径。特殊的时代人性被压抑,或多或少便成了“准精神病”,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等身上都有时代面向的缩影,韩少功把这些常发生在生活中的精神状态,“陌生化”地表现。当读者发现所见与预想的情况并不相同,所有的线索让人感到陌生不知所措,可在故事中又分明感受到人性露出了尾巴,于是只能开始反思生活的原貌,韩少功的构想就完成了。 什么是陌生化? 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①? 这是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也就是“间离理论”),在他看来,间离的过程,就是人为地与熟知的东西疏远的过程。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或事突然变得非同一般,令人吃惊和费解,自然就会引人深思,并最终获得全新的认识。间离化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能使观众与剧中人物在感情上完全融合为一体,无批判地陷入事件中去。表演使题材与实践经历着一个疏远而陌生化的过程”②。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也是韩少功所认同的。对他来说“小说是一种发现,陌生化则是发现的效果呈现”。《再提陌生化》③ 一文中,韩少功这样阐述: 主体陌生化是另一种,相对难度要高一些,却是新闻业高度发达以后作家们更应重视的看家本领,体现于审美重点从“说什么”向“怎么说”的位移。网上曾有一些戏作,比如同样一则刑事案报道,用琼瑶体、鲁迅体、新华体、淘宝体等多种口气来说,会说出大为异趣的效果,分泌出各自不同的言外之义,亦即隐形的“内容”。在这里,形式就是内容,“怎么说”就是“说什么”。 两者关于“陌生化”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具体的来说,“词条体”对于完整叙述的打断,突如其来的哲思,叙述者“我”的介入,种种阅读障碍其实都是韩少功有意为“陌生化”的匠心。除了“陌生化”的叙述手法和“词条体”的文体表达,“拆解式”的叙述顺序也是大陆版《日夜书》的用心 之处。端上来的,老板娘只负责喊一声“菜好了”。 在别人家里吃年夜饭,一切变得规规矩矩。父亲更像一个远道而来主持会议的人,大家都左右围着他坐开,母亲、我、爷爷、弟弟。 父亲说,大崽,过了年,你还不打算去广东打工? 我懒得回答。 父亲又说,哪个高中毕了业不都是去打工的? 母亲帮了一句,年轻人个个都在外面,你一个人在月拢沙干什么?那两块石板还没踩够? 那两块田有什么好种的?要田好种,大家早在家里种了。父亲接 着来。 年轻人要出去见见世面。母亲跟着又接了一句。 我就是想种田。我说。 请你别笑我。我真的是想留在月拢沙,种田,种稻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象一片田野蔓延着水稻的图景。夏天,禾苗出穗,风过处,青叶点头,还是瘪着的谷粒逐渐有了重量,禾秆由嫩黄变成淡黄。稻穗的味,清香。认真闻,没有,不经意鼻子一扫,又有了。 这个时候,一只绿背脊、白肚子的青蛙,在水田里跳跃,伸直的后腿,宣告它又消灭了一只害虫。 八月十五过后的二季稻秋收,惬意悠长。一年里的最后一季,不用像一季稻那样,被鬼赶似的,担心秧苗是否过老,担心旱情是否来到。早点去晚点去都没关系,一把细锯齿镰刀扫过去,五六坡禾苗倒下,握成一手,放在脚边,一起身,一块田被剃成了瘌痢头。喝口水,再蹲下去,再起身,身后的禾堆,纵横有序,像正饶有耐心地下一盘陆战棋。 脱粒后,谷子运回家,搬上楼顶。秋阳下,谷子翻身,晒干。晒干的谷子,味道不再是稻穗那种隐隐约约的清香,而是一股沉甸甸的香,刚脆的香,太阳底下的香。 再回到田野,禾苗变成了禾草。禾草也干了,把它锁起来!扯四五根禾草,做绳子,一掐,一绕,一紧,一顿,好了。一个小圆锥就站在田野上了。半天工夫,一块田站满了禾草小垛子。它们这回下的不再是陆战棋,而是活生生的国际象棋。 我种过水稻。高中毕业后的夏天,我在爷爷的帮助下,跳过一季稻,插上二季稻。 是的,只有年过七十的爷爷帮助我。 整个村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我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十八岁。 我们是农民,为什么让田野荒废? 我问爷爷。 文章是作者素质的全面表露,文章的集合,更能将一个人的一切呈现无遗。尽管这只是她的第一部作品集,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已能够清楚看出她的志趣、学养、眼光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