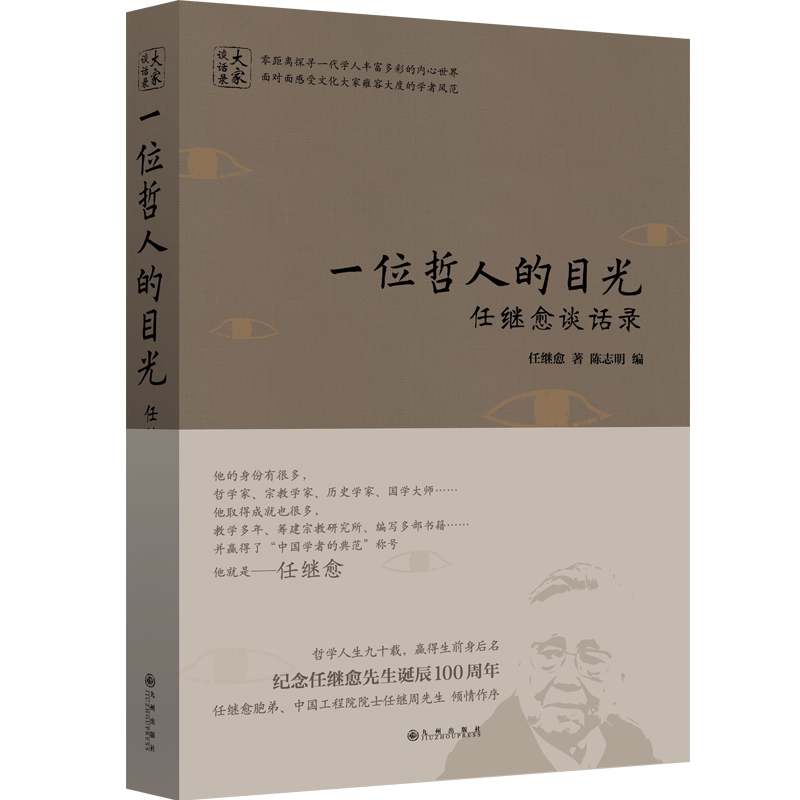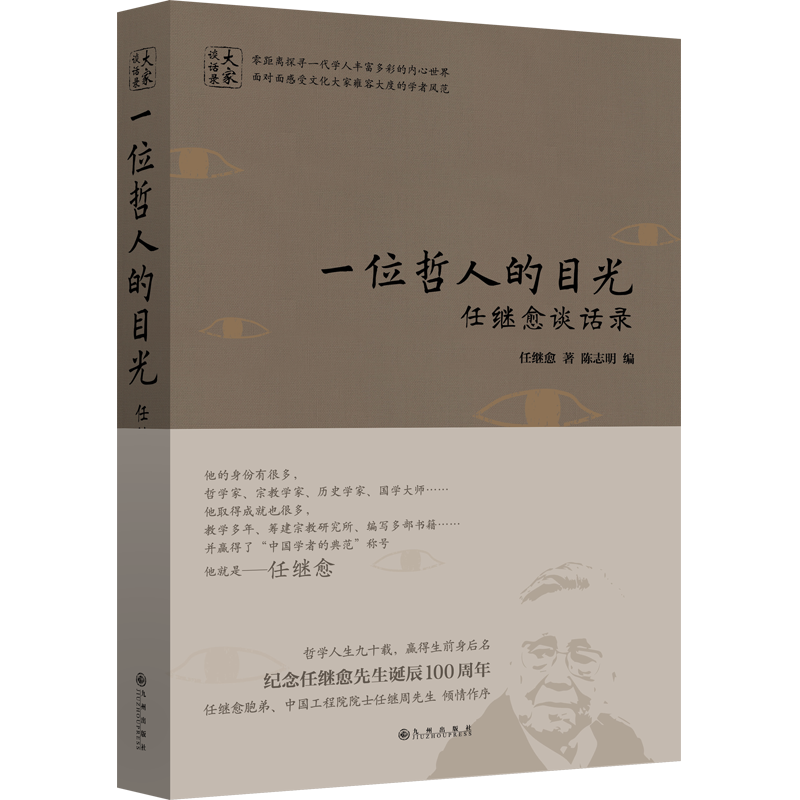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一位哲人的目光(任继愈谈话录)
ISBN: 97875108486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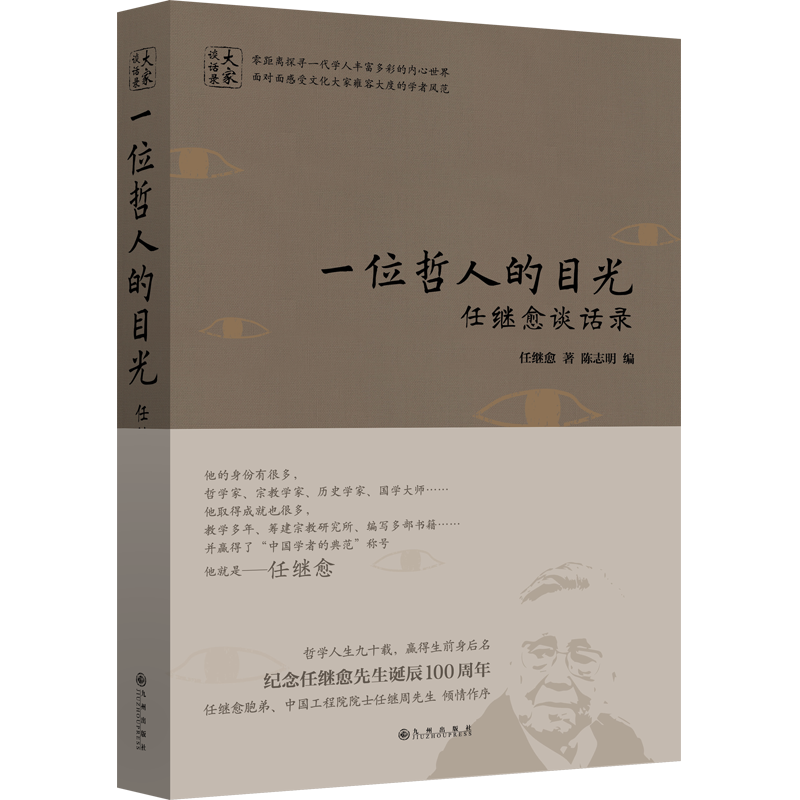
任继愈(1916—2009),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写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专著;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书。此外,还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典藏的编辑出版。
精彩章节试读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 访问者:白岩松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幻想,想追求点真实的东西,找最后的真理是什么,理想浪漫主义。没有想到毕业后找个工作都非常困难。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白岩松:1938 年您从湖南徒步走到了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大约一千多公里。沿途您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困,还有社会的败落,那么这两个月的旅行是不是彻底影响了您以后做学问时的一种心态? 任继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做学问也得拿出上前线时冲锋的那个劲儿才行,没这个劲儿也搞不成。 白岩松:我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当时您在昆明西南联大无论求学也好还是后来留校也好,您书斋的名字一直叫潜斋。潜心读书是不是给您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学问底子? 任继愈:在做学问上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马克思就说过这个话。我们中国也有这个真理,就是很平凡才叫真理。太离奇古怪的,很新奇的,那个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很朴素、很平凡,就是大实话。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1964 年毛主席倡议成立了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您当所长和教授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当初(指 1964年)要不是毛主席建议的话,您会离开校园吗? 任继愈:不会离开,我想我还会在那儿。 白岩松:那从您本人来说,您还是更喜欢校园的工作? 任继愈:是的,我喜欢学生。教书多年,我喜欢学生。 白岩松:先生非常注重中小学的教育,您也编过历史丛书一百一十本,那是面对中学生的。您撰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包括说话、包括一些发言之中,对于现在过于注重大学教育都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 任继愈:小农意识就是注重近期效益,信不过的我就不肯做,短期行为,不会见效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教育的根本还是在中学。回顾起来,我自己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就是在十二三岁那个阶段,后来发现某些研究生写论文答辩,看见有的学生的论文中标点符号还用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词不达意。这不能怨大学的老师,这是中学的底子没打好,小学没学好,基础没打好,改就很难了。在京剧艺术中这样的例子最明显,舞蹈也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底子打不好,后来就不好办了。 白岩松:古为今用这个问题很多年来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您是不主张古为今用的。 任继愈:嗯,我不主张。因为这样主张会产生一种流弊,虚无主义往往就是利用这个东西:用得着的我就来。真理是不能这么玩弄的,真理有它自身的尊严,你随便拿来用是不合适的。 白岩松:您好像也不主张厚今薄古? 任继愈:我主张实实在在的。 白岩松:我最钦佩先生的也是这一点。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整理佛教、儒家的资料,要是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如果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一个想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任继愈:我们也是借这个前人栽树,我们乘过凉,我们也要栽栽树,希望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这样整个社会才会不断地前进。文化在不断地积累,文化的特点就是积累,不能斩断,不像别的。政权可以是一刀两断,文化不能一刀两断。新中国政权与旧中国政权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但文化这个界限不能依从这个来划定。文化有几千年就有几千年,绝不是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始的。 白岩松:1956 年您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入党以后,包括入党以前您所积极追求解决的,也就是您作为用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任继愈:我始终看到农民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也讲了农民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从思想上看,从哲学史上来看,也发现中国农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有好些失误,在建设中走了一些弯路,这就是小农意识在作怪,是小农意识带过来的,意识没有改变,限制了新事物,对于走向世界、与现代世界接轨,都有局限性。 白岩松:先生从事学术工作已经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了,您自己怎样评价您这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 任继愈:我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怎么样评价。我是想大道理不用讲。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就是在集体中生活,依靠着群体,没有群体的话人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可以从群体中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从集体中拿些东西就要奉献一些给集体。如拿一杯水就要添一杯,或是奉献一勺,社会才能富有。文化事业也要靠大家向里面添东西,能添多少就添多少,若光拿不添的话社会非垮不可,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任继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富国强国离不开科技,但光靠科技还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代表一个民族的总体水平,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系,万万忽视不得。 (《精神的田园》,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 访问者:林在勇 林在勇:先生是大陆学界的哲学老人,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中国哲学史、宗教学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请您就人文学科谈一谈,如今文、史、哲划分过细,有否必要? 任继愈:此无非为方便计,大学把课程分别归于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古人则不然。譬如,司马迁既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韩愈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王安石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还是哲学家,文学上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个整体,浑然一体,如果面太窄,就无法继承古代文化传统。我们常说要接受古代优良传统,究竟如何接受?这不是某一学科的问题。唯有全面接触,才可能接续传统。以近代看,鲁迅非常博学,在文学、哲学、思想等领域都有很大成就;又如王国维,哲学史、文学史、考古学上都要讲到他。所以文化是个整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林在勇:先生所言极是。学者应重器局、规模,自封畛域,乃成其小者,必无足观。当然,还有另外一面,落实到具体个人,各人分珠量异,未必都能学史迁、昌黎。马援告诫子弟“画虎不成”的危险,建议莫如画鸿鹄,至少还能像大雁。以学界现状思之,结论似乎应辩证地得出。请问,先生治学中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 任继愈:只能说略有一些体会。首先要注意研究方法。我感觉自己年轻时念书念得也不少,可怎样才能解剖它?怎样才能看懂?自从接受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后,我才找到钥匙。这很要紧。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主要发现,是人类认识深化的结果。说到底也很简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某种思想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就要从社会存在着眼,社会存在包括各个方面,历史、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即原理与实际的结合。我们研究历史、研究思想也如此,要把原理和实际结合起来。实际是什么?历史就是实际,五千年之久的实际。脱离了这个实际,凭空说十月革命来了,一切都变新变好了,没那么一回事。过去我们吃亏就吃在误认为文化可以重塑,我看这恐怕不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有继承性。别的都可以新旧分开,譬如政权,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分出旧中国、新中国,文化却不能这样一刀切。说“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说 1919 年 5 月 4 日之前是旧文化,其后就是新文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四”前就已开始,新书籍、新思想已经出现,“五四”后仍在变化。所以说,文化不像政权那样可以一刀两断,它有继承性。 除了继承性,文化还有渗透性。中外也不能截然分开,互有渗透。佛教是外来的,到了中国就成了中国的了,与印度的不一样,发生了变化。冯友兰、汤用彤等前辈先生对中国哲学造诣很高,但也已经接受了西方好些东西,如思想方法等,已经不是纯粹的乾嘉方法了,与段玉裁、王念孙不一样了。文化渗透中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起了变化,与德国的,与莫斯科传来的,就不太一样。研究中国哲学史须注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摘也摘不清,去也去不掉。 林在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有这么强的接受基础? 任继愈:第一是客观需要,当然政府提倡也是一个因素。光提倡不行,反过来说,有客观基础的东西,反也反不掉。历史上排佛,有几度官方拆庙毁佛,但佛教终究没有被排掉;再如“文革”中打倒孔老二,砸孔庙,废“四旧”,结果孔子打不倒,“四旧”也废不了。文化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凡有客观需要的东西,什么力量也反不了的。当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依靠政权来推广,马克思本人最倒霉时连饭都吃不上,伙食费都没有,他的学说不是靠势力,而是靠本身的吸引力慢慢地使人们信服。当然,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形式主义,那是推行它的人造成的误差,随着历史发展总会逐渐得到解决。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林在勇:您应该说是师承汤用彤先生吧? 任继愈:也不能这么说,近代大学毕竟不是私塾。过去私塾是住到一个老师家里,现代大学不是这样。我们当研究生时的制度比现在要好些,导师有正、副二人,我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副导师是贺麟先生。我做中国哲学史的毕业论文,而贺麟先生并非研究中国哲学的,他的专攻是黑格尔。这样,我就也读了不少外国哲学的书。 林在勇:是否应该说您有幸从许多前辈大家那里获得了教益? 任继愈:大学是个工厂,不是作坊。讲唯心论的熊十力先生,我听过他的课;梁漱溟先生那里,我去拜望请教过;胡适在北大讲文学史,讲中古思想史,讲王充,我听过;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课,我从中也有收获。所以,学习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单一师承哪一个。 金岳霖先生的课我也听过。抗战前我是北大学生,你们华东师大的冯契先生原来是清华的,抗战中我们都合并到西南联大。他是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我们都必须听金先生的逻辑学必修课。冯契先生与金先生的思想体系比较接近,所以他从导师冯友兰先生那里得到的没有那么多。这就好比走进一个大百货店,看你自己在哪个柜台选取了。 林在勇:您在方法论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师从诸位先生还只能说是打个基础。 任继愈:是的。看了许多书,回头看,看书也值得。当时不太理解,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便有领悟。 林在勇:像您和冯契先生这一代哲学家,都比较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与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那一代哲学家有了差别。今天来回顾,您认为彼此各有什么所长? 任继愈:彼此共同的是爱国主义。当自己的民族遭受欺凌、文化被人轻视之际,我们都想要发现,中华文化有哪些是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甚至有哪些是将来可以对人类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 七七事变时,正是暑假。学生不能回北平,就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我当时是北大三年级,去临时大学报到,读了半年。长沙屡遭轰炸,并不安定,学校决定撤退。一部分师生乘船,经香港绕道安南(越南)赴昆明;一部分体检合格而又自愿的人员参加步行,从沅陵、贵阳一线走着去,有三千里路程。我参加了,有些老师也参加了,如闻一多先生、生物学家李济同先生,他们当时是四十岁左右。步行相当艰苦,好处是亲眼目睹了中国很贫困的地方…… 林在勇:三千里路会给人不少思考的机会,一路步行也用了不短的时间吧? 任继愈:走了两个多月,这种教育很难得。且不说风餐露宿、冒雨跋涉,有时还遇上绿林好汉。湘西虽多土匪,但学生一没钱二没武器,提前一天派人到必经前路向剪径者打个招呼,就不来骚扰。 林在勇:好像那时连土匪都比较尊重读书人! 任继愈:(笑)爱国主义对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一个共同心愿。那时品评某个人,抗日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到达西南联大后,条件仍很艰苦。校舍是茅草顶,窗户倒是能开能关,但没玻璃,关不关都一样。学生听课晚去没座位,隔着窗户也一样听课。幸好昆明的冬天并不冷,夏天也不热。 林在勇:先生能否讲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哪几个重要阶段,及研究领域的变化和学术脉络的延展,其中肯定有许多东西能予后学以启发。 任继愈:我与哲学界几位前辈的不同在于,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佛教、道教、儒教(儒也应被视为宗教),这三教的影响和关系,不能不予以重视。我之所以研究佛教,是因为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中,少不了佛教这条腿。以《红楼梦》中秦可卿的丧事为例,就兼有佛道,一边是和尚,一边是道士。民间并不把佛、道看作对立的两派。其实对儒家也是这样。佛教里也主张儒家的东西,出家人若不忠不孝,也成不了正果。在行善积德这一点上很一致。所以我很注意三教的关系,注重这三大支柱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林在勇:先生是从何时起比较清晰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阐释的? 任继愈:这随着我的研究逐步深入而有所变化。我初涉中国文化问题时就发现,佛教不搞通,就研究不下去,这好比修铁路,有一个隧道没打通,怎么过去呢?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即为儒、佛关系。这并非只为找个题目,而是实际遇到了这样无法回避的问题。后又发现道教也不能略过。更为明确时是在宗教研究所成立之际,此后即大规模地从事这项研究了。 林在勇: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对宗教问题似乎着墨不多。 任继愈:学术是发展的。我也不过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对某一局部有所推进。没有前人的成就,也就没有我的一点成绩,文化的继承性就在于此。有的学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不对。成绩不能光记在自己的账上。不少大学用我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教科书,说我做了这样那样的贡献,其实无非是让我来主编。让别人做,不是也行吗?全揽为自己的成绩,以为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这就不实事求是。 林在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印了七八次吧? 任继愈:现在还在印,1961 年开始编,三十多年了,印了多少次我也记不清。 林在勇:您自己相对满意的著作是? 任继愈:我还没有自己满意的著作。罗素晚年写了一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我也计划写一本简明的《中国哲学史》,不引经据典,只把主要线索、结论写出来。 我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七册),其中有些资料性的内容不必要。结论固然要根据资料来做出,但资料很占篇幅。八卷本的《中国佛教史》,我也想重写成一卷本。这两项工作现在尚未着手,所以也很难说满意不满意。 林在勇: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力图使您的哲学研究体系化? 任继愈:我觉得,这一代人,倒也不必急于建立自己的体系。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建立新的体系,还需要一些条件。 诸多条件中至少有这样一条:要全面掌握世界学术界的已有成果。目前我们对世界学术情况还不太了解,并非没有引进来一些东西,但进来的是否果真是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呢?有时候,流行的并不是有价值的,也未必是有代表性的。今天西方有许多东西供我们选择,我们还须有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才能做出取舍。 朱熹的体系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达到的哲学准备和学术积累,有全面的掌握。他所作的哲学解答,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当时的人们能接受,认为他的解释能够成立。现在我们的新体系解答不了社会涌现的诸多问题,说服力不够。你可以自认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人家不相信,效果就差,这其实说明你本身还没有弄透。相反,汉朝董仲舒那一套体系,看起来很粗糙,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之类,但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就有其社会效益和文化的价值。董仲舒影响了数百年,朱熹的影响也有数百年,而我们现在构建体系,要取得那样的效果,恐怕条件还不够。这倒不一定说哪个人不行,而是说时代就是这么个状况,做不了,做不出。 林在勇:那么,先生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或者可以称之为“文化责任”的,是什么呢? 任继愈:要清醒地认识目前的状况,以此决定自己当做什么。我们这一辈,包括你们这一辈,应从资料积累入手。资料理清摆在这儿,后世必有能者兴。他们就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尽出些个人论文集,多半没有太大价值,不消几天就被遗忘、抛弃。徒耗力气,浪费纸张,用处却不大。若真正是想为文化做一点贡献,还是要先整理资料,于人于己,都有用处。我搞《中华大藏经》就是这个意思。总共有 106 大册,十年才完成,现在已经印出了 70 册。我们把现存各处的《大藏经》全都汇集起来,搞了版本互校,一书在手,方便后人。将来还可输入电脑光盘,检索起来就方便多了。 哲学史研究上我极力讲儒、释、道三教关系。集体编著主要是跟与自己思想接近的同志、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做。哲学也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它会影响自己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审美趣味等许多方面。 林在勇:一位大家的成就也不光是体现在他写下的文字里边,应当说,他所达到的造诣和境界未必就能轻易被外人窥到,还须看一看他的弟子如何承传绍述、发扬光大才行,学术史上的一般情形大概是这样吧?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学生辈人物? 任继愈:例如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解放初在我班上的研究生,北京大学的汤一介,人民大学的杨宪邦,中国社科院的余敦康,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晚一些的如李申等人。 林在勇:李申先生比较年轻,是您 80 年代的博士生吧?他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从中也能看出您关心的问题。 任继愈:是的。我觉得应该跨学科地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过去一般强调唯物论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说是科学推动了哲学。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考虑,哲学是否影响了自然科学。正反两方面都看一看,可能会更清楚些。我的博士生金正耀,原来学化学,他就从技术上来研究道教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我觉得,道教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还有操作的部分,譬如炼丹。不把这部分搞清楚,就不全面。 林在勇:我们现在的哲学史研究,缺陷就在于大量的古代实际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理清楚,就急于构建体系、宏观论述。 任继愈:要扩大视野,不能只局限在文献里。 林在勇:恐怕连文献还未曾尽量占有。 任继愈:这样确实不行。现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室主任宋立道,是我最后一个博士生,也曾经是我的硕士生,他先做移民课题,后来研究东南亚的宗教。研究道教的还有四川大学宗教所的陈兵,是我 1978 年招的硕士生,现在是教授了。 上海社科院的业露华、潘桂民,现为安徽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的赖永海,研究佛教,现在是年轻的博导,是我博士生里面已经带博士生的一个。上海和南京很近,你们可以多联系。还有像复旦大学的洪修平,他是孙叔平先生的学生,不是我正式的弟子。此外,跟我一起合作写佛教史的杜继文,是社科院的博导,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 这些同志都各有专长,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所深入,但目前还没有谁把这些方面都综合起来。 林在勇:我翻检了先生历年发表的数十篇论文,1963 年的《哲学研究》所刊载的《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一文,您近年出版的一卷本《自选集》里好像未收,甚至附录里也未存目。先生能谈一谈吗? 任继愈:我写了这么多文章,但从来没有提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我有意避免它,因为此中有很多政治的干扰。如果总是按照当下需要,古为今用地“用”它一下,那怎么行呢?历史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可改动,不能改造,想改也改变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往往是领导上有个什么想法,只言片语,下边听到一点儿风,接着就往哪儿刮。这是糟蹋学术。学术要有尊严,不能翻来覆去。讲“儒法斗争”时,这个也是法家,那个也是法家,哪来那么多的法家?学者不应当乱讲话,如果真正相信真理,可以沉默。不说总可以吧?我觉得学术界也要“自重、自爱、自强”,像妇女界的口号那样。 林在勇:学术界的地位跟旧式妇女比较相似。(笑) 任继愈:学术界要自重、自爱、自强,不能跟着风头跑。 林在勇:先生此言,不仅针对过去,对时下同样有意义。只要大气层不消失,地球还在转,总归会有东西南北风。 学术上的迷失,有些是认识或功力问题,有些是投机所致,是人格问题。我们注意到,先生在 50 年代、60 年代初发表了大量文章,非常活跃,研究领域也非常宽广;而“文革”期间,先生的名字几乎不见于报章。这正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当来自政治的压力太大时,学术的话语已经无从说起了。那么,是否还可以这样说,您认为:尽管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也带有特定时代的色彩,但还属于在一种思潮之下大家的共识,某些现象还应该算在学术的范畴之内? 任继愈:是的。所以我在《自选集》里就说,也谈不上我有多少贡献,我只是说我自己想得通的一些东西,想不通的我没有跟着凑热闹。 林在勇:据晚辈浅见,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否可以这样来简单概括?一是先生较早注意到,佛教问题倘若不搞清楚,会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障碍。据先生刚才的介绍,早在读研究生的阶段就开始致力于此。从 60 年代起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史,旨在理清儒、释、道三教关系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二是先生对道教及其源头上的老庄(主要是其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由此也对古代科技史,例如对中医和古代哲学的关系等等,从 50 年代即全面研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些是否是先生的主要贡献? 任继愈: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吧,贡献还谈不上。 林在勇:上述方面当然也并非没人谈过,也不是只可以有一种讲法。不过应该说,还是先生关注得比较早,强调得比较多…… 任继愈:算是比较自觉一点吧。 林在勇:直到 80 年代,从您的弟子如赖永海、李申、金正耀等人的研究方向,还可以看出您早年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任继愈:做论文、定方向总要师生双方商量。 林在勇:佛教界人士对佛陀的认识,和您作为人文学者的见解,显然有着许多隔膜。对这种异议,先生怎样看待? 任继愈:我认为佛教徒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们对所信仰的对象不敢怀疑,佛经内容是否都对,不能提出疑义。信是第一位,底下再说研究。我们不承认这个前提。我们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来对待的。我跟佛教界的高僧、居士来往比较少,原因在于一涉关键处,彼此会发生障碍。信仰是他的自由,你也不能强加于我呀,只能互相尊重吧。我尊重他的信仰,不要求他们相信唯物主义,但是我也不能跟着他们跑。马克思曾经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跪着看别人就会看得比自己高。佛教徒就是跪着看佛,佛高得不得了。让我们看呢,释迦牟尼也是人,是一位创立了某种学说的思想家,一位开辟了某个领域的伟大人物,而不是碰不得的神。 林在勇:让我们姑且假定这样一种人文科学的态度,也许也会错过些什么。佛教界高僧大德对世界的领悟、体味也自有其独到之处,而这正因为他们有“信仰”这个前提,通过并不唯物的方式。先生对此怎么看? 任继愈:宗教有排他性。佛教徒不相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里面有什么真理,这至少不合乎事实,世界上信基督教的人比信佛教的人还多嘛。难道唯独佛教中有真理,其他教派就未曾看到一些真理?同样,也不能说哲学家就完全看不到宗教界所体会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感觉到了某些东西,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而已。所以,不宜太狭隘,世界本来就非常复杂嘛。你喜欢红色,大家就都必须着红装,这不行;你不喜欢就不准别人喜欢,那也不行。宗教问题也一样,佛教讲自己的道理当然可以,但不应去骂基督教是外道、邪教。 林在勇:郑板桥有句诗“外道天魔冷眼看”,我们不妨改一个字,说“外道天魔热眼看”,以最大的同情看一看热闹的世界中不同的价值。从先生刚才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先生虽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观照宗教史,却没有那种曾经是理所当然的“俯视”意态。 先生您能否对 20 世纪的学术作一评价?它肯定有不少伟大的成就,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就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但它显然也存在缺憾。究竟 20 世纪能在整个学术史上留下哪些东西?由此,您能否对下一世纪的学术作一展望?或者换一种问法:假如您再有一生的可能,重头来过,那么您将会怎样做? 任继愈:开放不可逆转,也不可避免。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交流,不交流就停滞了。所以,21 世纪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中外文化健康地进行交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自我提高,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过去是外边来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这恐怕不行,要有选择。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要允许慢慢地来挑选。譬如匆匆忙忙到商店,进门就抓一个来,也许也算买到了,但是不是对你合适的东西呢? 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是生活文化,吃喝穿戴,一眼就看得到;二是观念文化,藏在内里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不是一眼看得透的。真正代表一个民族性格的是观念文化。观念文化层面上的交流若要深入,需要时间。譬如一部著作,也不是今天买来明天就全部读完读懂了。中国自己的孔孟老庄,几千年来真正弄懂的人并不很多。外国有他们的“孔孟老庄”,要弄懂一样不容易。所以,我不认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会很快得到最大成效。回顾历史,佛教花了好几百年才和中国固有文化合为一体,我们也接受释迦牟尼是中国人了,不把佛当外国人,和孔子一样,取得“绿卡”了嘛!将来,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也达到了这样的融合程度,那么我们的新文化就呈现出来了。 林在勇:先生认为融汇中西的新文化,须水到渠成,还不能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达成,恐怕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这是否隐含着这样的意思:20 世纪是一个过渡期,它的学术不是某种“完成了的”东西,假如一千年后的人们来写学术史的话,我们 20 世纪这一段,就好像是盛唐文化之前的准备期——南北朝一样。 任继愈:我们无非是为后人张本,作些铺垫。所以,不要自我估计过高,以为到我这里就可以总结了。时候未到,谁也总结不了,倒不是谁不愿意做那种总结。 林在勇:先生的意思是说,21 世纪要做的,在文化上是交流、积累、准备,具体到学术上就是多做资料的工作。 任继愈:不要误以为资料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方面,学界的基本功亟待加强。比如说要介绍外国的东西,准确翻译,正确理解,把文风也传达出来,相当困难。《老子》古文今译,我做了好几十年,直到前年才有定本出版。中国自己的古文今译尚且如此,要引进外国的文化也一样会碰到许多难题。 林在勇:先生在 50 年代初发表《老子今译》,当时还特意括号加注“初稿”字样,这也就是表示准备不断地理解、吃透它。 任继愈:翻译不容易……了解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审美趣味等许多方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总起来看就好像人的两条腿,但自然科学这条腿很长,社会科学那条腿很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自然不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