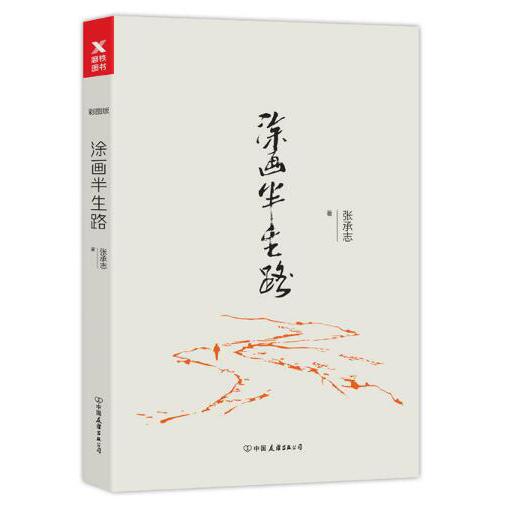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5.87
折扣购买: 涂画半生路
ISBN: 9787505741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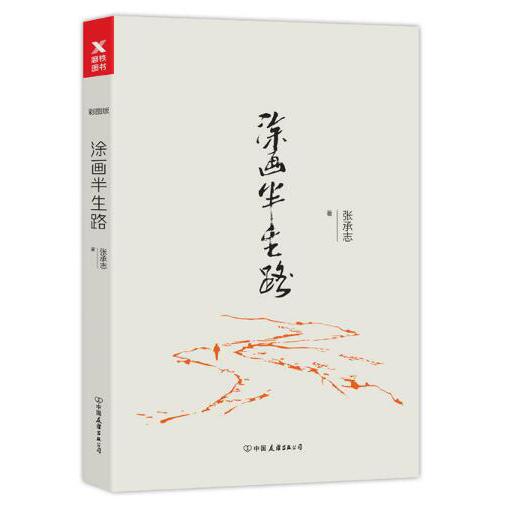
张承志,回族,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作家、学者。同时也是“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创始人。1948年生于北京,1967年从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插队,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1981年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并熟练掌握蒙、满、哈萨克三种少数民族语言。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后来的作品转向宗教题材,引起过不少争议。80年代以小说创作为主,90年代至今以散文为主。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已出版各类著作30余种。
草原十张画 摇篮 如它的蒙古语名称(tal,平原,草原)表述一样,乌珠穆沁草原的地理特征,是平原,是舒缓和辽阔。以前我不懂怎么有个名称叫干旱草原,我没留意这里缺少河流,没发觉井和水泡子(淖尔)只是脆弱的水源。乌珠穆沁或许就因此不能成为历史的中心,虽然它的确是草原的奥深。在乌珠穆沁,牧民们不用像哈萨克人那样劳累数百公里走场,也不用似西藏人一般,驱着羊群沿路奔波好久才能进入放牧的场地。 草原的辽阔曾具有封闭作用,所以古老的磨制小刀能上溯匈奴时代。它还具有神秘的消融性,走马灯般,过往的民族都杳无踪迹,剩下的蒙古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考古是困难的,人群文化类近,包括游牧技术的传统都代代因袭。 谁也没有料到,当这里被铁丝网划分为以户为单位的私用营地以后,亘古的牧草居然不够吃了。一页已经呼啦翻过,一切都迎来了质的改变。愈是目击今日,我就愈是惊讶不已——我们居然是最后一代见识了古老游牧方式的人。 生命(春) 这个季节生产和牧人意识的核心,都是生命。春天只是一种风吹雪的代名词,他们称春季为“接羔时节”(tul ?aγ)。对牧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重要的了,此时迎接的不仅是生命,还是财富。 由于生产对象和财富、家畜生命的一体化,这里很少有无视生命的例子(如对私生子的歧视)。游牧技术的秘密,就在于唯有牧民能像对待人一样“看”家畜。不用说,在这干系重大的季节里,学龄儿童处于两难境地。牧区学校在这时放假,不仅由于忙,不仅由于儿童在接羔生产中分担着重要的任务,还因为念书远不及接羔中的接触生命重要。 白色(夏,上) 白马比喻夏季的奶食和丰饶。 虽然有酷暑和暴雨,但是青草茂盛,马儿肥胖,舒适的日子来了。繁忙一春之后,搬到绿油油的夏营盘。羊和人都懒洋洋的——羊群像粘在草地上一样原地吃草,人消磨着酷暑和丰腴。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驻夏”,它用以描写这种日子特别贴切,以至我总怀疑它来源于某种游牧的启发。 “白色食物”(?aγan yidege)包括奶食和奶酒。酸奶豆腐和鲜奶豆腐、黄油以及美味的奶皮子,是生活中的佳肴。还有奶酒,它是一种低度蒸馏酒,它给蒙古人以享受,也浇灌了酗酒奢侈之风。 喜庆(夏,下) 在财富的积累之上,文化和传统诞生了。 草原的游艺聚会,多是与游牧生产和传统宗教联系的。祭敖包,是最基本的丰足吉祥庆典。虽然也有“白月”(汉地农历春节)的祭典,但它一般在夏末举行,水草膘情都最为肥美之际。百姓们惯用宗教意味清晰的词儿(nair)称呼它,而并不用意为戏耍的新词“那达慕”。近年来恢复了由喇嘛主持的方式,各庙宇在研究之后,排列了各地的当祭敖包。祭会的宗教内容有高僧诵经,而赛马和摔跤,则是祭典中最基本的两项世俗竞技。 迁徙(秋) 秋天的草结了实,前面就是可怕的严冬。牧人把老小留在毡包瓦房,轻便出牧,追逐多汁饱油的草。走场(otor)这个词应该古老至极。走场的含义,演变为多搬家、吃好草、少饮水,使牲畜油膘结实,还有冬天雪灾时逃出围困。 游牧的本质就是迁徙。1970年前,乌珠穆沁草原牧人的年迁徙数,有15~20次之多。也就是说,大约到1970年为止,游牧方式在北亚草原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个世纪。 雪国(冬) 一年有一半是严寒冬季。气候在那时(仍以1970年为限)如古代一样冷,需要穿上皮裤、有马蹄袖的大羊皮袍子、毡靴以及皮帽子。青营盘,避风坡,补充盐——经验决定着生死。即便在严冬,放牧也一天不少,虽然出牧晚一些。 怕冷的人,未曾深思熟虑就慌张选择了更结实的土木房屋。人们已经快要忘了——车和毡组成的棚圈,也曾奇异地御寒。那时早上发抖的山羊挤在车下,死命挤在雪下取暖。无疑那样的防御是薄弱的,带有冬贮草的房子,亘古以来就充满了诱惑。 血脉(社会) 几个不同来源的家族(ayimaγ),恰好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几块基石。如一切东方的民族一样,所有政治的、阶级的和表面的争斗和睦,都围绕家族关系展开。 在牧区,家族和家庭的第一含义是生产性的。家,是一座(ger)或一组(ayil)毡包,是一个男出牧、女守夜的牧人小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游牧单位。 牧人(人) 古老的游牧生活造就了“mal?in”,即牧人。 这个词汇,这种人遍布于整个阿尔泰语系覆盖的广袤北亚。从观念到语言都是一样的,比如在哈萨克语中牧人被称为“malxe”。不用说,-?in和-xe,都是表示“者”的后缀。由于骁勇强悍,由于敬天爱人、童叟无欺,他们成了一种古典,成了一种传奇,成了一种被向往的形象。 必须男靠女、长靠幼。那里的男女拼成一对,如一个浑然的太极。加上长者和小孩,大家各司其职,男出牧,女挤奶,老人警示经验,儿童看护仔畜——家庭俨然是一艘草海里不沉的船。 朋友(畜) mal,也就是牲畜,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核心。 经济学不能洞彻丰满的游牧。牧人与牲畜的关系,不同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牲畜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主食、朋友。马有骏马,牛通人性,人性被牲畜的生命启发了。 Mal——牛、马、羊、山羊、驼,合称“五畜”。匈奴云“使我六畜不安息”,可能加上了牦牛。它们是牧人的依靠,也是牧人的朋友。至于狗,这种更加灵性的家伙虽不可或缺,但它不算牲畜。 古歌(艺术) 环境和生活的调子,创造了艺术形式。马鬃和肠弦相摩擦,奏出的音质只会是悲凉的。马头琴的物质特性,使它完成了对舒缓的蒙古古歌的伴奏。两根肠弦间的呜咽,强调了大草原的平坦感觉,也暗示了它的单调。当然是歌在前、乐器在后。但细细端详,马头琴起源的古老是无疑的。 游牧世界并非缺乏变化。哈萨克崇山峻岭的牧区,养育了另一类乐器,是急促宛如蹄音的冬不拉。 要注意,冬不拉也是使用肠弦。这是它起源古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