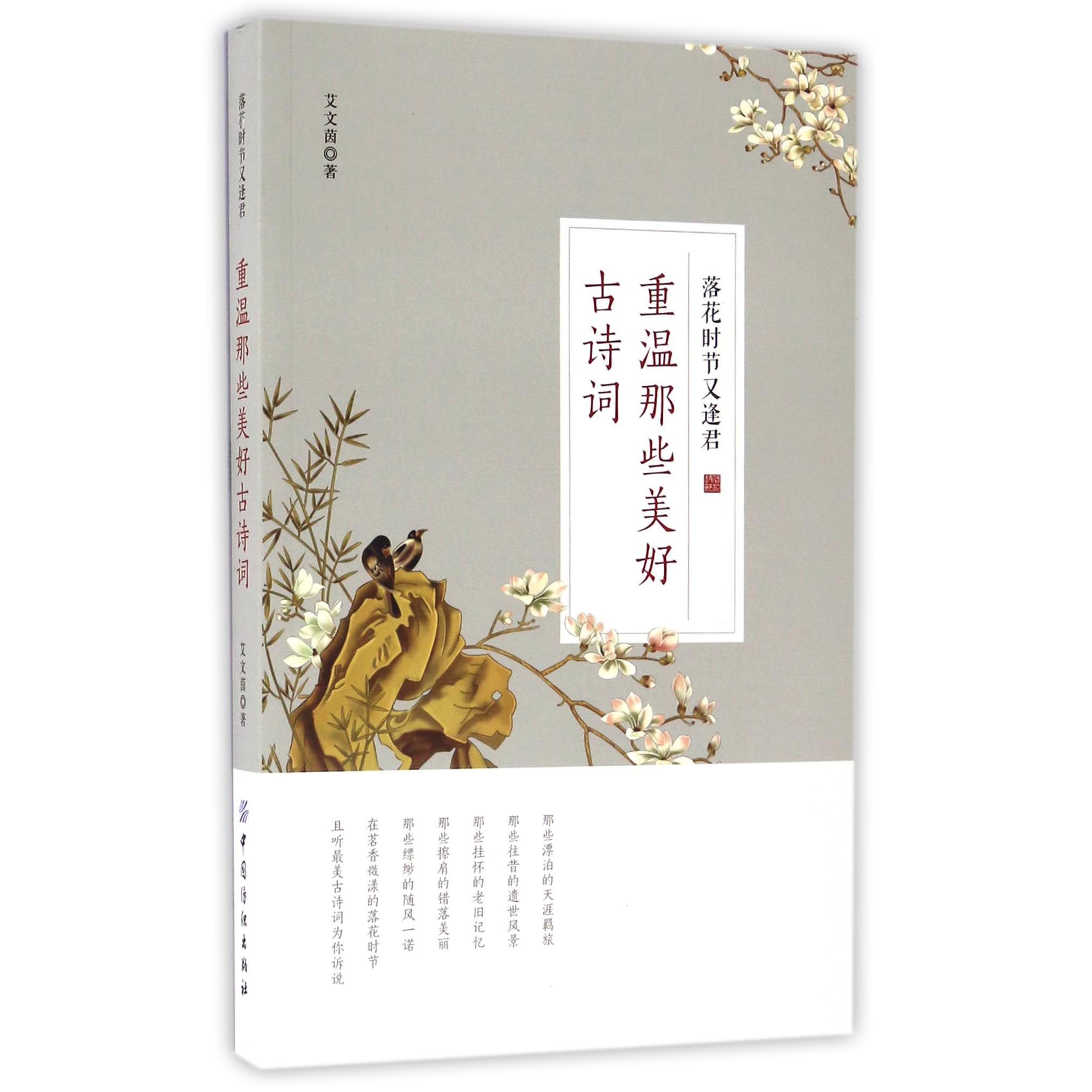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纺织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1.70
折扣购买: 落花时节又逢君(重温那些美好古诗词)
ISBN: 9787518029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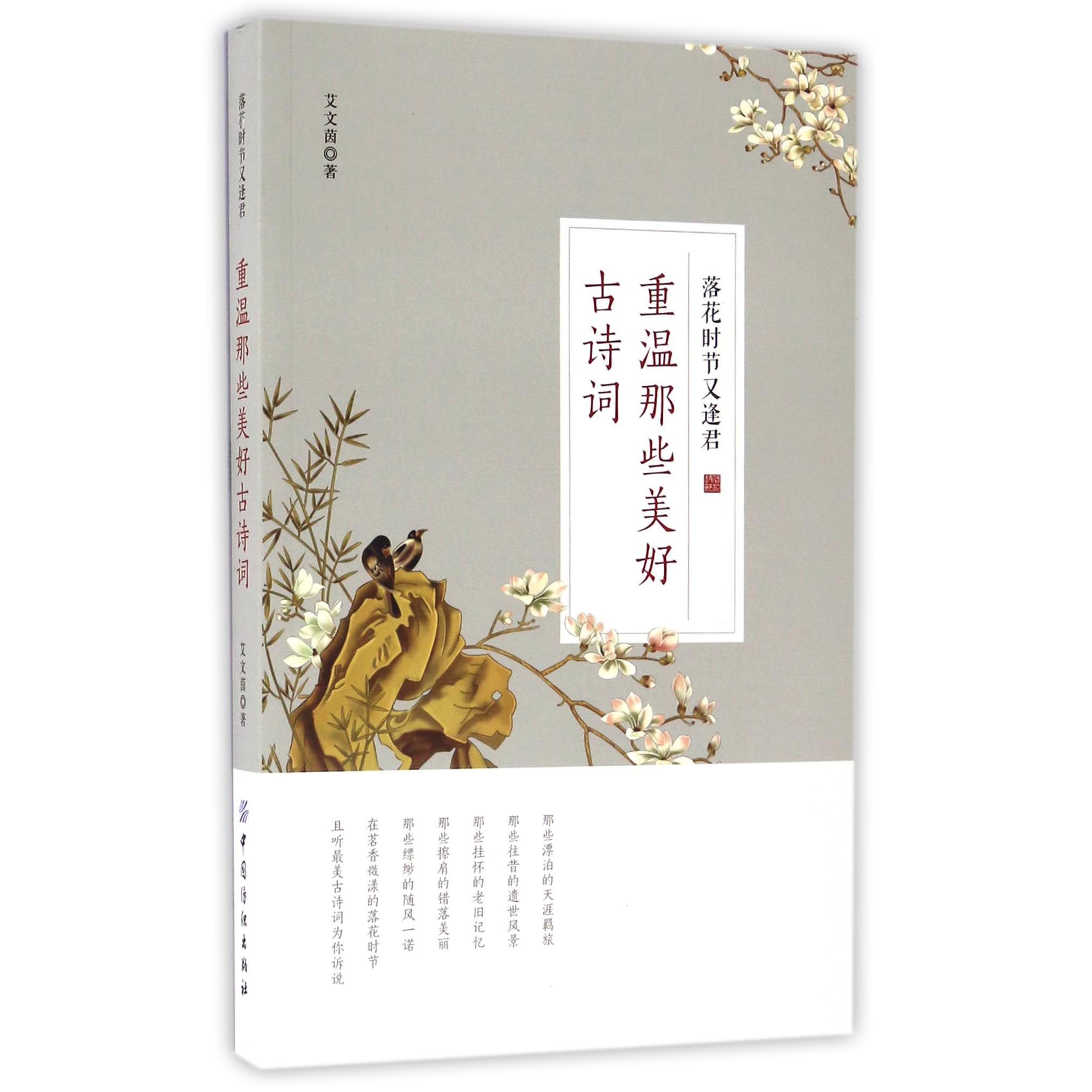
艾文茵,原名王欣然。一支墨笔,满身花雨;三两情思,几盏人世。倾心褪了色的往事,挂怀未讲完的故事,摩挲斑驳了的历史,重翻风霜里的旧诗。著有《撒哈拉不哭泣:三毛传》《爱过,才不枉此生:陆小曼传》等。
1 作个闲人 乐尽天真 行香子(苏轼)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 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 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 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说世事一场大梦,沧桑历尽后人反而达观了 起来。 晓行暮宿、宦海沉浮,为人构陷、一贬再贬,亲 见过多少丑恶的嘴脸,也曾在流放之路泥足深陷,看 破多少奥援有灵的钻营,旁观过几度政以贿成。 正因为他是苏轼,哪怕他谙熟所有的所谓规则, 哪怕尽可机关算尽搏功名,再不济也能充耳不闻见溺 不救,可他那天生的一颗七窍玲珑心又总是不饶不依 ,呼唤着:“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他酿酒,并饮酒成瘾;他擅行、楷书,笔势尽展 法度;他无肉不欢,也爱参禅打坐;他身陷“乌台诗 案”,仍旧笔耕不辍;他的道德只拘束他自己,却宽 恕着别人;他是士大夫,是佛教徒,是以文章而名天 下者,也是*平凡的耕稼陶渔人。 *为难得的是,无论将苏轼置于怎样的境况里, 都不能灭他那种蓬勃的精气:好的坏的,坦然面对、 照单全收。在你以为他已被催逼得渐行渐远、踪迹杳 然的时刻,他只作淋了一场无防备的雨,而后满身花 雨又归来,而后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们崇拜他、倾慕他,便也难免神化了他。事实 上,苏轼并非生来豁达无争。道理如同见多了生死, 也便把一生一死视若了一来一往的平常。经历是可以 荡平人的锐气与哀婉的,多几番经历,也往往等同于 多看透了几层道理。 宿命希望他活得透彻,所以不愿轻易予他顺遂, 为官如此,为人夫也是一样,历尽了离恨与郁郁。在 官场上,他三起三落,*终客死他乡;在生活里,他 相继痛失三位伴侣,*终鳏夫独居。 与**任妻子王弗的缘分始于在中岩书院读书时 ,苏轼的老师名为王方,是王弗的父亲。 在中岩书院附近有一泓未名的绿水隐匿林间,偶 有清风拂过,掠起层层波纹,看得人心荡神迷。苏轼 得闲便会来此流连,玩性大发地用力叩掌,引得岩穴 中的鱼群闻声骚动,纷纷朝着声音的方向游来。 王方也极爱此地,于是便在某个踏春*邀来诸多 文人雅士及自己的得意门生,给此水题名。为求高雅 牵强附会者有之,游离其宗落入窠臼者有之。在王方 看来,大多的投笔都并非见心见性,那些所谓才子的 才情也未免名不副实。 直至看到苏轼的答案,只短短三个字,“唤鱼池 ”,既雅且新,有声有色,王方不禁拍案叫*。*到 夸奖的苏轼正忙不迭地自喜着,却见王方的女儿王弗 遣身边侍女也送来了题名,“唤鱼池”三个大字跃然 纸上,隽秀而醒目。举座皆惊,大赞:“不谋而合, 韵成双璧。”此事过后,惜才的王方便将女儿王弗许 配给了苏轼。 王弗温婉娴静,婚后的家事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 条,此外,她还是苏轼*得力的助手。刚嫁给苏轼时 ,苏轼只知王弗是识字的,却未料到她也曾读过百卷 书。每每苏轼挑灯夜读时,王弗都会陪伴身侧,研墨 温茶。 若是苏轼有遗忘或不解处,王弗便会从旁点拨, 像是位有大智慧的扫地僧,只给些提醒,却从不拨云 见*,故虽不会被她醍醐灌顶,学识却可与*长进。 各色的书,王弗仿佛都有见识,若是苏轼夸奖,她反 倒谦逊了起来,说仅是一知半解,有愧谬赞。 “乃知天壤间,何处不清安”,与王弗的相处就 是这样,她给人惊喜与温存的方式都是平铺直叙的。 她以为好女子便是要做到平顺,于是她便用*温和的 火候调理家庭这道餐点。 原本王弗的骨子里也是热衷掌控的,她会躲在屏 风后面,听客人与苏轼的谈话,待拜访者离去后,她 则告知苏轼来者是为弹冠结绶还是人心叵测。她心思 深重,却也只为苏轼所劳。王弗是苏轼生活的老师, 也是他灵魂的伴侣,他们之间没有太多风花雪月、缠 绵悱恻,但谁敢否认平淡也是另一种伟大。 在与苏轼相知相守的第十一年,王弗辞世,留下 一子苏迈,刚满六岁。苏轼将王弗葬在了母亲的坟旁 ,并在安葬王弗的那座山坡上,亲手植了三万棵青松 。 王弗去世的第十年,苏轼再度梦见亡妻,于是他 写下了那首被传诵千年的悼词双璧之一《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 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 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 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你我黄土之隔已是十载光阴,我们互相想念却又 无从相见。我本忍着不去想你,可思念在晨曦或是月 夜里不请自来,我对你终究是难以忘怀。你永远寄身 在遥远乡里,而我却踟蹰客地,没了*懂我的你,我 的心事还有谁能开解。你去,或是我来,总之这世间 欠我们一场相见。可再看我这满头的霜雪,我这满面 的尘埃,只怕纵是相见,你也已识不得我如今模样, 而你却永远美丽地定格在我记忆里。 说来怕你笑我只知儿女情长,你不知你曾多少次 入我梦乡,我梦见你在小窗前对镜梳妆,那真切的画 面带我回到了十年前每一个有你的清晨。我们凝望着 彼此,纸短情长,你应懂我的泪千行。我为你种了三 万棵青松,让那明月照着你,让那松树伴着你,就像 有我在这里永远牵挂着你。 后来,苏轼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王闰之不似 王弗有幸,她是在苏轼*为困顿失意的时光出现的, 也是真正陪他颠沛流离的那一个,从“乌台诗案”到 黄州贬谪,十六年间,从杭州到密州,再到徐州、湖 州。王闰之曾跟着苏轼在连天大旱的蝗灾里灭蝗、沿 着城墙拾救弃婴、挽起裤管挖采野菜…… 但无论生活如何困苦,她仍是将嫁给苏轼视为自 己此生*大的幸运,那时的姑娘家不兴有什么名字, 就连苏轼的母亲也只被唤作程夫人,苏辙的妻子*是 被叫了一生的史氏。而王闰之不同,苏轼不但为其取 名“闰之”,*让她有了自己的字:季璋。此等权利 在旧时,唯有男人可享,可见苏轼是重视闰之也敬闰 之的。 王闰之陪伴了苏轼二十五年,为苏轼生苏迨、苏 过二子,并视王弗之子如己出,“妇职既修,母仪甚 敦”。王闰之是个不懂抱怨的人,赤脚耕田、栉风沐 雨皆不能去她欢颜。哪怕后来苏轼再度策名就列,飞 黄腾达,王闰之也依旧如闲云流水,声色不改。陪他 耕织的是她,每*迎门的是她,布衣韦带也不怨他, 行返丘园也不弃他。 后来,王闰之在汴京染病去世,苏轼亲写祭文: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 同穴,尚蹈此言。”为践“同穴”之诺,王闰之的灵 柩被停放在京西的寺院内,直到十年后,与苏轼同在 客乡合葬。 *后点缀苏轼生命的女子,名叫王朝云,是位西 湖名妓。彼时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某*,他与几位 文友共游西湖,并在宴饮时找来歌舞班助兴。台上的 舞女们个个美艳妖娆、浓妆艳抹,台下的看客们也都 把酒持螯、放浪形骸。 在众多舞女中,有一女子因舞姿高超显得尤为出 挑,苏轼的目光始终追随于她。直到丝竹声将歇,舞 女们被安排侍酒,苏轼仔细一看,身旁的女子竟正是 群芳中*为夺目的那个,只是她换了素服、卸了浓妆 ,唯有轻启的朱唇上还留着一抹亮红,这般的清丽可 人,实不该是**女子应有的面目。 苏轼与她交谈了几句,得知她叫王朝云,自幼家 境贫寒,身世可怜,不得已才沦落风尘,便对她*为 怜惜。那天,苏轼始终兴致颇高,于是他写下了“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写西湖,也是写身旁的女子。 解人难得,王朝云是懂苏东坡的人。在苏轼被贬 惠州时,王朝云也一路相随。苏轼*爱听她唱《蝶恋 花》,可朝云每到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都会 哽咽而止,而后泣如雨下似五内俱崩。东坡问起缘由 ,她只道不敢续唱,因为下一句是“天涯何处无芳* ”。 的确,他们两个都是漂泊的可怜人,身是柳絮, 却不知哪一处才是可容他们栖身的芳*,而故乡,只 能遥望。苏轼比她还要感伤,却仍旧笑着劝她:我正 在悲秋,而你又在伤春。世人都羡慕他是个诙谐的乐 天派,只有他自己清楚,所谓洒脱看透,不过是无奈 之下的自我救赎罢了。 某*吃食毕,苏轼抚着肚子,问身边婢女可知腹 中为何物,一人答都是文章,又一人答都是学识,苏 轼对她们的谄媚通通不以为意。问至朝云,她则道: “学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道:“知我者 ,唯有朝云也。” 朝云还为苏轼生下了一个儿子,苏轼为其取名“ 遁”,意喻遁世、归隐。老来得子的苏轼对小儿没有 任何大的祈盼,唯愿他一生平安:“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 卿。”只可惜在他羁旅途中,刚满半岁的幼子因中暑 不治,夭折在了朝云怀里。那可怜孩儿的眉眼,早已 有了几分苏轼的模样。可叹,苏轼连这*卑微的祈愿 ,也未能达成。 再到后来,朝云也因染病离他而去,他切齿,这 一生究竟要有多少次告别。苏轼在朝云墓上筑了六如 亭,并亲写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 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自朝云死后,苏轼终生 不再听昔**爱的那首《蝶恋花》唱词,并一直鳏居 至死。“天女维摩总解禅”,可惜这世间再没有了他 的天女维摩。 苏轼为朝云所写墓志铭只短短百字,写她是钱塘 人,写她故去的时辰,写她何*入门,写她身栖寺之 东南。而悼亡的话,苏轼却只字未提:“浮屠是瞻, 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对朝云,无有赘 言,他只剩性命相见。 “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此生的泪水都已 流干殆尽,再没什么眼泪能够为你。 得一贴己者,而后从她的视角重看自我、重看天 地万物。虽身世浮沉,但苏轼终是幸运的,因为一直 都有人爱着他。 雪堂的西侧有泉鸣,山坡上有长亭,小溪横在门 前,北山微倾,此间宛似昆仑仙境,*胜似斜川当* 境。他多像陶渊明,走遍了人间,却躬耕一田园。昨 *的东坡又下了一场春雨,乌鹊喜,报新晴;人老矣 ,寄余龄。 把人生都泡在杯酒里,斟酒时,须满十分;且陶 陶,乐尽天真……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