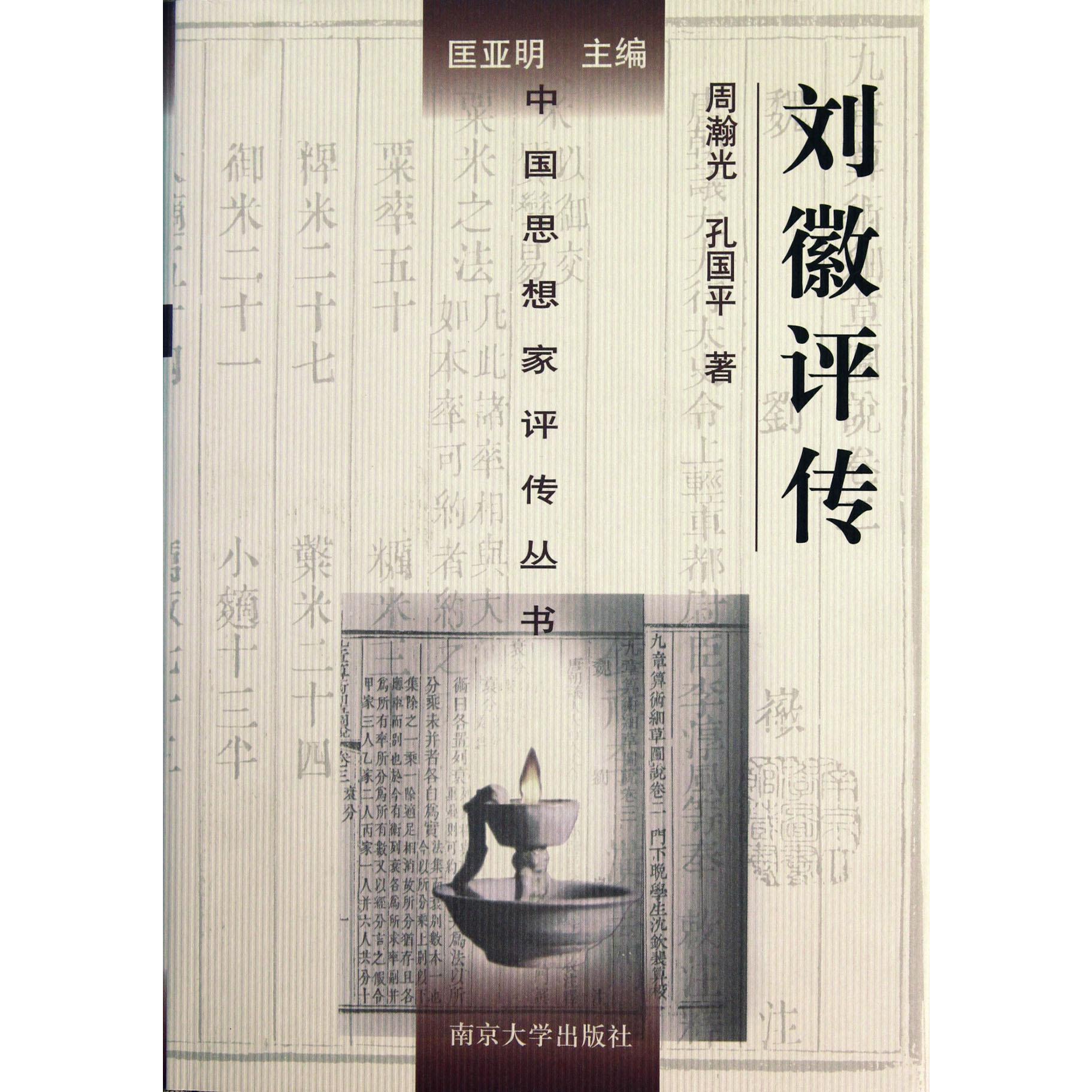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4.12
折扣购买: 刘徽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5022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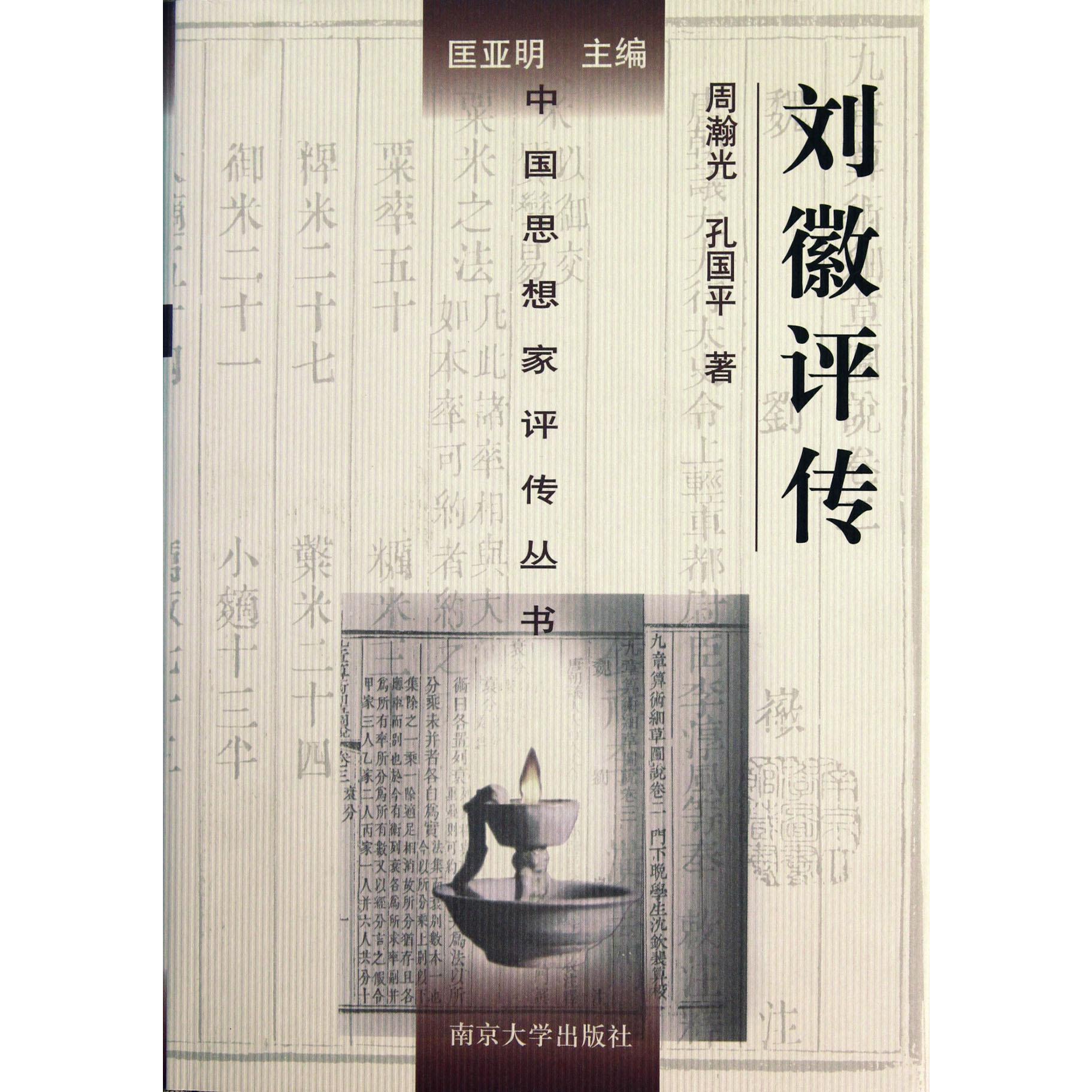
周瀚光,男,1950年7月生。1983年于复旦大学获哲学硕士学。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等书。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孔国平,1947年3月生于河北肃宁。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5年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获数学史硕士学位,1990年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数学史博士学位。1994—2002年任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现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片反社编审,负责科学史图书的编辑工作。 专著《李冶传》获全国优秀科技史图书二等奖,与杜石然共同主编的《世界数学史》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此外还发表专著《测圆海镜导读》、《李冶朱世杰与金元数学》,合著《刘徽评传》、《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参加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数学史大系》等12部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著作总字数约200万。
刘徽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社会从战乱走向统一,思想从解放走向争鸣 ,科学从恢复走向发展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一段五彩纷呈 的“非常之世”,而正是这种五彩纷呈的“非常之世”,造就了刘徽这样 一个精彩纷呈的“非常之士”。 3世纪的中国,神州大地经历了一场社会的磨难。尽管席卷全国的黄巾 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东汉末期的腐朽政权,给水深火热之中的贫 苦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起义之火很快就被各地豪强地主的联合镇压扑 灭了下去。各地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割据 称雄,独霸一方,动辄兴兵、互相吞并,使中国社会又陷入军阀混战、饿 莩遍野、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灾难之中。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在 连年的战争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如曹操、诸葛亮那样的优秀的政治家。首 先是曹操统一了北方,接着是孙权统一了南方和诸葛亮辅助刘备统一了西 蜀,形成了一个曹魏、孙吴和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在北方采取了一 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屯田制,适当抑制豪强兼 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等,使北方的农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复苏,从而 为最终吞并蜀汉和东吴打下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东吴和蜀汉为了自身 生存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生产,使江南和西蜀也 出现了一定程度生产复苏、经济发展的形势。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正是 著于此时。《晋书·律历志》和《隋书·律历志》说:“魏陈留王景元四 年,刘徽注《九章》。”魏陈留王景元四年为公元263年,次年魏亡,再次 年即是西晋泰始元年(265)。差不多与此同时,蜀汉和东吴先后相继为魏、 晋所灭,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度短暂的统一。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可谓掀起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 一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高潮。汉代数百年独尊儒术,固有其适应当时 社会需要的一面,但却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后果:其一是谶纬迷信盛行 ,儒学成了神学;其二是形成一种经学独断论和烦琐学风,甚而“说五字 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解释经文五个字,竟然要用 两三万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是如此。先秦时期除儒家以外的其他诸 子学说在汉代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有的学说如极富科学精神和逻辑 理论的墨家思想竟成绝学。这样一种沉闷、独断、神秘、烦琐的学术风气 所幸在汉末的黄巾大起义中遭到了彻底的扫荡。魏帝曹丕在后来修复孔庙 的诏书中说:“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 ,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魏志·文 帝纪》)可见汉代的儒家经学到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 数百年经学独断论的冲垮,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无疑是一次大的解放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学说应运而生,学术争鸣此起彼伏。在魏晋时期,首 先兴起并盛行的是玄学。玄学派高举《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 面旗帜,号称“三玄”,援道人儒、以儒解道,表面上重道轻儒,实际上 儒道合流,建立了一个上至“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下至“言不尽意” 的逻辑名理,远而崇尚清谈玄议,近而揉合名教自然的新的理论体系。玄 学开创者何晏(约195—240)和王弼(226—249)都以“贵无”为其理论核心 ,主张“无”(亦即“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万物都由“无”所派生, “凡有皆始于无”,“万物皆由道而生”(王弼《老子注》)。在他们看来 ,客观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来源于“无”、决定于“无”、统一于“无” ,这就从本体论的高度打倒了两汉儒家的天命神学。王弼又主张“言不尽 意”、“得意忘言”,认为语言和概念不能完全表达“无”和“道”的微 妙真意,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意”而不在纠缠于“言”。他专讲“三玄 ”的微言大义,尽扫汉儒的牵强解释和烦琐学风,使当时的学术界耳目一 新。与此同时,另一位玄学代表,“竹林”名士嵇康(224—263)则自称“ 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释私论》)的口号,主张摆脱儒家纲常礼教的束缚。当然,嵇康所鼓吹的 “越名教”其实并不一定便是出于本心。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嵇康等人之 所以反对礼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打着“以孝治天下”等礼教的幌子进 行篡弑掠夺,迫害政敌,嵇康等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 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 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稍后一点的玄学家郭象(?—312)又提出“独化”的 思想,认为万物都是“自己而然”地生生不息、运动变化,“天地万物无 时而不移也”(《庄子注·大宗师》)。在这样一个永恒的变化之流中,什 么都留不住,一切现象即生即灭。王朝的交替也罢,理论的更迭也罢,“ 皆在冥中去矣”。 魏晋玄学以其崭新的姿态取代了已趋没落的两汉经学,这无疑是思想 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玄学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论弱点。玄学家把 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统统归结于“无”、统一于“无”,实际 上否定了客观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是一种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言不尽 意”论把“意”看作是可以脱离“言”、“象”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认为 人的认识不能把握道的本质,又导向了一种放弃认识的蒙昧主义。特别是 玄学家倡导了一种远离现实、虚无飘渺的清议空谈风气,从而使当时的一 批知识分子“口之所谈,身不能行;长于识古,短于理今”;“入不能宰 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操柯犹豫,废法效非, 枉直混错,终于负败”(《抱朴子·行品》)。因此,从玄学产生的一开始 起,反对玄学的思潮也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三国时吴人杨泉著《物理论》 ,继承了先秦《管子》“水气”本原论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由水而生、 由气而成,用物质性的水和气来反对玄学家超物质的“无”和“道”。晋 初裴頠(267—300)著《崇有论》,明确认为“以无为宗”是“偏而害当” 。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 用客观实在的“有”去批判和取代玄虚飘渺的“无”。同时的欧阳建(约 267—300)则著《言尽意论》,从言意统一的角度驳斥了“言不尽意”的不 可知论。这种对于玄学的批判和争鸣,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充满了勃勃生 气。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