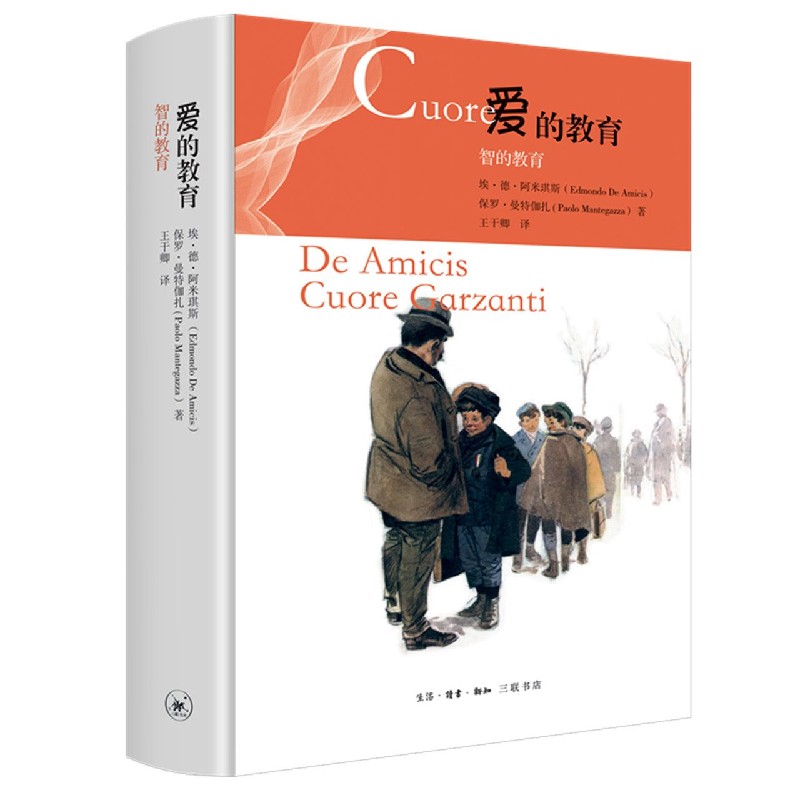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9.60
折扣购买: 爱的教育 智的教育
ISBN: 9787108070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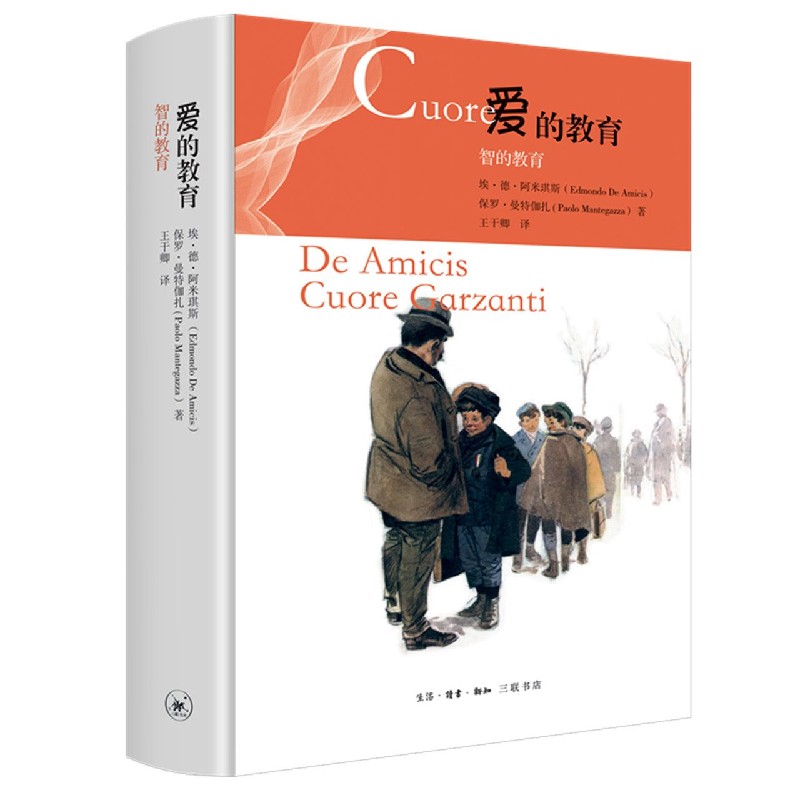
埃·德·阿米琪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意大利19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他自幼酷爱学习,喜欢军旅生活,青年时代就成了一名步兵军官,著有《军事生活》一书。他曾游历过许多国家,发表过一系列游记。但阿米琪斯还是以描写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见长,《朋友们》《大家的马车》等作品在意大利脍炙人口,《爱的教育》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读《爱的教育》,有些国家还把《爱的教育》作为小学生的教科书来学习。 保罗·曼特伽扎(Paolo Mantegazza ,1831—1910),意大利著名的人种学家、病理学家兼医生,曾在几所大学的医学系任教多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意大利成立了第一个国家级人种学博物馆,完成了多项与此有关的科学考察及研究项目。因其在这个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于186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除了《智的教育》外,保罗·曼特伽扎的其他作品还有著名的三部曲《爱的生理学》《欢悦生理学》和《女子生理学》,以及《马德拉一日》《无名的上帝》等。
寻母记—从亚平宁山脉到安第斯山脉(每月故事) 很多年以前,一个热那亚的十三岁少年——一位工人的儿子—独自一人离开热那亚到美洲去找他的母亲。 少年的家庭屡遭不幸,穷困潦倒,债台高筑。母亲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让家中摆脱困境,两年前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富人家当用人。那时用人在美洲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于是,不少勇敢的意大利女子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到那里去找工作。短短几年,她们就能挣上几千个里拉回国。可怜的母亲哭干了眼泪,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一岁。可她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满怀着希望出发了,整个旅途一帆风顺。 她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便通过丈夫一位在那里定居多年、当店主的热那亚堂兄的介绍,在一户殷实人家找到了工作。这家人给她报酬很多,待她也很好。她跟家里人保持着正常的通信联系。他们之间配合默契:丈夫先把信寄给堂兄,然后堂兄再转给她。她给家人的信交给堂兄,堂兄再写上自己的片言只语,寄到热那亚。她每月挣八十个里拉,因为她没有什么花费,每三个月就能给家里寄一笔可观的钱。丈夫是个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他用这笔钱逐步还清了债务,重新赢得了好名声。他在家乡辛勤做工,对自己的为人处世十分满意。可家里没有妻子,总是显得冷冷清清,尤其是小儿子一直想念妈妈,无法忍受远离妈妈的痛苦,因此常常忧愁悲伤。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是多么盼望妻子早日回国啊! 一年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她在一封短信中说自己身体不怎么好。可打这以后,再没有她的音信了。家人曾两次给堂兄写信,但没有回信;给雇用她的那户阿根廷人家写信,因为地址写得不全,可能没有收到,也没回信。丈夫和儿子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幸,便给意大利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馆写信,请他们帮助寻找。过了三个月,领事馆回信说,尽管他们在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既没人来领事馆接洽晤面,也没人提供这方面的任何消息。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们猜测,也许她觉得当用人有损于家庭名声,为了保全亲人的面子,这位善良的女人向那户阿根廷家庭隐瞒了真实姓名。 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杳无音信。丈夫和儿子坐卧不安。小儿子更是伤心难过得不能自拔,怎么办呢?向谁求助呢?丈夫的第一个想法是自己亲自去找妻子,但工作怎么办呢?他去了谁养活孩子呢?大儿子刚能挣上几个钱,家里很需要他,显然他不能去。他们父子三人就是这样每天重复着痛苦的永恒话题,焦虑不安,面面相觑,在万分痛苦中打发日子的。一天晚上,小儿子马尔科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到美洲去找妈妈!” 父亲没吱声,只是忧虑地摇摇头。孩子的想法是好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到美洲去,要走一个月的路程,实在不容易。但孩子坚持要去。他今天要求,明天要求,天天如此,顽强执着,像个通情达理的大人,道理讲得也很明白。他说: “很多人都去了,他们比我还小呢。不就是坐船去吗?只要坐上船就没事了。别人能去,我也能去。到了那里,我就去找堂伯的店铺。那里有很多意大利人,有人会给我指路的,找到堂伯,就等于找到了妈妈。假如找不到堂伯,我就去领事馆,请他们帮忙找那户阿根廷人家。不管发生什么事,那里总能找到工作的,我也可以找一份工作干,起码可挣足路费回家。” 就这样,他渐渐说服了父亲。父亲很器重他,觉得他有主见,有勇气,能吃苦,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优秀品德加上寻找他所敬重的母亲这样一个神圣的目的,他肯定能迸发出双倍的勇气来。另外,船长是父亲一个熟人的朋友。船长听说后,答应给他一张免费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 父亲犹豫片刻,还是同意了,定下了旅程的日子。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包衣服,给他几枚银币,把堂伯的地址交给他。在四月一个迷人的夜晚,将他送上了船。 站在将要启程的轮船扶梯上,父亲热泪盈眶,亲了小儿子最后一次,依依不舍地说: “马尔科,我的孩子,鼓起勇气来,为了神圣的目的,你放心地走吧,上帝会保佑你的。” 可怜的马尔科啊。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准备经受旅途中最严峻的考验。但一看到美丽的热那亚从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四周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海水,巨大的船上全是背井离乡的农民,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背着一个跟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小包袱,沮丧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两天来,他像一条狗一样蜷伏在船头,几乎什么也没吃,恨不得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各种悲观的古怪念头一一掠过他的脑海。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最痛心、最可怕的念头就是母亲死了。在昏昏欲睡中,他总是朦朦胧胧看见一个陌生人,用怜悯的目光细细地打量着他,附在他耳边低声说: “你母亲死了!” 他苏醒过来后,心里憋得透不过气来。 轮船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他第一眼看见大西洋时,又重获了一些勇气和希望,但这只不过是短暂的慰藉。四周总是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海,天气越来越热,可怜的马尔科忧心忡忡,孤苦伶仃……这一切都增添了他的哀愁。死气沉沉和一成不变的生活使他心烦意乱,像病人一样神志不清。 他觉得自己在海上已走了一年的光景。每天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总是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漂泊,一次又一次地流露出惊讶的神情。美丽的飞鱼常常嗖嗖地落在船上,热带地区奇妙的晚霞和厚厚的云层映照成血红色,夜晚的海面粼光闪闪,整个大海仿佛燃烧着的熔岩。在他看来,这一切好像都不是真实的,而是梦幻中朦朦胧胧看到的奇观。 在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索性一直把自己关在舱里打发时间。船上一片狼藉,抱怨和怒骂声不绝于耳。他觉得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有时候,大海风平浪静,暗黄色的海水一望无际,天气酷热得叫人无法忍受。烦恼永无止境,险恶的日子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精疲力竭的旅客四脚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甲板上,所有的人都像死了一样。 旅行没有尽头。大海,天空,天空,大海,昨天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天天如此,永恒不变。 他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靠在船舷上,痴呆发愣地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恍恍惚惚地想着母亲。想来想去,直到闭上眼睛,进入梦乡。他再次看到那陌生人的面孔,用怜悯的神情打量着他,贴着他的耳朵说: “你母亲死了!” 听到这声音,他猛地惊醒过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一成不变的地平线,重温梦幻中的情景。 旅程持续了二十七天。最后几天是最好的日子,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马尔科在船上结识了一位善良的伦巴第老人。他儿子是阿根廷罗萨里奥附近的农民。老人要到那里去探望儿子,马尔科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人。老人拍着他的后脑勺说: “孩子,勇敢起来,你母亲肯定平安无事。她见到你会满心欢喜的。” 老人的陪伴安慰了他。他的不祥预感由悲观变成了快乐。他坐在船头,依偎在吧嗒吧嗒抽着烟斗的老人身旁。在迷人的星空下,颠沛流离的农民引吭高歌。他翻来覆去地想象着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景:他来到那条大街上,找到堂伯的店铺,一阵风似的飞跑过去,迫不及待地连声问道: “我母亲的身体怎样了?她在哪里?我们马上去找她!马上去!”于是他和堂伯飞快奔跑,爬上楼梯,门开了……他的自言自语到此为止,他的想象也到此为止。他沉浸在无法形容的脉脉温情中不能自拔,便偷偷地摘下戴在脖子上的小小圣像亲吻,并轻声细气祷告一番。 在启程后的第二十七天,他们终于到达了阿根廷共和国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边无际的拉普拉塔河蜿蜒曲折地流过城市,轮船就在岸边抛锚。 这是五月中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中浸染了胭脂色的彩霞,朝阳绚烂。在马尔科看来,这朝霞似锦的好天气是个好兆头。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欣喜若狂了。他母亲离他仅有几英里远。再有几个钟头,他就能见到母亲了。他已来到美洲,来到一个新的世界,是冒着风险、独自一人来的。现在想起来,漫长的旅程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好像是做着美梦飞到这里,现在才醒过来似的。为了不让别人将钱全部偷走,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分成两份装好,结果还是被人偷走了一份。他既不吃惊,又不难过,而是感到十分幸福。现在他只剩下几个里拉了,但这无关紧要,反正他马上就能见到母亲了。 马尔科手提包袱,随同许多意大利人一起走上小汽船。小汽船把他们送到离岸很近的地方。下了小汽船,又上了一只名叫“安德烈·多利亚”号的小船,在防波堤上了岸。然后,他告别了伦巴第老朋友,大踏步地向城里走去。 马尔科来到第一条马路的街口,叫住一个过路人,向他打听“艺术大街”怎么走。他打听的这个人正好是一位意大利工人。他好奇地望着马尔科,问他识字不识字,马尔科点点头,那人指着马尔科刚刚走过的街道说: “识字就好。你一直往前走,每个拐弯的地方都写着街道的名字,你看看名字,就能找到你要找的街道。” 马尔科向那人道谢后,就一直往前走。这是一条笔直而看不到尽头的狭窄街道,两旁是白色的像小别墅一样的低矮房子,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喧嚣嘈杂的声浪震耳欲聋,五彩缤纷的大幅旗帜迎风招展,上面用粗大的字体赫然写着轮船前往各个城市的时间。每走一段路他都左顾右盼一番。走着走着,来到另外两条依然望不到尽头的笔直大街,两旁依然是白色低矮的房子,依然车水马龙,人潮涌动。说到底,这里就是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的美洲大平原。城市仿佛宽大无边,不管你走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到处都是一样的房子,仿佛整个美洲都是这样似的。 马尔科注意着每条街名,费劲儿地读着那些古怪的名字。每走到一条新街道,他的心就怦怦跳个不停,嘀咕着这就是他要找的街道。因为他有遇上母亲的想法,便注视着每一个女人。有一次,他看见走在他前面的女人很像母亲,他的血液直往上涌,等追上去一看,原来是黑人。他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念起来。原来这就是“艺术大街”。他回头一看,门牌是一一七号,而他堂伯的家是一七五号。他再次加快脚步,跑步来到一七一号门前,这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心里连连念叨着: “妈妈啊!妈妈啊!再过一会儿,我就会真的见到你了!” 他继续向前跑,来到一家服饰用品铺子跟前站住了,就是这个店铺。他抬头一看,见到一位头发灰白、戴眼镜的女人。 “孩子,你要干吗?”女人用西班牙语问。 “这是弗兰西斯科·梅列里的铺子吗?”马尔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发出声音这样问。 “弗兰西斯科·梅列里死了。”女人用意大利语回答。 马尔科的胸部仿佛挨了一记重拳般难受。 “他什么时候死的?” “唉,早死啦。死了几个月了。他做生意赔了本,便从这里出走了。听说,他去了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巴哈布兰卡,刚到那里就死了。这个铺子现在是我的。” 马尔科的脸唰的一下变得煞白,急巴巴地说: “梅列里认识我母亲。她在梅奎纳兹先生家当用人。只有梅列里能告诉我母亲到底在哪儿。我就是为了寻找母亲才来美洲的。我们的信就是梅列里转交给她的,我必须找到母亲。” 女人回答说: “可怜的孩子,我可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问问后院儿的那个男孩子。他认识给梅列里买卖东西的年轻人,他也许知道点儿什么。” 女人来到铺子的后面叫那男孩子马上进来。孩子听到有人叫他就跑了过来。 女人问他:“喂,请你告诉我,你还记得那个给‘故乡之子’家里的女用人送信,替梅列里家里做事的年轻人吗?” 孩子回答说:“太太,我知道这件事。她有时在梅奎纳兹先生家当用人,就住在‘艺术大街’的尽头。” 马尔科高兴得大声说:“好哇,多谢太太!请您把门牌号告诉我。您知道吗?要是不知道,请让他领我去。” 马尔科又转向男孩恳求说:“小哥们儿,马上陪我去一次,我还有些钱。” 小男孩禁不住马尔科一再央求,没等女人吩咐就痛快地回答说:“好,我们走吧。”说完,就第一个快步走了出去。 路上他俩一句话也顾不上说,走走跑跑,一直来到这条很长很长的大街的尽头。穿过一座小白房的狭长过道,他们在一道很漂亮的铁栅栏前停下来。这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面摆满了盆花。 马尔科摁了一下门铃,一位小姐从里面走出来。 “这里是梅奎纳兹的家吗?”马尔科焦急不安地问。 “以前住过,现在是我们泽巴罗斯家住在这里。”小姐用西班牙腔调的意大利语回答说。 “那么,梅奎纳兹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马尔科问,心怦怦直跳。 “搬到科尔多瓦去了。” 马尔科惊叫起来: “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在什么地方?他们家的女用人在哪里?她是我母亲呀!女用人就是我母亲呀!他们也把我母亲带走了吗?” 小姐打量着马尔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父亲知道。他们离开时,我父亲见过他们,请你们等一等。” 小姐跑进屋里,不久她跟父亲——一位高个子、花白头发的绅士一块儿走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端详了一会儿眼前这位金黄头发、鹰钩鼻子的少年—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酷似热那亚小海员的形象,然后用十分蹩脚的意大利语问: “你母亲是热那亚人吗?” 马尔科点点头。 “对啦,热那亚女用人跟他们一同走了,我敢肯定。”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科尔多瓦城去了。” 马尔科喘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那我到科尔多瓦去找她。” 绅士带着怜悯的神情感叹地说: “啊,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科尔多瓦离这里有几百英里呢。” 马尔科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他的一只手扶在铁栅栏门上。 绅士的怜悯心被打动,于是开了门说: “让我们想想看,让我们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你进来坐一会儿吧。” 绅士先坐下,也请马尔科坐下,让他原原本本地讲讲自己的情况。绅士屏息凝神地倾听,又想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其事地问: “你没有钱了,对吗?” “我还有……还有一点儿。”马尔科回答说。 绅士沉思几分钟,然后坐到桌子跟前写了一封信,封好后交给马尔科说: “意大利小鬼,你听着,你带着这封信波卡市,那是一座有一半热那亚人居住的小城镇,离这里有两个钟头的路程,谁都会给你指路的。你到了那里,就去找信上写的这个人,那里的人都认识他,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就行了。明天他会安排你到罗萨里奥去。他会把你介绍给那里的某个人。这个人会安排你去科尔多瓦的旅程。到了那里,你将找到那户梅奎纳兹人家和你的母亲。喏,这里有几个里拉,请拿去用吧。”绅士把几个里拉放到马尔科手上,继续说: “孩子,你去吧,拿出勇气来。那里到处都有你的同乡,他们不会对你撒手不管的。孩子,再见!” 马尔科实在找不出其他什么答谢之辞,只道了声“谢谢”,就拎着包袱出来了。他告别了给他带路的小男孩,穿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喧闹的大街,带着悲伤和惊奇向波卡慢慢走去。 从启程那一刻直到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让马尔科的记忆模糊不清,思维紊乱,活像一个热病患者沉浸于梦幻之中。他感到疲惫不堪,灰心丧气,惶惶不安。当天夜里他是在波卡一户人家一间肮脏不堪的小屋里同一位码头搬运工睡在一起的。白天一整天他都是坐在一堆梁木上,迷梦般地望着来来往往数千只客船、货船和小汽艇来打发时光的。一直等到第二天黄昏,他才搭上一只满载水果、开往罗萨里奥的大帆船。他坐在了船尾。这只船由皮肤晒得黝黑的三个身强力壮的热那亚人驾驶。听着他们讲话的声音和可爱的方言,马尔科的心里稍微感到一点宽慰。他们出发了,这次航行持续了三天四夜,对于这个小小的旅行者马尔科来说,这是一次惊奇不断的旅程。他们三天四夜都是在这条不可思议的巴拉那河上航行的。我们的波河跟巴拉那河相比,简直是一条小溪了。整个意大利全长的四倍也没有这条河长。 船在雪团一般的浪花中缓慢地溯流而上,穿行在许多长长的岛屿之中,这些岛屿早已成为蟒蛇和老虎的藏身之地,覆盖着橘子树和柳树,看起来活像浮动的林海。船时而行驶在狭长的运河上,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时而驶进浩渺无际、风平浪静的湖面,然后经过一个群岛纵横交错的水渠,行驶在一片葱绿的植物中。四周寂静无声。在漫长的航行中,蜿蜒连绵的河岸,宽阔寂寥的水域,给人留下一种这是一条陌生河流的印象,可怜的小船在这从未有人涉足的、神秘莫测的地方进行了首次探险! 越往前行驶,这条可怕的河流就越让马尔科感到惊慌不安。他想象着母亲可能是住在离河流的源头不远的地方,这要走好多好多年才能到达。他与船工们每天两餐只吃一点儿面包和咸肉。船工见他满面愁容,从不主动跟他说话。他夜间睡在甲板上,时常突如其来地被晶亮晶亮的月光照醒,显露出惊恐的神情。月亮的银辉洒满一望无际的水面和远处的河岸,照耀得像白昼一样明亮。马尔科心里非常痛苦,默默地重复念叨着: “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在他看来,这是一座神秘的城市,是听别人讲童话时提到的城市。可是他又想: “妈妈也曾经过这里,也看到过这些岛屿和河岸!”于是他马上觉得母亲经过的地方不再显得古怪和荒凉了。 夜里,一个船工唱起歌来。这歌声使他想起妈妈哄他睡觉时唱的催眠曲。最后一夜,他听着船工的歌声,竟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船工停止唱歌,大声对他说: “小家伙,鼓起勇气来。你中了什么邪?一个热那亚人难道因为远离家乡就哭鼻子吗?热那亚人往往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扬扬地走遍天涯海角的!” 听了船工的话,马尔科重新打起精神来,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热那亚人的血液而自豪。想到这里,他昂首挺胸,用拳头捶打着船舵。 “是的,就是走遍全世界,不论走上多少年,步行多长的路,我也要勇往直前,直到找着母亲。”马尔科暗暗下定决心,“即使倒下,哪怕死在她的脚下,但愿我能见她一面,鼓起勇气来!”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满天红霞的寒冷的清晨,乘船到达坐落在巴拉那河上游的罗萨里奥的。来自各个地区的百艘轮船在这里抛锚,桅杆和彩旗倒映水中。 上了岸,马尔科拎着包袱,按照波卡的那位保护人给他的名片地址,进城去找当地一位阿根廷绅士。进入罗萨里奥市区,马尔科觉得好像来到一座早已熟悉的城市。这里到处都是望不到尽头,向各个方向辐射的笔直马路,两边也都是低矮的白色房子,屋顶上架着一束束密如蛛网般的电报线和电话线,马路上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掀起一股股嘈杂的声浪。他大脑发昏,觉得又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再一次来找堂伯了。他在街上东找西找,左拐弯,右拐弯,大约转悠了个把小时,觉得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同一条街道上。经再三打听,他终于找到了新保护人的住处。他摁了门铃,一个面有愠色、模样像个农场总管的粗壮高大的金发汉子向门外探出头来,操着外国腔,毫不客气地问: “你找谁?” 马尔科说出主人的名字。 那人回答说: “昨天晚上,主人带着全家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马尔科顿时目瞪口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 “但是,我……我这里没有熟人,我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啊。”说着,他把名片递给那汉子。 那大汉接过名片,扫了一眼,态度粗暴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月后主人回来,我再交给他吧。” 马尔科禁不住叫起来: “但是,我……我只一个人,我多么需要帮忙啊。” “哎哟,算了吧,你们国家讨人嫌的人在罗萨里奥还少吗?快滚开吧,到你们意大利去讨饭吧。”那个人说完,当着马尔科的面,砰的一声把铁栅门关上了。 马尔科像一尊石像,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发呆。 随后马尔科又拎着包袱慢慢地走开了。他的心像刀割似的难受,脑袋昏昏沉沉,一下子陷入思绪万千之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