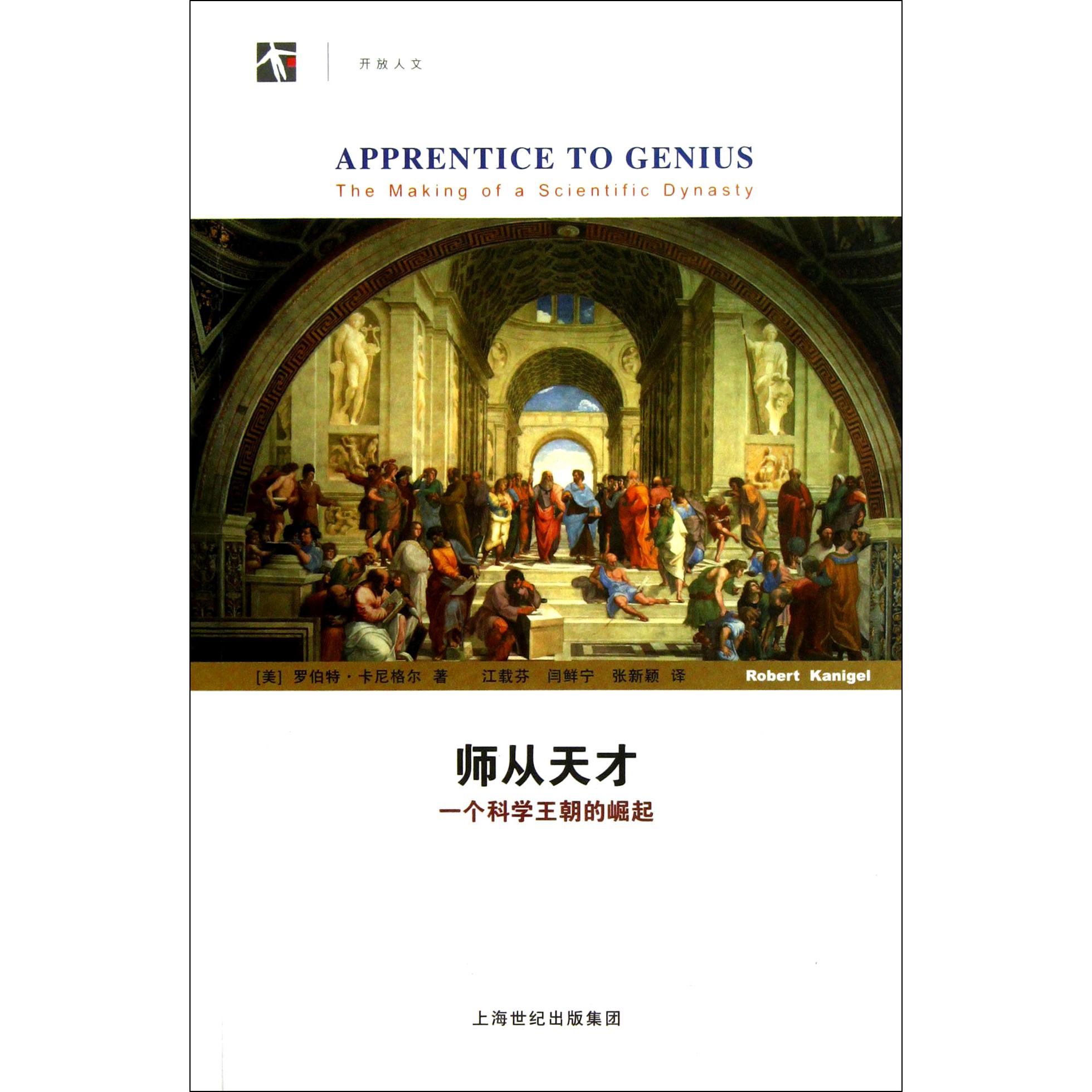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科教
原售价: 42.50
折扣价: 28.10
折扣购买: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
ISBN: 9787542854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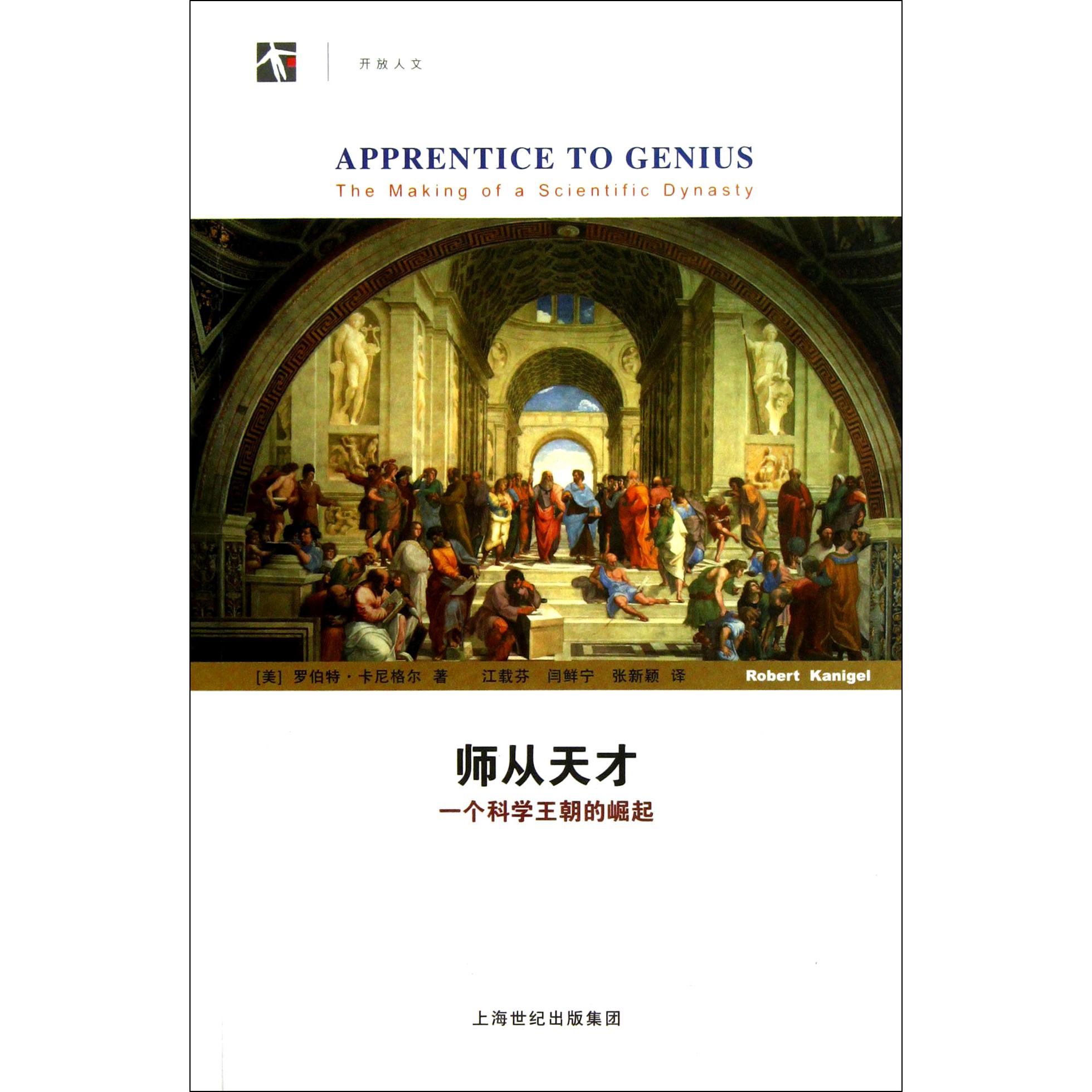
罗伯特·卡尼格尔,科学作家,曾获格雷迪—斯塔克科学写作奖,是《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等书的作者。作品散见于多种刊物,其中有《纽约时报杂志》、《文明》、《**心理学》、《健康》、《科学》等等。他定期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和《洛杉矶时报》写书评。卡尼格尔还是巴尔的摩大学耶鲁·高登文学艺术学院语言、技术和出版设计研究所的**研究员,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新闻文学。
汤姆·肯尼迪向香农作了抱怨。香农二话不说,马上打电话给一 个陆****官,并驱车直奔格林黑文医院。 汤姆·肯尼迪回忆这段故事时眼睛一亮,“他大步流星走进那家 伙的办公室,把脚翘在他的办公桌上,说: ‘我刚给沃尔顿(Walton) 将*通过电话,他说……’他给对方造成的印象是,如果他不按规矩 办,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很不错,后来一切都顺利多了。” 令人惊叹的是,时局发展如此顺利——或至少如此之快。到1943 年春天,当麦克阿瑟(MacArthur)上将准备让南太平洋的部队采取 “蛙跳”战术*击*本人时,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已解开阿的平的秘 密,使它成了一种强效抗疟药。 回想一下,蚊子并不直接引起疟疾,而是将寄生物传染给寄主。 这些寄生物——几种疟原虫——在寄主的红细胞中繁殖,有时达到每 立方毫米50万个。当红细胞破裂时,碎片和疟原虫将充斥于血液系 统,这时机体做出的反应是发高烧。如染上一种特定的恶性疟原虫引 起的疟疾,血中的寄生物竟会堵塞大脑血管,从而引起死亡。 为起到治病效果,抗疟药必须打乱寄生物的生命周期。为此,它 必须接近寄生物,也就是要进入血液。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面临的关 键问题是,找到一个办法测定血中的药物含量。 测定纯阿的平没有什么困难:在适当波长的光线照射下,阿的 平和其他许多有机的、含碳的化合物一样,会发出荧光;就是说*到 入射光的激发时,它本身也会发光。它发出的光在电磁波谱上属于紫 外线,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可用实验室的标准设备——荧光计来测量 它。而且荧光的强度与化合物的浓度是成比例的,这一点很重要。因 此可先用一点儿淡水使荧光计归零,然后用已知的样本进行校准,即 可直接测定药物浓度。 但如果手头没有纯阿的平的样本怎么办?当然,可以用基本上标 准的化学方法从血浆中分离出阿的平。另一个显然不太常见的办法 是,把它与它的代谢物区别开。从典型意义上讲,人服下的药物不会 保持其原来形式。它一部分或全部会被代谢,或从化学意义上讲被人 体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但怎么知道你是在测量阿的平,、而不是在测量 它的化学上类似的表兄呢? 布罗迪注意到,阿的平一类化学上里碱性的药物的代谢物常比原 药物*具极性。这是关键性的发现(极性分子在电荷上是不均衡的, 它的两端必有一端伸出一个“量”*多一些的电荷)。他想到,能否 利用这一差异呢? 极性物质会在其他极性物质中充分溶解。通过溶液中物质的密切 接触,似乎解除了双方的电荷不均衡状态。例如,水是高度极性物 质,极性分子会很容易溶于水中。另一方面,极性不高的分子不溶于 水,但能很好地与非极性液体,如有机溶剂二氯乙烯及苯溶合。 布罗迪推测,由于阿的平的极性低于其代谢物,有可能因其不易 溶于水,而将两者分开。也许阿的平可以被低极性液体析出,而其代 谢物则留在水溶液中。 当时下了不少功夫去优化基本的技术,如选择适当溶剂、为提取 过程的各化学步骤确定理想温度及酸度,以及解决出现的麻烦等。布 罗迪和乌登弗兰德采用这一基本战略成功地完成了研究。在可以纯净 地分离出这种药物后,通过荧光计来测量它,确定它的浓度就比较容 易了。 《生物流体和组织中阿的平的测定》这篇论文发表于1943年的 《生物化学学报》上,但他们两人在1942年冬天就完成了相关方法 的研究。如布罗迪几年后所说,可以合理地说,他们研究的阿的平测 定方法“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意味着香农的科研班子不必再在 黑暗中摸索。他们现在可以轻松地跟踪测定病人服下的阿的平的浓 度。而且新技术不仅适用于血浆,亦适用于尿、粪及任何机体组织。 新技术既适用于人,亦适用于实验动物。 事实上,在用狗做实验时,产生了可能是*惊人和*有意义的发 现。先给狗静脉注射10毫克阿的平。4小时后解剖,检测血浆及不同 机体组织中的药物浓度。结果发现肌肉纤维中的药物浓度比血浆高 200倍,而肝中的浓度比血浆高2 000倍。 机体组织似乎吸收了阿的平。血液中如有足够的阿的平,才会有 较好的疗效,但血中却没有留下多少阿的平。如按当时规定剂量给人 注射阿的平,则它将主要集中于肌肉和肝等组织中。血液中的含量只 会慢慢上升到每升30微克的水平,这时才足以杀死疟原虫寄生物。 怪不得按当时的规定剂量给药,很久才会见效。 答案是明显的。正常剂量增加一或二倍,会很快杀死寄生物,但 对士兵的副作用将加剧到不可忍*的地步。然而可以在疗程的** 天,开出大剂量的“着陆剂量”,以后每*给服较小剂量,以保持血 中已达到的药物浓度。这样可使人体组织中的药物含量立刻达到饱 和,后来摄入的药物会直接进入血液。 他们就这么干了,一切都成功了。到1943年春天,已解决了这 个难题,制定了新的剂量表。如布罗迪后来写到,到1944年1月, “疟疾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战术或战略问题。” 布罗迪一次曾写信给香农,“与您在戈尔德沃特纪念医院共同参 与疟疾项目,是我职业生涯中*令人激动的阶段之一。那是我职业生 涯的真正开始。” 那也是其他一些东西的开始。布罗迪和他在戈尔德沃特医院的同 事已对D楼地下室空气中的一种东西着了迷——一种狂热,一种紧急 和激动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令人振奋 的科学根本算不上科学。他们将把在戈尔德沃特医院达到的科研高水 准传给以后的同事和部下。香农在戈尔德沃特医院培育了沃土,种子 已经发芽,并将抽枝长叶,茁壮生长,而且还会伸出卷须,几年后就 会到处扎根,伸展到几英里之外。 战争开始时,布罗迪尚名气不大,战争结束时,他已是一位科学 明星。戈尔德沃特医院的战时紧急研究使他精神抖擞。他信心十足, 脑子里有无数的思路,他已准备向世界推出主要由自己创立的新药 理学。 P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