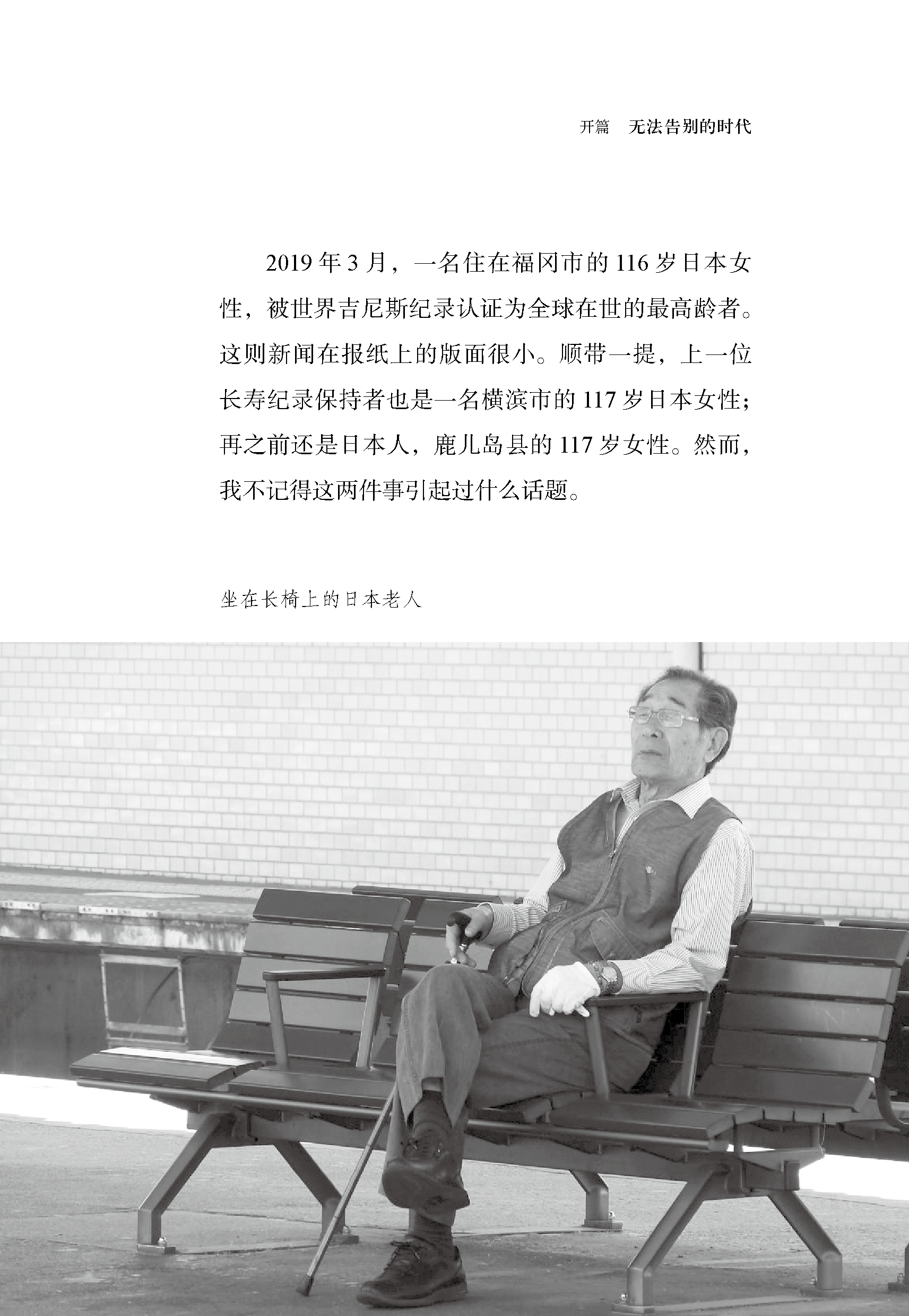出版社: 科普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9.50
折扣购买: 无法告别:日本的安乐死与临终哲学
ISBN: 9787110104965

村上阳一郎,日本著名科学史泰斗、科学哲学家,193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教养学院学士,东京大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曾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院教授、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长、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校长等。获颁东京大学、广岛市立大学荣誉博士。著有《生与死的关照现代医疗启示录》《科学史·哲学史入门》等。
【六眼之下】 这是我在本书第一次提到类似结论的意见:我个人基本上认为不应当经常否定医助自杀和安乐死。这是因为大家现实中都见过许多“活下去不见得是好事”的例子。 世界上有许多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例子。例如,船只“洞爷丸”沉没时,有位牧师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其他年轻人,最后成为波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里,有许多人站出来代替他人牺牲。我认为这些行为不该遭到批判。回到根本问题,这些例子都违反了日本社会目前的表面共识,但一口咬定“生命的价值胜于一切”肯定是错误的。认为自己相信的事物价值超越生命,为了崇高信仰而牺牲生命,这些都不该被否定。 专家与公众对安乐死和医助自杀如何应用于现实社会,有过许多讨论。我认为,必须设置门槛,以免适用范围被轻易扩大,形成“滑坡现象”。日本新闻屡屡报道某家属因为长期照护绝症患者造成身心沉重负担,结果发生了子杀父母、妻杀夫、夫杀妻等悲惨事件。这些例子虽然和末期患者主动想死的情况完全不同,但立法通过安乐死,或许会为这些人带来一些影响。我认为,这些可能性也必须纳入考量范围。 我的基本立场是:倘若当事人同意且当事人、亲近的家属和医疗团队建立起足够的信赖关系,不应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的安乐死或医助自杀。家父主修病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小的诊所。他曾经通过“六只眼睛之下”的说法,与我分享他实际执行过相当于安乐死的行为。所谓“六只眼睛”,指的是当事人、医生和另一名家属或负责照护的人,彼此建立起信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安乐死。“对医疗一线人员而言,对患者采取致死的措施以缩短痛苦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家父对我说这番话,是因为我将来可能继承家业,想当医生就得做好心理准备!当时我还是高二学生,认为父亲是在暗地问我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然而,老实说,我实在没有勇气亲手夺走他人的性命。 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是死在医院的,医生、患者和家属之间的人际关系相当紧密。我之前很少公开这个观点,不过我在和精神科医生 Naday Nada(本名堀内秀,1929—2013 年)的 往来书信中(收录于《生与死的凝视》一书)提到:“要是建立起紧密的人际关系,我认为医生是可以帮助需要安乐死的患者稍微缩短寿命的。”对方在回信中也表示:“正如您所言,安乐死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因为以往的医生、患者与家属的关系较为紧密,才没有成为问题。换言之,现在安乐死等医疗问题浮上台面,是因为医疗第一线的紧密关系已不复存在。” 然而,他也补充道:“尽管我的想法与推动安乐死立法的人十分接近,但是我与安乐死立法运动还是一直保持着距离。我不明确表示赞成,是因为觉得这个问题无法立法。要是立法通过安乐死,我很担心安乐死会变成某种权利或义务。”我也赞成他的看法。 1.随着“婴儿潮一代”(1945—1965 年出生的日本人)进入“超高龄社会”,日本迎来了一个“无法告别”的时代,人们是否能主动“迎接”死亡,活得有尊严,“走得”也有尊严?生死观、安乐死、尊严死、缓和医疗……我们了解过多少? 2.日本哲学泰斗村上阳一郎以86岁高龄阅历,从零解答:高龄社会已然来临,我们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迎接生命终点? 3.揭秘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传统;安乐死与“尊严死”的区别;现代医学的治愈界限;老去的痛苦如何排解;现代人为何需要树立生死观? 4.视角独特,从哲学与文化角度介绍安乐死问题,借东亚传统与现实 乘哲学与医学之西风关注当下,启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