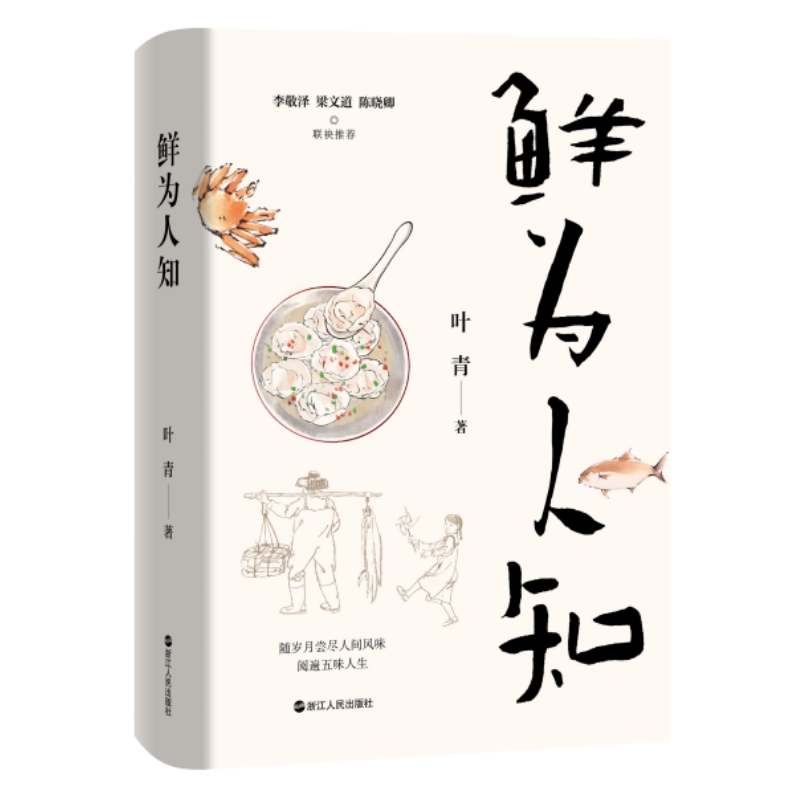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38.80
折扣购买: 鲜为人知(精)
ISBN: 9787213112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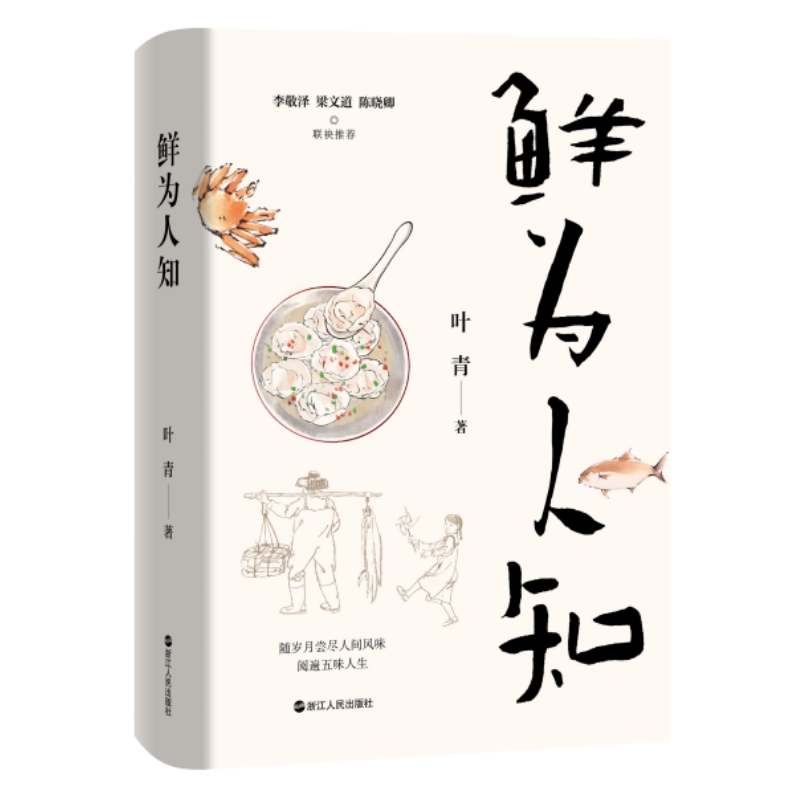
叶 青 叶青,浙江玉环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浙江散文》《浙江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台州日报》等报刊。
干妈的浇头面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幼时三天两头发高烧,不到两周岁,就做了骨髓穿刺。虽然病理结果排除了怀疑的疾患,但外婆着急了。她一生生养过多胎,只有我妈一个活了下来,看我身体虚弱,外婆决定给我认干亲。 旧时,我的家乡有这样的习俗,小孩出生后不容易带,被认为命理八字身弱,风行认干亲,说是有护荫生扶,可以改运,能变得健康易养。通常找人丁兴旺的家庭,通过生辰八字合对认亲。我认了我妈的堂姐为干妈,师范生的妈妈说这是“白菜叶子炒大葱”,亲上加亲(青上加青),觉得很安妥。 拜干亲改命理要从改名字开始。干妈有六个儿子,名字里都带有“辉”字,不识字的干妈便给我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李辉静,跟干爹的姓,顺哥们的“辉”,一个“静”字大致希望我往后日子风平浪静,无灾无难。外婆让道士把我的新名字写在一张黄纸上,附上我的八字,画了几个叫符的图形,交给我的干妈。自此,每年正月初二,我都要去干妈家拜年,三岁开始,历时四十载。 四十碗浇头面,从时光的隧道穿梭而过,向光而来。蓝白相间的青瓷碗上有黄冠高耸,有鹤立亭亭,有抱犊山巅,有江河款款,它们在我面前环绕着,一圈又一圈,时近时远,似镜花水月,又触手可及。我努力伸出双手去捧碗,手却软塌塌的,怎么用力都提不起来,醒来时手按在胸口,这样的梦境时不时袭击我。 浇头面是台州民间特色面点,家里有亲戚远道而来,会煮一碗热腾腾的浇头面款待。提着藤编篮子,抓着鸡鸭去送月子,定能吃到一碗香喷喷的菜油姜浇头面。面点可以是米粉、干挂面或带咸味需要过水煮捞的索面。浇头可谓五花八门,山海不同,南北各异。随着时代的变迁,贮存条件的变化,浇头面的浇头也与时俱进。走亲的浇头比旧时丰富,街肆的浇头面价格不一,有十几元一碗的香菇肉丝面,也有几十元到百元一碗的特色浇头面,而上千元一碗的黄鱼海参鲍鱼面,吃的那是噱头。 干妈的浇头面四十年不变。从六个儿子亟待抚养到各自成家立业,日子从艰辛到宽裕,都是一样的浇头。老家坎门有很多带“岙”字的地名,玉岙、渔岙、钓艚岙、鹰捕岙、墨贼岙等名字都有来历,我干妈住的地方叫岙仔,特别偏僻。三间破旧小石屋,与宗亲合住,各一间半,坐落在海拔一百多米的凹形小山丘上,往东就是濒临东海的悬崖峭壁。这里有一条两米宽的石阶通向山岭头,石阶非常平缓,两侧是依地势而建的石头屋,层层叠叠,居住着本地居民。 长大后独自去干妈家拜年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我一踏上石阶,蹲在井边洗洗涮涮的左邻右舍就和我打招呼——素兰的契姿囝儿(干女儿的闽南语)来拜年了,并站起来大着嗓门对着后一排石屋井边的主妇喊一遍。素兰是我干妈的名字,可见她人缘特别好。这一句招呼像是今天朋友圈的文本,台阶两侧邻里纷纷往上转发,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年代,干妈在我走在石阶上时就已经收到朋友们的信息。她小步跑着,微胖的身体紧跟双手的节奏,双颊的苹果肌像沾染了两抹高原红,随着小跑节奏上下颤动着。每次我登上岭头,她也片刻不差就到了,接过我手中的“手巾包头”,双眼笑成两弯月,那慈祥可亲的样子像极了电视连续剧《人世间》里萨日娜扮演的秉义妈。从岭头到干妈家不到一百米,可一路不知回复了多少个“是啊是啊,我家辉静来拜年了”,她的语气乐呵呵的,浓郁了春节的喜庆。 干爹是渔民,也是红旗渔业大队舞鱼龙灯的高手,每年大年初二上午都坐在屋檐下整理鱼龙灯,似乎在等我,轻轻咕哝一声“来了”,就停下手中活,起身往灶沟间(厨房的闽南语)帮忙。几个未成家的哥哥在一丛鸡冠花边轮流劈甘蔗,这是一种吃甘蔗游戏,他们只对我嘿嘿地笑笑。 干妈的浇头面是用山东粉,也就是现在有名的龙口粉做的,那时的龙口粉是稀罕物,都是托人买来的。浇头可不是用“琳琅满目”一词就形容得了的,有鱼胶、鱼皮馄饨、鱼饼、猪肝、猪肚、猪肺、九节虾、蛏子肉、蛤蜊、黄花菜、香菇,等等。这么多浇头,一个点心碗怎么盛得下呢?家乡有一种大汤碗叫“水碗”,家乡人喜欢汤汤水水,坎门菜曾被不明就里的人说成稀汤寡水一大碗。我家通常配一个大水碗盛汤,可供一家八口人下饭。干妈每年在大水碗上垒塔,再在塔尖上盖一层金黄的煎蛋,任宠爱在碗里泛滥。 鱼胶是干爹从黄鱼肚取出来的,一条条贴在门板上晾干收拾好,存到年底用菜籽油炸至金黄,待我拜年时吃。后来黄鱼少见了,又攒起鱼胶,用作浇头后,剩下的让我带走,现在市面上好几千元也难买到一斤。再说猪下水——猪肺,因为我小时候常发烧还伴有咳嗽,家人认为我肺气薄弱,吃动物内脏可对应补人体的脏器,以至于我好上这一口,喜欢它酥软味腴和咀嚼软骨时脆生生的嘎嘎响。带六个儿子生活粗糙的干妈,却会用最精细的猪肺清洗法,提一木桶一木桶井水往猪肺里灌,反复冲洗浸泡至猪肺至清至白,再在油锅里加姜蒜爆炒后备用。蛏子剥了壳去了体侧线,九节虾挑了泥筋。 那时,我的胃口容不下心里垂涎着的这碗面,干妈也心知肚明,但还是一劝再劝:“多吃点,多吃点才能长肉,不喜欢吃的夹到这个碗里。”她早准备好一个粗瓷碗放在我面前,又从灶沟间端出一碗浓汤,是用山珍海味加入鸡汤熬制的。大年三十杀一只鸡炖汤是他们家一年难得的奢侈,汤先盛出一大碗留给初二煮浇头面。“汤不够再加。”干妈知道我喜欢喝汤,收拾好后坐在我身边油漆剥落的条凳上,上下仔细打量我,和我唠嗑,“怎么没胖一点啊,是不是读书太辛苦?”“还是没长肉,是不是工作太累?”我年轻时食量小,若是今日已练就了饕餮胃口并对美食趋之若鹜的李辉静,定会拿出金庸笔下穆念慈的豪气:“你给煮一碗面条,切四两熟牛肉。”以如此气势把干妈做的比佛跳墙还丰富、还香甜的浇头面吃完,干妈肯定会笑靥如花。 后来我结婚生子,远离家乡,每年初二仍去干妈家拜年。干妈不再是获知信息后匆匆跑来,六个儿子都成家了,劳碌一生的干妈闲了下来,她站在山岭上等我。每年初二翘首以盼,那身姿在我心中如坐定千年。 干爹走后,干妈不再站在山岭上等我,她喜欢上玩纸牌,在当地叫“洞九”,按点数出牌,几个老人一起玩。但当我走上岭头,她就会从某个旧四合院或某家堂房跑出来,搓着手,像个腼腆的孩子,不停地说“亏姆(干妈的闽南语)没事干,就跟她们玩玩”,又是一路招呼乡邻,一路对我问长问短。 2010年的正月初二,我在岭头没见到干妈,到了低矮的门厅时,干妈弯着腰扶着楼梯从小阁楼上下来。她脸色苍白,人也瘦了一圈。她的大儿媳、二儿媳在厨房忙碌,端出了干妈的浇头面。我没心思吃,一再询问干妈是不是病了。她中气十足,声音爽朗地回答我:“亏姆没有病。”“那怎么瘦了?”“千金难买老来瘦,你放心吧,只是胃口不好,人有点乏力,躺几天就会好的。”8月,我出差南美,返程近三十个小时。飞机降落上海浦东机场时,我打开手机准备给家人报平安,妈妈的信息跳出来:“速速回来,干妈病危。”我如被雷击,头晕目眩。 干妈往生了,速速赶回来的我是给干妈送终,我涕泪交流。其实她去医院检查早就得知自己已是胃癌晚期,就一直隐瞒病情,包括自己的六个儿子,她不想给六个儿子增加负担和麻烦。 从此世上再无干妈的龙口粉,再无正月初二干妈的浇头面。 ★李敬泽、梁文道、陈晓卿联合推荐 ★一食一味,都是人间风味;一餐一饭,都带着人情温暖 ★在寻常的岁月中发现生活的丰盛,在平淡的光阴中发现人生的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