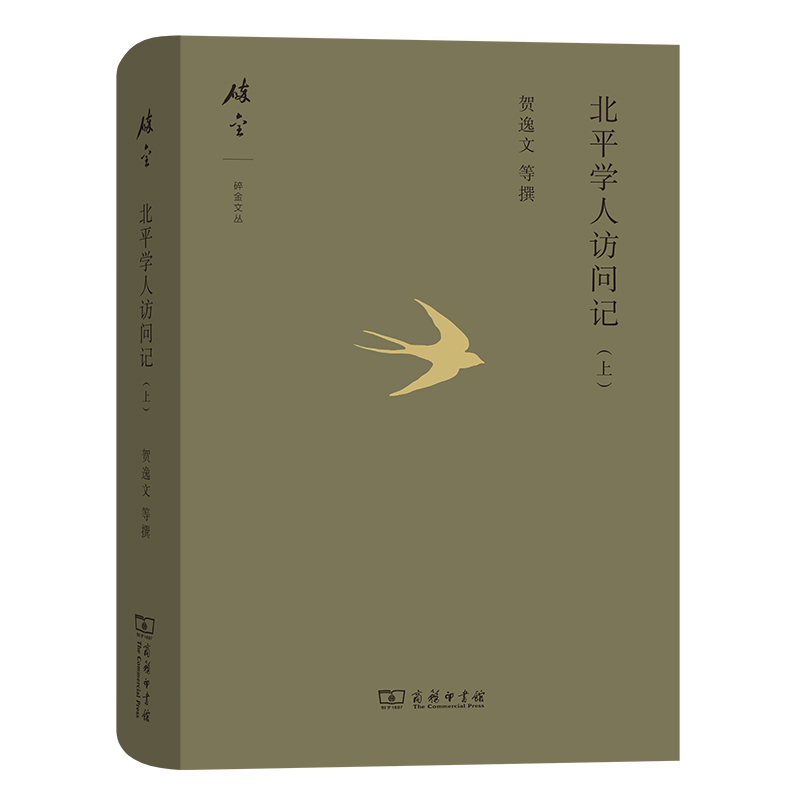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3.60
折扣购买: 北平学人访问记(上)(精)/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1828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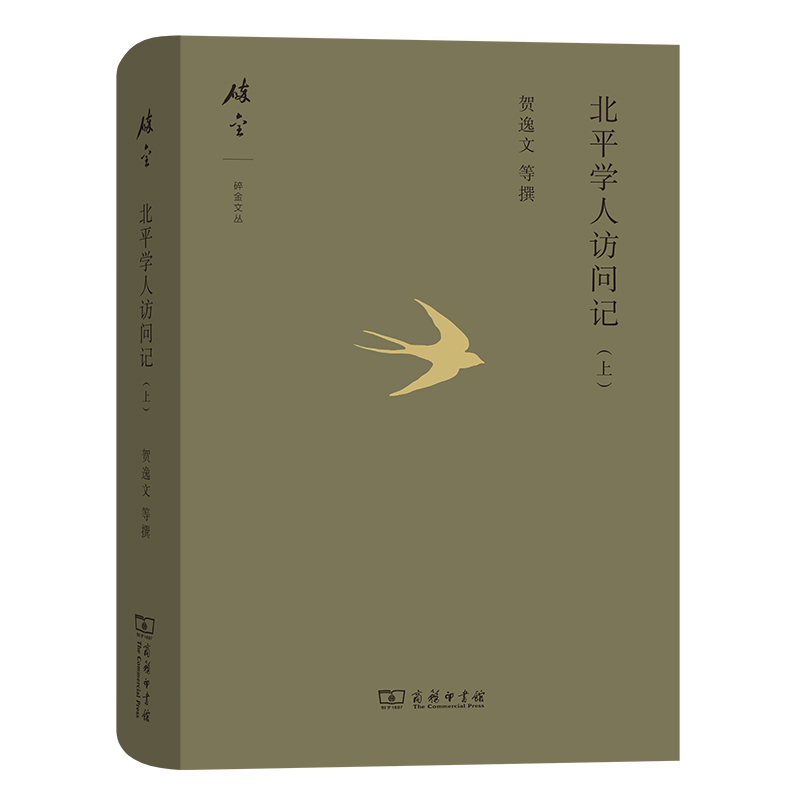
贺逸文(1910—1983),民国知名报人,抗日战争之前在北平《世界日报》工作,担任“教育界”副刊的主编、采访部主任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教务长。
戏剧家余上沅 余定七日离平南下,二 十二日偕梅兰芳赴俄。 “戏剧”是艺术,因为它 不仅包含诗、文学、书法、 雕塑、建筑、音乐、舞蹈各 项的艺术的元素,同时它还 是人生的艺术。然而中国的 社会,不曾把戏剧看得认真 ,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没有 一个适当的“剧”的观念。甚 至于觉得“戏”就是游戏,唱 戏是下流人做的事,所以在 封建社会的时候,“戏子”是 不能中功名的。新文化运动 的黎明,易卜生给旗鼓喧闹 地介绍到中国来了,固然西 洋戏剧的复兴最得力处是易 卜生的介绍,可是中国戏剧 界和西洋当初一样,依然是 在表面上活动,政治问题、 家庭问题、职业问题、烟酒 问题等,做了戏剧的目标。 演说家、雄辩家、传教士, 一个个跳上台去,读词讲道 德。他们不知道探讨人心的 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却 要利用艺术去纠正人心,改 善人类,结果是戏剧愈变愈 繁琐,问题不存在了,戏剧 随之不存在。 在这样紊乱的中国戏剧 界里,有几个为得人生是艺 术的人,在民国十四五年的 时候,运用他们的热忱,做 一种种运动,希望艺术的鲜 花快开,就是“国剧运动”。 那些人是徐志摩、赵太侔、 张嘉铸、余上沅同熊佛西等 。现在为得事实的变迁,同 环境的关系,已各自分散, 仅有极少数未与戏剧运动脱 离关系。余上沅不但是现在 尚未与“戏剧”脱离关系,而 且在过去的戏剧运动上,他 是一个中坚分子。同时他保 持着研究与运用戏剧的雄心 ,他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英文 系教戏剧,同时任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秘书。最 近余氏受了教育部的委托, 同中华文化基金会八个月例 假的机会,他由私人方面筹 划经费,赴欧美考察戏剧。 已定二月七日离平南下,二 十二日由沪与梅兰芳出国赴 俄。记者在余氏未离平之前 ,与他做了一个长时间的谈 话,关于他的略历,同他与 戏剧的关系,给读者做了一 个简单的介绍,想必读者也 是愿意知道的吧。 一、余氏的略历及其与 戏剧的因缘 余氏生于逊清光绪二十 三年(即西历1897年),原籍 是湖北的一个商埠——沙市 。他的家庭是经营商业的, 所以经济很充裕,使着他平 稳地完成他以往的历程同志 愿。同时更因为这种的关系 ,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缘。 他的家庭因为营商的关系, 与山西“票号”时有来往。那 样的来往自然是要应酬的, 而“看戏”却是主要应酬之一 ,所以在戏园里定有长期的 包厢,因此,他能有许多的 机会去看戏,同时也得了许 多机会接近“唱戏”的。 自然,在他那样的家庭 ,不能叫他完全沉溺在戏园 里,所以民国元年时,便送 他到武昌文华大学(今称华 中大学)的中学部里读书。 他在这个学校的时间最长, 除去六年的中学外,并且还 在大学部读了两年书。当他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正是“ 五四”运动兴起,他在学校 里对文化运动的介绍,非常 努力,而且很活动,因此被 举为武汉学生总会的主席, 时常地在公众集会的时候演 说,而且演过两次戏,一次 是当父亲,一次是做一个演 说者,虽然是一种很幼稚的 戏剧表演,却逗引起他蕴蓄 着对于戏剧的兴趣。 后来,不久他便转学到 北京大学英文系,到民国十 年毕业。当他在北大的时候 ,他的朋友同学们因为他过 去活动的关系,都以为他要 去做爱国运动同新文化运动 的活动,然而他自己感到空 虚,却是闭门地读了两年书 ,一直到他毕业的时候。毕 业后,便在清华学堂(即现 在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有 中学部)教书,惟因性之所 近,时常给《晨报副刊》写 些关于戏剧的稿子,而引起 了戏剧界的注意。 民国十二年夏天,得到 清华学堂半官费地送到美国 去读书,他的志愿是学习戏 剧,可以说是他实际从事戏 剧的开始。然而当时同行的 百余人,差不多都是学习普 通文学、政治经济,或理科 的,只有余氏是志愿学戏剧 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发表 以后,颇引起社会上人士的 注意与惊讶,想不到竟有人 肯学漫不着边际的戏剧。因 此他们到上海的时候,便有 些从事或志愿戏剧的人,如 欧阳予倩等,特别地去找他 谈话,并且给了善意的鼓励 。尤其是当时的蒲伯英,对 他更为鼓励。特别约他谈话 ,并且相约等他回国的时候 ,将其经办的人艺戏剧学校 ,交给余氏办理。可是余氏 未回国,这个学校便停办了 。记者这次和他谈起来的时 候,余氏还说:“我很感谢 蒲先生的知遇,可惜没得着 机会帮他的忙。”P9-12 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民国学人是中国学术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这批学人由于因缘际会,既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交汇点上,又处于东方与西方的中西沟通线上,有其不可复制的养成条件。群星璀璨之下,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其有着怎样的学术成长经历,学成归来后又处于怎样的环境中,做出了什么贡献,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预期,如此种种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前都分散于诸位学人各自的自传中,待研究者一一撷取。而这本《北平学人访问记》恰恰通过记者的观察和记录,为这批学人描摹出了一个面目鲜明又生态丰富的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