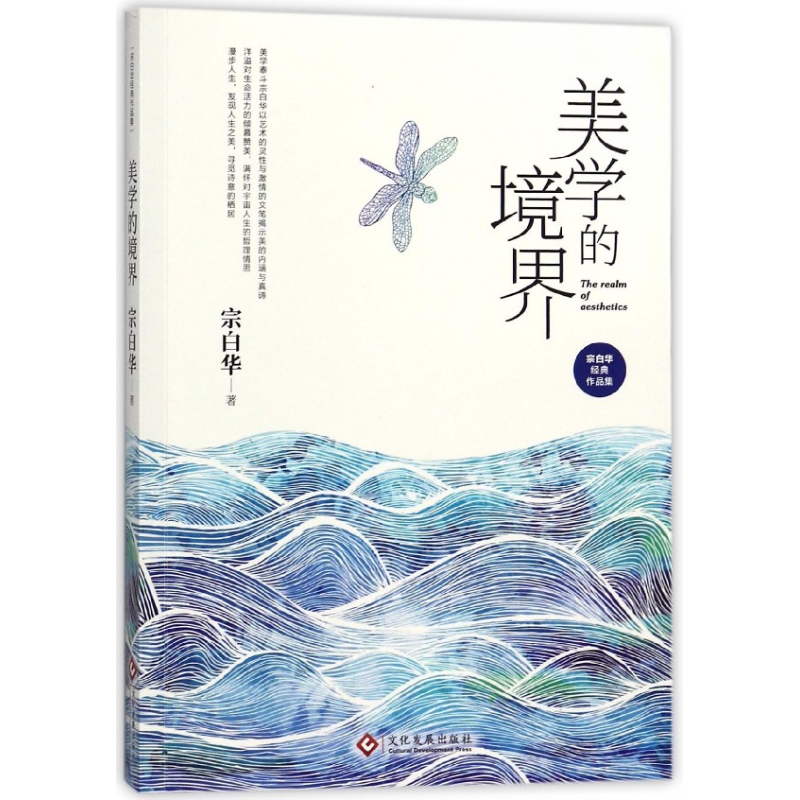
出版社: 文化发展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美学的境界(宗白华经典作品集)
ISBN: 9787514219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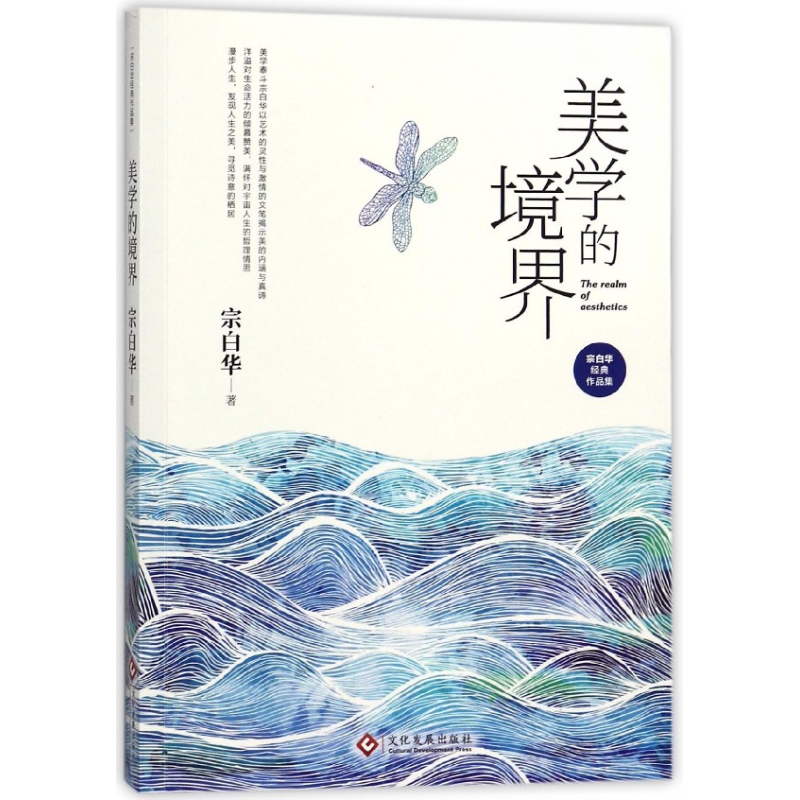
宗白华,哲学家、美学大师、诗人,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语言科,1920到1925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回国后,自30年代起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49到1952年任南京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之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顾问。
美从何处寻? [1] 啊,诗从何处寻? 从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流云小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载某尼悟道诗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我们都是从目观耳 听的世界里寻得她的踪迹。某尼悟道诗大有禅意,好像是说“道不远人”,不 应该“道在迩而求诸远”。好像是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 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 然而梅花仍是一个外界事物呀,大自然的一部分呀!你的心不是“在”自 己的心的过程里,感觉、情绪、思维里找到美;而只是“通过”感觉、情绪、 思维找到美,发现梅花里的美。美对于你的心,你的“美感”是客观的对象和 [1] 本文原载于《新建设》,1957 年第6 期。—编者 003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存在。你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她,你可以分析她的结构、形象、组成的各部分, 得出“谐和”的规律、“节奏”的规律、表现的内容、丰富的启示,而不必顾 到你自己的心的活动,你越能忘掉自我,忘掉你自己的情绪波动,思维起伏, 你就越能够“潄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你就会像一面镜子,像托尔 斯泰那样,照见了一个世界,丰富了自己,也丰富了文化。人们会感谢你的。 那么,你在自己的心里就找不到美了吗?我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起伏万 变,经常碰到情感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 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感亚或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 或是你自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你的欢乐表现在舞蹈的形象里,或把你的 忧郁歌咏在有节奏的诗歌里,甚至于在你的平日的行动里、语言里。一句话, 就是你的心要具体地表现在形象里,那时旁人会看见你的心灵的美,你自己也 才真正地切实地具体地发现你的心里的美。除此以外,恐怕不容易吧!你的心 可以发现美的对象(人生的,社会的,自然的),这“美”对于你是客观的存 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的意志只能指使你的眼睛去看她,或不去看她, 却不能改变她。你能训练你的眼睛深一层地去认识她,却不能动摇她。希腊伟 大的艺术不因中古时代而减少它的光辉。) 宋朝某尼虽然似乎悟道,然而她的觉悟不够深,不够高,她不能发现整个 宇宙已经盎然有春意,假使梅花枝上已经春满十分了。她在踏遍陇头云时是苦 闷的、失望的。她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心的圈子里了。只在自己的心里去找寻美 的踪迹是不够的,是大有问题的。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是东晋大书 法家在寻找美的踪迹。他的书法传达了自然的美和精神的美。不仅是大宇宙, 小小的事物也不可忽视。诗人华滋沃斯曾经说过:“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 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 达到这样的、深入的美感,发现这样深度的美,是要在主观心理方面具 有条件和准备的。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 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和特性。我们要把美从何处寻? [1] 啊,诗从何处寻? 从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流云小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载某尼悟道诗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我们都是从目观耳 听的世界里寻得她的踪迹。某尼悟道诗大有禅意,好像是说“道不远人”,不 应该“道在迩而求诸远”。好像是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 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 然而梅花仍是一个外界事物呀,大自然的一部分呀!你的心不是“在”自 己的心的过程里,感觉、情绪、思维里找到美;而只是“通过”感觉、情绪、 思维找到美,发现梅花里的美。美对于你的心,你的“美感”是客观的对象和 [1] 本文原载于《新建设》,1957 年第6 期。—编者 003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存在。你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她,你可以分析她的结构、形象、组成的各部分, 得出“谐和”的规律、“节奏”的规律、表现的内容、丰富的启示,而不必顾 到你自己的心的活动,你越能忘掉自我,忘掉你自己的情绪波动,思维起伏, 你就越能够“潄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你就会像一面镜子,像托尔 斯泰那样,照见了一个世界,丰富了自己,也丰富了文化。人们会感谢你的。 那么,你在自己的心里就找不到美了吗?我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起伏万 变,经常碰到情感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 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感亚或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 或是你自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你的欢乐表现在舞蹈的形象里,或把你的 忧郁歌咏在有节奏的诗歌里,甚至于在你的平日的行动里、语言里。一句话, 就是你的心要具体地表现在形象里,那时旁人会看见你的心灵的美,你自己也 才真正地切实地具体地发现你的心里的美。除此以外,恐怕不容易吧!你的心 可以发现美的对象(人生的,社会的,自然的),这“美”对于你是客观的存 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的意志只能指使你的眼睛去看她,或不去看她, 却不能改变她。你能训练你的眼睛深一层地去认识她,却不能动摇她。希腊伟 大的艺术不因中古时代而减少它的光辉。) 宋朝某尼虽然似乎悟道,然而她的觉悟不够深,不够高,她不能发现整个 宇宙已经盎然有春意,假使梅花枝上已经春满十分了。她在踏遍陇头云时是苦 闷的、失望的。她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心的圈子里了。只在自己的心里去找寻美 的踪迹是不够的,是大有问题的。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是东晋大书 法家在寻找美的踪迹。他的书法传达了自然的美和精神的美。不仅是大宇宙, 小小的事物也不可忽视。诗人华滋沃斯曾经说过:“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 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 达到这样的、深入的美感,发现这样深度的美,是要在主观心理方面具 有条件和准备的。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 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和特性。我们要把 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了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 004 美学的境界 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 艺术。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琴曲《伯 牙水仙操》的序上说: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 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赉粮从之,至蓬莱 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 但闻海水汩波,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操 而作歌云:“繄洞庭兮流斯护,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 钦伤宫 仙不还。” 伯牙由于在孤寂中受到大自然强烈的震撼,生活上的异常遭遇,整个心 境受了洗涤和改造,才达到艺术的最深体会,把握到音乐的创造性的旋律,完 成他的美的感受和创造。这个“移情说”比起德国美学家栗卜斯的“情感移入 论”似乎还要深刻些,因为它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改造是“移情”的基础 呀!并且“移易”和“移入”是不同的。 这里我所说的“移情”应当是我们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而 美学家所说的“心理距离”“静观”,则构成审美的消极条件。女子郭六芳有一 首诗《舟还长沙》说得好: 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 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 形象里。 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德 国表现主义先驱保拉·莫德松·贝克尔所绘里尔克像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 005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宋人陈简斋的海棠诗云:“隔帘花叶有辉光”。帘子 造成了距离,同时它的线文的节奏也更能把帘外的花叶纳进美的形象,增高了 它的光辉闪灼,呈显出生命的华美,就像一段欢愉生活嵌在素朴而具有优美旋 律的歌词里一样。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 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 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 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 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又说:“创造一 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节奏,而且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 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不仅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格 式或图形,而是一种恰是如此思想感情的方式”,而具有着理想的形式的诗是 “如此这般的诗,以致我们看不见所谓诗,而但注意着诗所指示的东西”(《诗 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 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部结构 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 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 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了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 004 美学的境界 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 艺术。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琴曲《伯 牙水仙操》的序上说: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 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赉粮从之,至蓬莱 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 但闻海水汩波,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操 而作歌云:“繄洞庭兮流斯护,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 钦伤宫 仙不还。” 伯牙由于在孤寂中受到大自然强烈的震撼,生活上的异常遭遇,整个心 境受了洗涤和改造,才达到艺术的最深体会,把握到音乐的创造性的旋律,完 成他的美的感受和创造。这个“移情说”比起德国美学家栗卜斯的“情感移入 论”似乎还要深刻些,因为它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改造是“移情”的基础 呀!并且“移易”和“移入”是不同的。 这里我所说的“移情”应当是我们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而 美学家所说的“心理距离”“静观”,则构成审美的消极条件。女子郭六芳有一 首诗《舟还长沙》说得好: 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 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 形象里。 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德 国表现主义先驱保拉·莫德松·贝克尔所绘里尔克像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 005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宋人陈简斋的海棠诗云:“隔帘花叶有辉光”。帘子 造成了距离,同时它的线文的节奏也更能把帘外的花叶纳进美的形象,增高了 它的光辉闪灼,呈显出生命的华美,就像一段欢愉生活嵌在素朴而具有优美旋 律的歌词里一样。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 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 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 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 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又说:“创造一 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节奏,而且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 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不仅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格 式或图形,而是一种恰是如此思想感情的方式”,而具有着理想的形式的诗是 “如此这般的诗,以致我们看不见所谓诗,而但注意着诗所指示的东西”(《诗 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 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部结构 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 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 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 “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有一段话精深微 妙,梁宗岱曾把它译出,现介绍如下: ……一个人早年作的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 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 大家所想象,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要写一句诗, 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 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势。得要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 光光望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 006 美学的境界 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别一人设的欢喜)和离奇变幻的小孩 子的病,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 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未足,还要享受过许多 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地便瞑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 曾经坐在临终人的床头和死者的身边,在那打开的、外边的声音一阵阵拥进来 的房里。可是单有记忆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 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 成我们的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己了, 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 这里是大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现 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 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 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 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我们上面所引长沙女子郭六芳诗中说过:“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 图中”,这是心理距离构成审美的条件。但是“十二珠帘夕照红”却构成这幅 美的形象的客观的积极的因素。夕照、月明、灯光、帘幕、薄纱、轻雾,人人 知道是助成美的出现的有力的因素,现代的照相术和舞台布景知道这个而尽量 利用着。中国古人曾经唤做“移世界”。 明朝文人张大复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里记述着: 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 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 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 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 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酱盎 007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纷然,瓦石布地而已,戏书此以信茂齐之语,时十月十六日,万历丙午三十四 年也。” 月亮真是一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替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现在 眼前。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瓦石布地而已。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美是不 存在的。我却要更进一步推论说象里 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 “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有一段话精深微 妙,梁宗岱曾把它译出,现介绍如下: ……一个人早年作的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 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 大家所想象,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要写一句诗, 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 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势。得要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 光光望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 006 美学的境界 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别一人设的欢喜)和离奇变幻的小孩 子的病,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 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未足,还要享受过许多 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地便瞑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 曾经坐在临终人的床头和死者的身边,在那打开的、外边的声音一阵阵拥进来 的房里。可是单有记忆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 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 成我们的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己了, 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 这里是大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现 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 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 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 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我们上面所引长沙女子郭六芳诗中说过:“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 图中”,这是心理距离构成审美的条件。但是“十二珠帘夕照红”却构成这幅 美的形象的客观的积极的因素。夕照、月明、灯光、帘幕、薄纱、轻雾,人人 知道是助成美的出现的有力的因素,现代的照相术和舞台布景知道这个而尽量 利用着。中国古人曾经唤做“移世界”。 明朝文人张大复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里记述着: 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 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 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 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 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酱盎 007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纷然,瓦石布地而已,戏书此以信茂齐之语,时十月十六日,万历丙午三十四 年也。” 月亮真是一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替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现在 眼前。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瓦石布地而已。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美是不 存在的。我却要更进一步推论说,瓦石也只是无色、无形的原子或电磁波,而 这个也只是思想的假设,我们能抓住的只是一堆抽象数学方程式而已。究竟什 么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回转头来说,我们现实生活里直接经验到的、不 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丰富多彩的、有声有色有形有相的世界就是真实存在 的世界,这是我们生活和创造的园地。所以马克思很欣赏近代唯物论的第一个 创始者培根的著作里所说的物质以其感觉的诗意的光辉向着整个的人微笑(见 《神圣家族》),而不满意霍布士的唯物论里“感觉失去了它的光辉而变为几何 学家的抽象感觉,唯物论变成了厌世论”。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色、声、 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色、声中的美更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世界成 了灰白色的骸骨,机械的死的过程。恩格斯也主张我们的思想要像一面镜子, 如实地反映这多彩的世界。美是存在着的!世界是美的,生活是美的。它和真 和善是人类社会努力的目标,是哲学探索和建立的对象。 美不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教 育着我们,提高生活的境界和意趣。它的力量大极了,它也可以倾国倾城。希 腊大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歌咏希腊联军围攻特罗亚九年,为的是 夺回美人海伦,而海伦的美叫他们感到九年的辛劳和牺牲不是白费的。现在引 述这一段名句: 特罗亚长老们也一样的高踞城雉, 当他们看见了海伦在城垣上出现, 老人们便轻轻低语,彼此交谈机密: “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阿开人, 为了这个女人这么久忍受苦难呢, 008 美学的境界 她看来活像一个青春常驻的女神。 可是,尽管她多美,也让她乘船去吧, 别留这里给我们子子孙孙作祸根。” —(缪朗山译《伊利亚特》) 荷马不用浓丽的辞藻来描绘海伦的容貌,而从她的巨大的惨酷的影响和 力量轻轻地点出她的倾国倾城的美。这是他的艺术高超处,也是后人所赞叹 不已的。 我们寻到美了吗?我说,我们或许接触到美的力量,肯定了她的存在, 而她的无限的丰富内含却是不断地待我们去发现。千百年来的诗人艺术家已 经发现了不少,保藏在他们的作品里,千百年后的世界仍会有新的表现。每 一个造出新节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 009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美学散步(一)[1] 小 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 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 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 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 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 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 芬奇在米兰街头 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 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 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诗(文学)和画的分界 ,瓦石也只是无色、无形的原子或电磁波,而 这个也只是思想的假设,我们能抓住的只是一堆抽象数学方程式而已。究竟什 么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回转头来说,我们现实生活里直接经验到的、不 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丰富多彩的、有声有色有形有相的世界就是真实存在 的世界,这是我们生活和创造的园地。所以马克思很欣赏近代唯物论的第一个 创始者培根的著作里所说的物质以其感觉的诗意的光辉向着整个的人微笑(见 《神圣家族》),而不满意霍布士的唯物论里“感觉失去了它的光辉而变为几何 学家的抽象感觉,唯物论变成了厌世论”。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色、声、 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色、声中的美更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世界成 了灰白色的骸骨,机械的死的过程。恩格斯也主张我们的思想要像一面镜子, 如实地反映这多彩的世界。美是存在着的!世界是美的,生活是美的。它和真 和善是人类社会努力的目标,是哲学探索和建立的对象。 美不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教 育着我们,提高生活的境界和意趣。它的力量大极了,它也可以倾国倾城。希 腊大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歌咏希腊联军围攻特罗亚九年,为的是 夺回美人海伦,而海伦的美叫他们感到九年的辛劳和牺牲不是白费的。现在引 述这一段名句: 特罗亚长老们也一样的高踞城雉, 当他们看见了海伦在城垣上出现, 老人们便轻轻低语,彼此交谈机密: “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阿开人, 为了这个女人这么久忍受苦难呢, 008 美学的境界 她看来活像一个青春常驻的女神。 可是,尽管她多美,也让她乘船去吧, 别留这里给我们子子孙孙作祸根。” —(缪朗山译《伊利亚特》) 荷马不用浓丽的辞藻来描绘海伦的容貌,而从她的巨大的惨酷的影响和 力量轻轻地点出她的倾国倾城的美。这是他的艺术高超处,也是后人所赞叹 不已的。 我们寻到美了吗?我说,我们或许接触到美的力量,肯定了她的存在, 而她的无限的丰富内含却是不断地待我们去发现。千百年来的诗人艺术家已 经发现了不少,保藏在他们的作品里,千百年后的世界仍会有新的表现。每 一个造出新节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 009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美学散步(一)[1] 小 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 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 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 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 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 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 芬奇在米兰街头 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 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 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诗(文学)和画的分界 苏东坡论唐朝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 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1] 本文原载于《新建设》,1957 年第7 期。在收入《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和《艺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时,由编者删去原题目中的“(一)”改为 《美学的散步》,现恢复。—编者 010 美学的境界 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 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 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 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 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 能直接画出来。这位补诗的人也正是从王维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 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 画有人物,那会更好的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 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 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恰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 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 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 “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 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 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是 个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人,然而他的话是有道理的。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 东施以活人来效颦西施尚且失败,何况是画家调脂弄粉。那画不出的“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 同在我们眼面前。达? 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在该画 初完成时,当也能给予我们同样新鲜生动的感受。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 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象 里追寻旧影了。我曾经坐在原画前默默领略了一小时,口里念着我们古人的诗 句,觉得诗启发了画中意态,画给予诗以具体形象,诗画交辉,意境丰满,各 不相下,各有千秋。 011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达? 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 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 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 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探索这微妙的分界,正是近代美学开创时为自 己提出了的任务。 十苏东坡论唐朝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 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1] 本文原载于《新建设》,1957 年第7 期。在收入《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和《艺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时,由编者删去原题目中的“(一)”改为 《美学的散步》,现恢复。—编者 010 美学的境界 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 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 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 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 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 能直接画出来。这位补诗的人也正是从王维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 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 画有人物,那会更好的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 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 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恰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 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 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 “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 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 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是 个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人,然而他的话是有道理的。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 东施以活人来效颦西施尚且失败,何况是画家调脂弄粉。那画不出的“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 同在我们眼面前。达? 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在该画 初完成时,当也能给予我们同样新鲜生动的感受。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 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象 里追寻旧影了。我曾经坐在原画前默默领略了一小时,口里念着我们古人的诗 句,觉得诗启发了画中意态,画给予诗以具体形象,诗画交辉,意境丰满,各 不相下,各有千秋。 011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达? 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 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 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 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探索这微妙的分界,正是近代美学开创时为自 己提出了的任务。 十八世纪德国思想家莱辛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美学名著《拉奥 孔》或称《论画和诗的分界》。但《拉奥孔》却是主要地分析着希腊晚期一座 雕像群,拿它代替了对画的分析,雕像同画同是空间里的造型艺术,本可相 通。而莱辛所说的诗也是指的戏剧和史诗,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因为我们谈到 诗往往是偏重抒情诗。固然这也是相通的,同是属于在时间里表现其境界与行 动的文学。 拉奥孔(Laokoon)是希腊古代传说里特罗亚城一个祭师,他对他的人民 警告了希腊军用木马偷运兵士进城的诡计,因而触怒了袒护希腊人的阿波罗神。 当他在海滨祭祀时,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从海边游来的大蛇捆绕着他们三 人的身躯,拉奥孔被蛇咬着,环视两子正在垂死挣扎,他的精神和肉体都陷入 莫大的悲愤痛苦之中。拉丁诗人维琪尔曾在史诗中咏述此景,说拉奥孔痛极狂 吼,声震数里,但是发掘出来的希腊晚期雕像群著名的拉奥孔(现存罗马梵蒂 冈博物院),却表现着拉奥孔的嘴仅微微启开呻吟着,并不是狂吼,全部雕像给 人的印象是在极大的悲剧的苦痛里保持着镇定、静穆。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者 温克尔曼对这雕像群写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描述,影响着歌德及德国许多古典作 家和美学家,掀起了纷纷的讨论。现在我先将他这段描写介绍出来,然后再谈 莱辛由此所发挥的画和诗的分界。 温克尔曼(Winckelmann,1717—1768 年)在他的早期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 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里曾有下列一段论希腊雕刻的名句: 希腊杰作的一般主要的特征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一种静穆的伟大,既在姿 态上,也在表情里。 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静寂里,不管它的表面多么狂涛汹涌,在希腊人 012 美学的境界 的造像里那表情展示一个伟大的沉静的灵魂,尽管是处在一切激情里面。 在极端强烈的痛苦里,这种心灵描绘在拉奥孔的脸上,并且不单是在脸上。 在一切肌肉和筋络所展现的痛苦,不用向脸上和其他部分去看,仅仅看到那因痛 苦而向内里收缩着的下半身,我们几乎会在自己身上感觉着。然而这痛苦,我 说,并不曾在脸上和姿态上用愤激表示出来。他没有像维琪尔在他拉奥孔( 诗) 里所歌咏的那样喊出可怕的悲吼,因嘴的孔穴不允许这样做(白华按:这是指 雕像的脸上张开了大嘴,显示一个黑洞,很难看,破坏了美),这里只是一声畏 怯的敛住气的叹息,像沙多勒所描写的。 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伟大是经由形体全部结构用同等的强度分布着, 并且平衡着。拉奥孔忍受着, 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菲诺克太特 (Philoctet):他的困苦感动到我们的深心里,但是我们愿望也能够像这个伟大 人格那样忍耐困苦。一个这样伟大心灵的表情远远超越了美丽自然的构造物。 艺术家必须先在自己内心里感觉到他要印入他的大理石里的那精神的强度。希 腊具有集合艺术家与圣哲于一身的人物,并且不止一个梅特罗多。智慧伸手给 艺术而将超俗的心灵吹进艺术的形象。 莱辛认为温克尔曼所指出的拉奥孔脸上并没有表示人所期待的那强烈苦痛 的疯狂表情,是正确的。但是温克尔曼把理由放在希腊人的智慧克制着内心感 情的过分表现上,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 肉体遭受剧八世纪德国思想家莱辛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美学名著《拉奥 孔》或称《论画和诗的分界》。但《拉奥孔》却是主要地分析着希腊晚期一座 雕像群,拿它代替了对画的分析,雕像同画同是空间里的造型艺术,本可相 通。而莱辛所说的诗也是指的戏剧和史诗,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因为我们谈到 诗往往是偏重抒情诗。固然这也是相通的,同是属于在时间里表现其境界与行 动的文学。 拉奥孔(Laokoon)是希腊古代传说里特罗亚城一个祭师,他对他的人民 警告了希腊军用木马偷运兵士进城的诡计,因而触怒了袒护希腊人的阿波罗神。 当他在海滨祭祀时,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从海边游来的大蛇捆绕着他们三 人的身躯,拉奥孔被蛇咬着,环视两子正在垂死挣扎,他的精神和肉体都陷入 莫大的悲愤痛苦之中。拉丁诗人维琪尔曾在史诗中咏述此景,说拉奥孔痛极狂 吼,声震数里,但是发掘出来的希腊晚期雕像群著名的拉奥孔(现存罗马梵蒂 冈博物院),却表现着拉奥孔的嘴仅微微启开呻吟着,并不是狂吼,全部雕像给 人的印象是在极大的悲剧的苦痛里保持着镇定、静穆。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者 温克尔曼对这雕像群写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描述,影响着歌德及德国许多古典作 家和美学家,掀起了纷纷的讨论。现在我先将他这段描写介绍出来,然后再谈 莱辛由此所发挥的画和诗的分界。 温克尔曼(Winckelmann,1717—1768 年)在他的早期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 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里曾有下列一段论希腊雕刻的名句: 希腊杰作的一般主要的特征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一种静穆的伟大,既在姿 态上,也在表情里。 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静寂里,不管它的表面多么狂涛汹涌,在希腊人 012 美学的境界 的造像里那表情展示一个伟大的沉静的灵魂,尽管是处在一切激情里面。 在极端强烈的痛苦里,这种心灵描绘在拉奥孔的脸上,并且不单是在脸上。 在一切肌肉和筋络所展现的痛苦,不用向脸上和其他部分去看,仅仅看到那因痛 苦而向内里收缩着的下半身,我们几乎会在自己身上感觉着。然而这痛苦,我 说,并不曾在脸上和姿态上用愤激表示出来。他没有像维琪尔在他拉奥孔( 诗) 里所歌咏的那样喊出可怕的悲吼,因嘴的孔穴不允许这样做(白华按:这是指 雕像的脸上张开了大嘴,显示一个黑洞,很难看,破坏了美),这里只是一声畏 怯的敛住气的叹息,像沙多勒所描写的。 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伟大是经由形体全部结构用同等的强度分布着, 并且平衡着。拉奥孔忍受着, 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菲诺克太特 (Philoctet):他的困苦感动到我们的深心里,但是我们愿望也能够像这个伟大 人格那样忍耐困苦。一个这样伟大心灵的表情远远超越了美丽自然的构造物。 艺术家必须先在自己内心里感觉到他要印入他的大理石里的那精神的强度。希 腊具有集合艺术家与圣哲于一身的人物,并且不止一个梅特罗多。智慧伸手给 艺术而将超俗的心灵吹进艺术的形象。 莱辛认为温克尔曼所指出的拉奥孔脸上并没有表示人所期待的那强烈苦痛 的疯狂表情,是正确的。但是温克尔曼把理由放在希腊人的智慧克制着内心感 情的过分表现上,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 肉体遭受剧烈痛苦时大声喊叫以减轻痛苦,是合乎人情的,也是很自然的 现象。希腊人的史诗里毫不讳言神们的这种人情味。维纳斯(美丽的爱神)玉 体被刺痛时,不禁狂叫,没有时间照顾到脸相的难看了。荷马史诗里战士受伤 倒地时常常大声叫痛。照他们的事业和行动来看,他们是超凡的英雄;照他们 的感觉情绪来看,他们仍是真实的人。所以拉奥孔在希腊雕像上那样微呻不是 由于希腊人的品德如此,而应当到各种艺术的材料的不同,表现可能性的不同 和它们的限制里去找它的理由。莱辛在他的《拉奥孔》里说: 有一些激情和某种程度的激情,它们经由极丑的变形表现出来,以至于将 013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整个身体陷入那样勉强的姿态里,使他的在静息状态里具有的一切美丽线条都 丧失掉了。因此古代艺术家完全避免这个,或是把它的程度降低下来,使它能 够保持某种程度的美。 把这思想运用到拉奥孔上,我所追寻的原因就显露出来了。那位巨匠是在 所假定的肉体的巨大痛苦情况下企图实现最高的美。在那丑化着一切的强烈情 感里,这痛苦是不能和美相结合的。巨匠必须把痛苦降低些;他必须把狂吼软 化为叹息;并不是因为狂吼暗示着一个不高贵的灵魂,而是因为它把脸相在一 难堪的样式里丑化了。人们只要设想拉奥孔的嘴大大张开着而评判一下。人们 让他狂吼着再看看…… 莱辛的意思是:并不是道德上的考虑使拉奥孔雕像不像在史诗里那样痛极大 吼,而是雕刻的物质的表现条件在直接观照里显得不美(在史诗里无此情况),因 而雕刻家(画家也一样)须将表现的内容改动一下,以配合造型艺术由于物质表 现方式所规定的条件。这是各种艺术的特殊的内在规律,艺术家若不注意它,遵 守它,就不能实现美,而美是艺术的特殊目的。若放弃了美,艺术可以供给知识, 宣扬道德,服务于实际的某一目的,但不是艺术了。艺术须能表现人生的有价值 的内容,这是无疑的,但艺术作为艺术而不是文化的其他部门,它就必须同时表 现美,把生活内容提高、集中、精粹化,这是它的任务。根据这个任务各种艺术 因物质条件不同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内在规律。拉奥孔在史诗里可以痛极大吼, 声闻数里,而在雕像里却变成小口微呻了。 莱辛这个创造性的分析启发了以后艺术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艺术科学的 方向,虽然他自己的研究仍是有局限性的。造型艺术和文学的界限并不如他所 说的那样窄狭、严格,艺术天才往往突破规律而有所成就,开辟新领域、新境 界。罗丹就曾创造了疯狂大吼、躯体扭曲,失了一切美的线纹的人物,而仍不 失为艺术杰作,创造了一种新的美。但莱辛提出问题是好的,是需要进一步作 科学的探讨的,这是构成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近代美学家颇有用《新拉 奥孔》标名他的著作的。 我现在翻译他的《拉奥孔》里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论诗里和造型艺术 014 美学的境界 里的身体美,这段文字可以献给朋友在美学散步中做思考资料。莱辛说: 身体美是产生于一眼能够全面看到的各部分协调的结果。因此要求这些 部分相互并列着,而这各部分相互并列着的事物正是绘画的对象。所以绘画能 够、也只有它能够摹绘身体的美。 诗人只能将美的各要素相继地指说出来,所以他完全避免对身体的美作为美来 烈痛苦时大声喊叫以减轻痛苦,是合乎人情的,也是很自然的 现象。希腊人的史诗里毫不讳言神们的这种人情味。维纳斯(美丽的爱神)玉 体被刺痛时,不禁狂叫,没有时间照顾到脸相的难看了。荷马史诗里战士受伤 倒地时常常大声叫痛。照他们的事业和行动来看,他们是超凡的英雄;照他们 的感觉情绪来看,他们仍是真实的人。所以拉奥孔在希腊雕像上那样微呻不是 由于希腊人的品德如此,而应当到各种艺术的材料的不同,表现可能性的不同 和它们的限制里去找它的理由。莱辛在他的《拉奥孔》里说: 有一些激情和某种程度的激情,它们经由极丑的变形表现出来,以至于将 013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整个身体陷入那样勉强的姿态里,使他的在静息状态里具有的一切美丽线条都 丧失掉了。因此古代艺术家完全避免这个,或是把它的程度降低下来,使它能 够保持某种程度的美。 把这思想运用到拉奥孔上,我所追寻的原因就显露出来了。那位巨匠是在 所假定的肉体的巨大痛苦情况下企图实现最高的美。在那丑化着一切的强烈情 感里,这痛苦是不能和美相结合的。巨匠必须把痛苦降低些;他必须把狂吼软 化为叹息;并不是因为狂吼暗示着一个不高贵的灵魂,而是因为它把脸相在一 难堪的样式里丑化了。人们只要设想拉奥孔的嘴大大张开着而评判一下。人们 让他狂吼着再看看…… 莱辛的意思是:并不是道德上的考虑使拉奥孔雕像不像在史诗里那样痛极大 吼,而是雕刻的物质的表现条件在直接观照里显得不美(在史诗里无此情况),因 而雕刻家(画家也一样)须将表现的内容改动一下,以配合造型艺术由于物质表 现方式所规定的条件。这是各种艺术的特殊的内在规律,艺术家若不注意它,遵 守它,就不能实现美,而美是艺术的特殊目的。若放弃了美,艺术可以供给知识, 宣扬道德,服务于实际的某一目的,但不是艺术了。艺术须能表现人生的有价值 的内容,这是无疑的,但艺术作为艺术而不是文化的其他部门,它就必须同时表 现美,把生活内容提高、集中、精粹化,这是它的任务。根据这个任务各种艺术 因物质条件不同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内在规律。拉奥孔在史诗里可以痛极大吼, 声闻数里,而在雕像里却变成小口微呻了。 莱辛这个创造性的分析启发了以后艺术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艺术科学的 方向,虽然他自己的研究仍是有局限性的。造型艺术和文学的界限并不如他所 说的那样窄狭、严格,艺术天才往往突破规律而有所成就,开辟新领域、新境 界。罗丹就曾创造了疯狂大吼、躯体扭曲,失了一切美的线纹的人物,而仍不 失为艺术杰作,创造了一种新的美。但莱辛提出问题是好的,是需要进一步作 科学的探讨的,这是构成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近代美学家颇有用《新拉 奥孔》标名他的著作的。 我现在翻译他的《拉奥孔》里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论诗里和造型艺术 014 美学的境界 里的身体美,这段文字可以献给朋友在美学散步中做思考资料。莱辛说: 身体美是产生于一眼能够全面看到的各部分协调的结果。因此要求这些 部分相互并列着,而这各部分相互并列着的事物正是绘画的对象。所以绘画能 够、也只有它能够摹绘身体的美。 诗人只能将美的各要素相继地指说出来,所以他完全避免对身体的美作为美来 描绘。他感觉到把这些要素相继地列数出来,不可能获得像它并列时那种效果,我们 若想根据这相继地一一指说出来的要素而向它们立刻凝视,是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统一 的协调的图画的。要想构想这张嘴和这个鼻子和这双眼睛集在一起时会有怎样一个效 果是超越了人的想象力的,除非人们能从自然里或艺术里回忆到这些部分组成的一个 类似的结构(白华按:读“巧笑倩兮”……时不用做此笨事,不用设想是中国或西方 美人而情态如见,诗意具足,画意也具足)。 在这里,荷马常常是模范中的模范。他只说,尼惹斯是美的,阿奚里更 美,海伦具有神仙似的美。但他从不陷落到这些美的周密的啰唆的描述。他的 全诗可以说是建筑在海伦的美上面的,一个近代的诗人将要怎样冗长地来叙说 这美呀! 但是如果人们从诗里面把一切身体美的画面去掉,诗不会损失过多少?谁 要把这个从诗里去掉?当人们不愿意它追随一个姊妹艺术的脚步来达到这些画 面时,难道就关闭了一切别的道路了吗?正是这位荷马,他这样故意避免一切 片断地描绘身体美的,以至于我们在翻阅时很不容易地有一次获悉海伦具有雪 白的臂膀和金色的头发,(《伊利亚特》Ⅳ,第319 行)正是这位诗人他仍然懂 得使我们对她的美获得一个概念,而这一美的概念是远远超过了艺术在这企图 中所能达到的。人们试回忆诗中那一段,当海伦到特罗亚人民的长老集会面前, 那些尊贵的长老们瞥见她时,一个对一个耳边说: “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阿开人,为了这个女人这么久忍受着苦难呢, 看来她活像一个青春常驻的女神。” 还有什么能给我们一个比这更生动的美的概念,当这些冷静的长老们也承 认她的美是值得这—场流了这许多血,洒了那么多泪的战争的呢? 015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凡是荷马不能按照着各部分来描绘的,他让我们在它的影响里来认识。诗 人呀,画出那“美”所激起的满意、倾倒、爱、喜悦,你就把美自身画出来 了。谁能构想莎茀所爱的那个对方是丑陋的,当莎茀承认她瞥见他时丧魂失 魄。谁不相信是看到了美的完满的形体,当他对于这个形体所激起的情感产生 了同情。 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把“美”转化做魅惑 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因此它对于画家不像对于诗人那么便当。 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因此在它那里魅惑力会 变成了做鬼脸。但是在文学里魅惑力是魅惑力,它是流动的美,它来来去去, 我们盼望能再度地看到它。又因为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 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 的作用要更强烈些。 甚至于安拉克耐翁(希腊抒情诗人),宁愿无礼貌地请画家无所作为,假 使他不拿魅惑力来赋予他的女郎的画像,使她生动。“在她的香腮上一个酒窝, 绕着她的玉颈一切的爱娇浮荡着”(《颂歌》第二十八)。他命令艺术家让无限 的爱娇环绕着她的温柔的腮,云石般的颈项!照这话的严格的字义,这怎样办 呢?这是绘画所不能做到的。画家能够给予腮巴最艳丽的肉色;但此外他就不 能再有所作为了。这美丽颈项的转折,肌肉的波动,那俊俏酒窝因之时隐时 现,这类真正的魅惑力是超出了画家能描绘。他感觉到把这些要素相继地列数出来,不可能获得像它并列时那种效果,我们 若想根据这相继地一一指说出来的要素而向它们立刻凝视,是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统一 的协调的图画的。要想构想这张嘴和这个鼻子和这双眼睛集在一起时会有怎样一个效 果是超越了人的想象力的,除非人们能从自然里或艺术里回忆到这些部分组成的一个 类似的结构(白华按:读“巧笑倩兮”……时不用做此笨事,不用设想是中国或西方 美人而情态如见,诗意具足,画意也具足)。 在这里,荷马常常是模范中的模范。他只说,尼惹斯是美的,阿奚里更 美,海伦具有神仙似的美。但他从不陷落到这些美的周密的啰唆的描述。他的 全诗可以说是建筑在海伦的美上面的,一个近代的诗人将要怎样冗长地来叙说 这美呀! 但是如果人们从诗里面把一切身体美的画面去掉,诗不会损失过多少?谁 要把这个从诗里去掉?当人们不愿意它追随一个姊妹艺术的脚步来达到这些画 面时,难道就关闭了一切别的道路了吗?正是这位荷马,他这样故意避免一切 片断地描绘身体美的,以至于我们在翻阅时很不容易地有一次获悉海伦具有雪 白的臂膀和金色的头发,(《伊利亚特》Ⅳ,第319 行)正是这位诗人他仍然懂 得使我们对她的美获得一个概念,而这一美的概念是远远超过了艺术在这企图 中所能达到的。人们试回忆诗中那一段,当海伦到特罗亚人民的长老集会面前, 那些尊贵的长老们瞥见她时,一个对一个耳边说: “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阿开人,为了这个女人这么久忍受着苦难呢, 看来她活像一个青春常驻的女神。” 还有什么能给我们一个比这更生动的美的概念,当这些冷静的长老们也承 认她的美是值得这—场流了这许多血,洒了那么多泪的战争的呢? 015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凡是荷马不能按照着各部分来描绘的,他让我们在它的影响里来认识。诗 人呀,画出那“美”所激起的满意、倾倒、爱、喜悦,你就把美自身画出来 了。谁能构想莎茀所爱的那个对方是丑陋的,当莎茀承认她瞥见他时丧魂失 魄。谁不相信是看到了美的完满的形体,当他对于这个形体所激起的情感产生 了同情。 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把“美”转化做魅惑 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因此它对于画家不像对于诗人那么便当。 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因此在它那里魅惑力会 变成了做鬼脸。但是在文学里魅惑力是魅惑力,它是流动的美,它来来去去, 我们盼望能再度地看到它。又因为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 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 的作用要更强烈些。 甚至于安拉克耐翁(希腊抒情诗人),宁愿无礼貌地请画家无所作为,假 使他不拿魅惑力来赋予他的女郎的画像,使她生动。“在她的香腮上一个酒窝, 绕着她的玉颈一切的爱娇浮荡着”(《颂歌》第二十八)。他命令艺术家让无限 的爱娇环绕着她的温柔的腮,云石般的颈项!照这话的严格的字义,这怎样办 呢?这是绘画所不能做到的。画家能够给予腮巴最艳丽的肉色;但此外他就不 能再有所作为了。这美丽颈项的转折,肌肉的波动,那俊俏酒窝因之时隐时 现,这类真正的魅惑力是超出了画家能力的范围了。诗人(指安拉克耐翁)是 说出了他的艺术是怎样才能够把“美”对我们来形象化感性化的最高点,以便 让画家能在他的艺术里寻找这个最高的表现。 这是对我以前所阐述的话一个新的例证,这就是说,诗人即使在谈论到艺 术作品时,仍然是不受束缚于把他的描写保守在艺术的限制以内的(白华按: 这话是指诗人要求画家能打破画的艺术的限制,表出诗的境界来,但照莱辛的 看法,这界限仍是存在的)。 莱辛对诗(文学)和画(造型艺术)的深入的分析,指出它们的各自的局 限性,各自的特殊的表现规律,开创了对于艺术形式的研究。 016 美学的境界 诗中有画,而不全是画,画中有诗,而不全是诗。诗画各有表现的可能性 范围,一般地说来,这是正确的。 但中国古代抒情诗里有不少是纯粹的写景,描绘一个客观境界,不写出主 体的行动,甚至于不直接说出主观的情感,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 “无我之境”,但却充满了诗的气氛和情调。我随便拈一个例证并稍加分析。 唐朝诗人王昌龄一首题为《初日》的诗云: 初日净金闺, 先照床前暖; 斜光入罗幕, 稍稍亲丝管; 云发不能梳, 杨花更吹满。 这诗里的境界很像一幅近代印象派大师的画,画里现出一座晨光射入的香 闺,日光在这幅画里是活跃的主角,它从窗门跳进来,跑到闺女的床前,散发着 一股温暖,接着穿进了罗帐,轻轻抚摩一下榻上的乐器—闺女所吹弄的琴瑟箫 笙—枕上的如云的美发还散开着,杨花随着晨风春日偷进了闺房,亲昵地躲上 那枕边的美发上。诗里并没有直接描绘这金闺少女(除非云发二字暗示着),然而 一切的美是归于这看不见的少女的。这是多么艳丽的一幅油画呀! 王昌龄这首诗,使我想起德国近代大画家门采尔的一幅油画(门采尔的素描 1956 年曾在北京展览过),那画上也是灿烂的晨光从窗门撞进了一间卧室,乳白的 光辉浸漫在长垂的纱幕上,随着落上地板,又返跳进入穿衣镜,又从镜里跳出来, 抚摸着椅背,我们感到晨风清凉,朝日温煦。室里的主人是在画面上看不见的, 她可能是在屋角的床上坐着。(这晨风沁人,怎能还睡?) 太阳的光, 洗着她早起的灵魂, 017 第一章 美学的意蕴 天边的月, 犹似她昨夜的残梦。 —《流云小诗》 门采尔这幅画全是诗,也全是画;王昌龄那首诗全是画,也全是诗。诗和 画里都是演着光的独幕剧,歌唱着光的抒情曲,这诗和画的统一不是和莱辛所 辛苦分析的诗画分界相抵触吗? 我觉得不是抵触而是补充了它,扩张了它们相互的蕴涵。画里本可以有 诗(苏东坡语),但是若把画里每一根线条,每一块色彩,每一条光,每一个 形都饱吸着浓情蜜意,它就成为画家的抒情作品,像伦勃朗的油画,中国元 人的山水。 诗也可以完全写景,写“无我之境”。而每句每字却反映出自己对物的抚 摩,和物的对话,表出对物的热爱,像王昌龄的《初日》那样,那纯粹的景就 成了纯粹的情,就是诗。 但画和诗仍是有区别的。诗里所咏的光的先后活跃,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 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 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而诗像《初日》里虽然境界华美,却赶不上门采尔油画 上那样光彩耀目,直射眼帘。然而由于力的范围了。诗人(指安拉克耐翁)是 说出了他的艺术是怎样才能够把“美”对我们来形象化感性化的最高点,以便 让画家能在他的艺术里寻找这个最高的表现。 这是对我以前所阐述的话一个新的例证,这就是说,诗人即使在谈论到艺 术作品时,仍然是不受束缚于把他的描写保守在艺术的限制以内的(白华按: 这话是指诗人要求画家能打破画的艺术的限制,表出诗的境界来,但照莱辛的 看法,这界限仍是存在的)。 莱辛对诗(文学)和画(造型艺术)的深入的分析,指出它们的各自的局 限性,各自的特殊的表现规律,开创了对于艺术形式的研究。 016 美学的境界 诗中有画,而不全是画,画中有诗,而不全是诗。诗画各有表现的可能性 范围,一般地说来,这是正确的。 但中国古代抒情诗里有不少是纯粹的写景,描绘一个客观境界,不写出主 体的行动,甚至于不直接说出主观的情感,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 “无我之境”,但却充满了诗的气氛和情调。我随便拈一个例证并稍加分析。 唐朝诗人王昌龄一首题为《初日》的诗云: 初日净金闺, 先照床前暖; 斜光入罗幕, 稍稍亲丝管; 云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