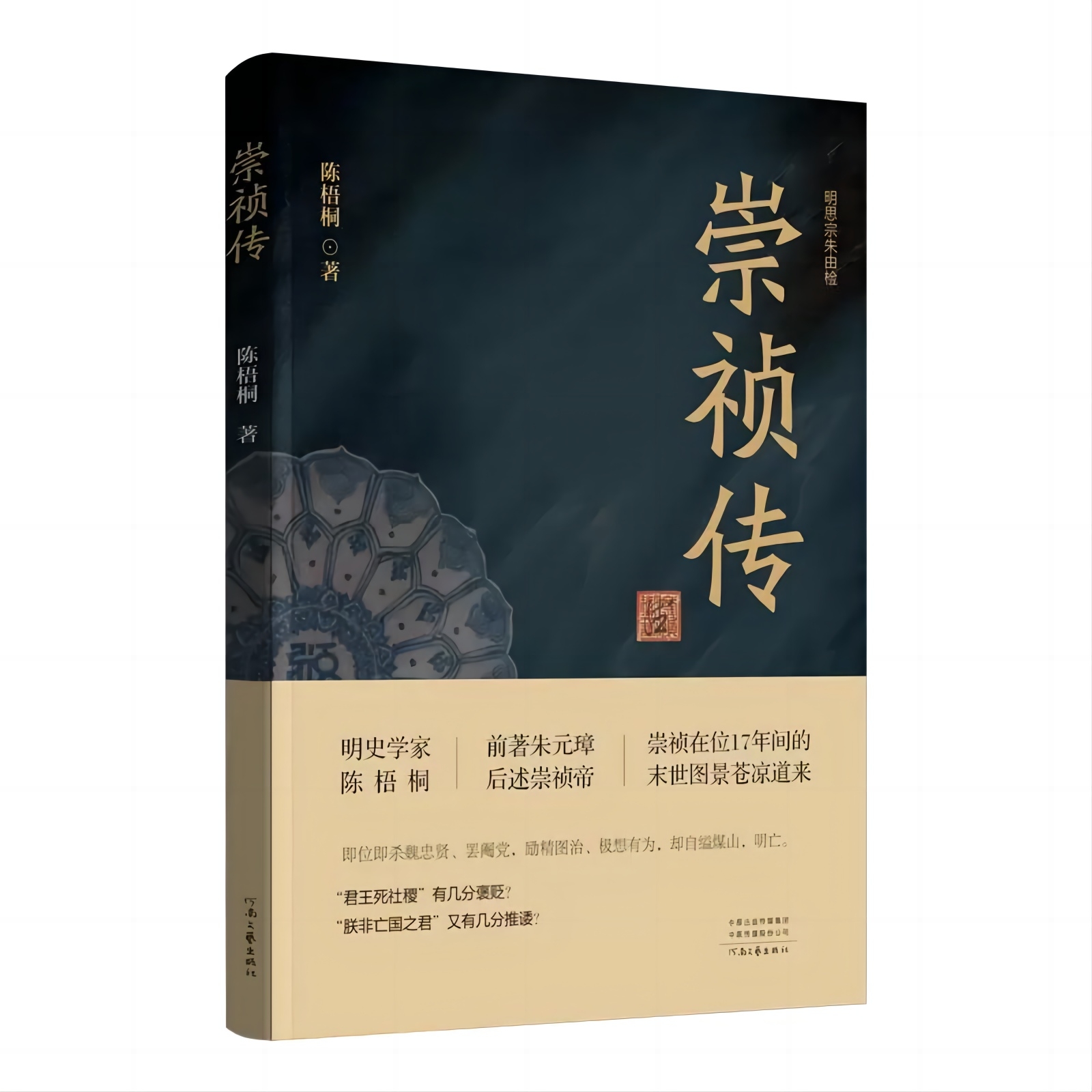
出版社: 河南文艺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崇祯传
ISBN: 9787555914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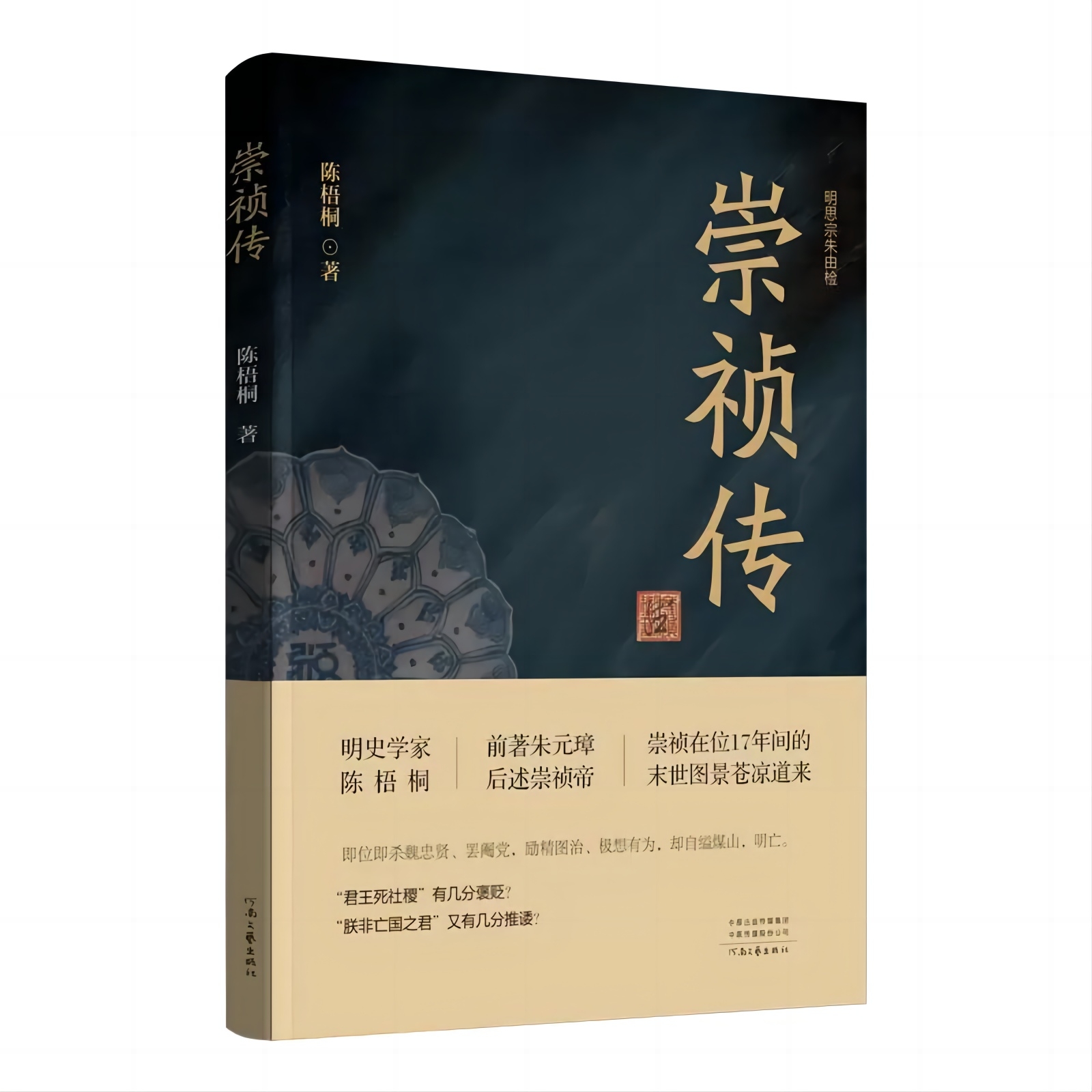
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202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儿国学》主编、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朱元璋传》、《朱元璋大传》、《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朱由检,因年号崇祯,人们也习称他为崇祯皇帝。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在皇寿亭畔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宣告了明王朝统治的终结。 统治长达 277 年的明王朝,最后葬送在明思宗手里,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明思宗自己却不这样看。 崇祯八年(1635),当凤阳的明皇陵遭到农民起义军放火焚烧之后,他发布了罪己诏,在“罪己”的同时,就指责文武大臣“夸诈得人,实功罕觏”,似乎明王朝面临的深刻危机,都是由“诸臣失算”造成的。 到崇祯十七年二月,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大肆谴责臣僚,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到了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在煤山自缢之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 作为明思宗的劲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二月率部横扫山西,发布檄文也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 明思宗死后,对他的评价便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既有斥责者,也有同情者,更有赞颂者,令人莫衷一是。 清康熙帝为修明史,曾对明史馆诸臣发表对明史的看法,谓:“当洪、永开国之际,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传诸累叶,虽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 又十六朝之内宫禁毖严,而女主不闻预政,朝纲独御,而权奸不敢上侵。 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 惟是晚近诸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不能接对群臣,巡省风俗,以致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 迨末季朋党滋繁,一时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国是淆乱,盗贼恣猖,役重赋烦,边腹交困,而明祚驯至衰危矣。”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明代诸帝的是非功过,既充分地肯定明初太祖、成祖“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的历史功绩,也无情地揭露晚明诸帝“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特别是末季崇祯帝“国是淆乱” “役重赋烦”而致明祚衰危的弊政。 清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在《庄烈帝纪》之后的赞语中,对明思宗做出这样的评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 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 兵荒四告,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这则代表清代官方的评论,褒多于贬,极力赞扬明思宗的“慨然有为”“不迩声色,忧勤惕励”,至于“祚讫运移,身罹祸变”,那不过是“气数使然”罢了。 明末的忧时之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评价明思宗说:“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 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 而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批评明思宗“太阿独操”,也就是独断专行,认为明王朝之亡就亡在他的独断专行。 清初浙江海宁人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评述明思宗一生的功过是非说:“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 此心诚可享上帝。 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 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 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 曰吾自不旁落,己旁落矣。 以饥益盗,以加派益饥,以缮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缮兵,久之兵皆盗也。 盟诸中者,不与众喻,有恝视耳。 帝信王时尝阅《三国志》,见十常侍及董卓、曹瞒矫制擅权,未尝不抚掌切齿。 已闻立枷之刑,颇为动色,乃逡巡似失初指,则事势流激之,不期其然也。 虽然,不屈者人臣之节,而天子先之。 为南面持大防,义矫百代,是故愿从者众。 为北面昭大节,亦矫百代。”赞扬明思宗勇于求治、寡欲崇俭、关心民瘼,最后以身殉国,是个“矫百代”的壮举。 同时批评他少推诚,稍舞智,疏远大臣而信任宦官,最后导致王朝的覆灭。清初直隶丰润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评论明思宗说:“怀宗之图治,与其所以致乱,揆之事实,盖亦各不相掩焉。 方其大东罢贡,便殿停香,记法重珥笔之臣,寒暑御文华之讲,进监司而问民疾苦,重宰执而尊礼宾师,以至素服论囚,蠲逋珥乱,罪己则辍减音乐,赈饥则屡发帑金,于是爱民勤政,发奸摘伏,此则怀宗之图治也。 及其御寇警则军兴费烦,急征徭则闾阎告病,以至破资格而官方愈乱,禁苞苴而文网愈密,恶私交而下滋告讦,尚名实而吏多苛察,于凡举措听荧,贞邪淆混,此则怀宗之致乱也。”认为明思宗的为政,其致治的绩效与致乱的祸患都极显著,互不相掩。 曾协助谷应泰编修《明史纪事本末》的文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明思宗的功过逐一进行评述,最后以同情的笔触写道:“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 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殒身。 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为愈也。”还说:“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 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褒扬多于谴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惋惜之情。 清乾隆年间驰誉文坛的全祖望,在《明庄烈帝论》中则针对明思宗自谓非亡国君的言论,评论说:“庄烈自言非亡国之君……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 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凡庄烈之召祸,在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在外吝于议和。”他认为放任宦官干政、拒绝与清议和,是导致明思宗亡国的两个关键问题。 对明思宗评价的这种意见分歧,在史学界长期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家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仍对其表示同情,甚至为之开脱、辩解,赞同其为“非亡国之君”说。 近年就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明思宗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那么,明思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上述的诸多评论究竟哪一种符合历史实际呢? 这部《崇祯十讲》,择取明思宗生平活动的十个专题,以点带面地概述其一生的重大活动及其对历史演进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对其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来回答读者的疑问。 陈梧桐先生治学严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有独到的创新之见的论著,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应关注本学科同行和相邻学科的研究状况与学术成果,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 陈梧桐先生对明史信手拈来,对传记写作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历史人物的写作,不能仅限于记述传主个人的活动,还应写出当时的时代风貌与诉求,是推动还是阻滞历史车轮的前进,对其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