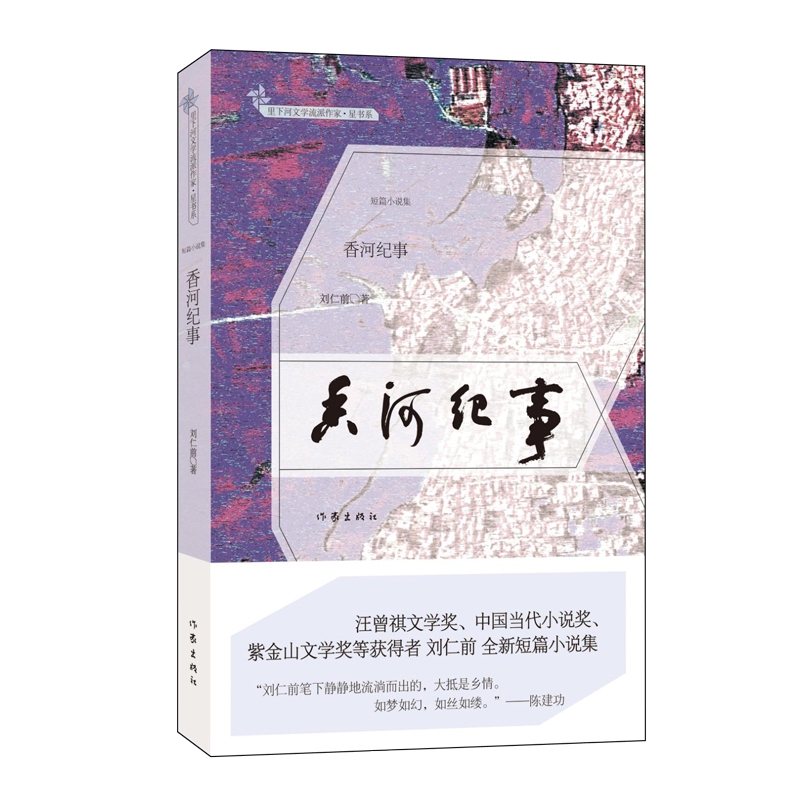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5.00
折扣购买: 香河纪事/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
ISBN: 9787521206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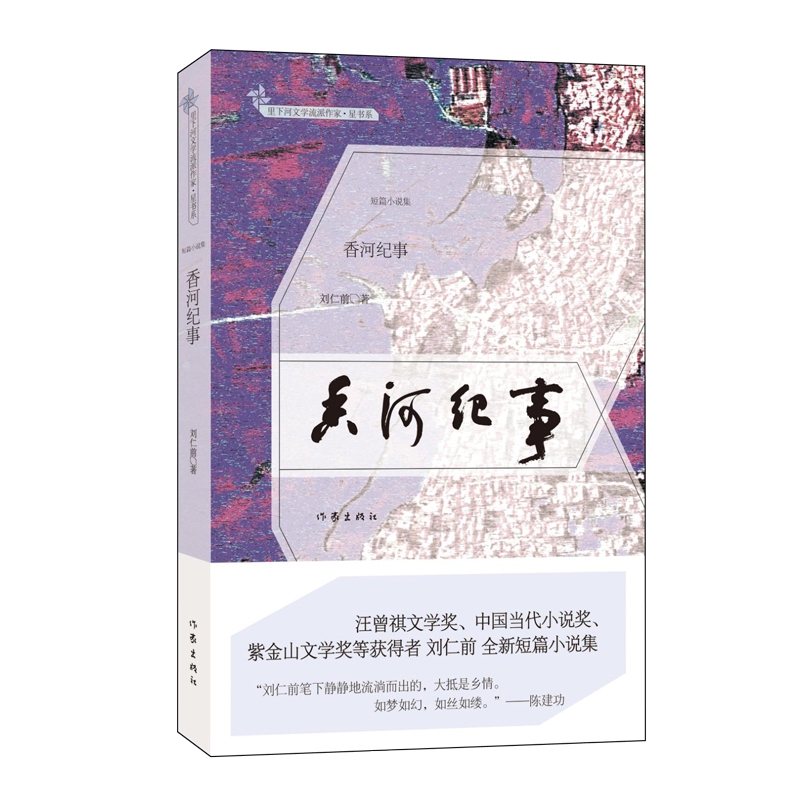
刘仁前,笔名瓜棚主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泰州市文艺界联合会**。1961年11月出生。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中国青年》全国小说**作征文奖、汪曾祺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中国散文年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安徽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中短篇小说集《谎媒》,散文集《瓜棚漫笔》《楚水风物》《那时,月夜如昼》《爱上远方》等多部,主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多卷,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民抗”司令——任天石烈士传》《丹心如虹——谭寿林烈士传》。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小说家代表作集》《中华文学选刊》等多种选本。长篇小说《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里下河版的《边城》”,2017年6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
喊 工 天刚麻花亮,阿根伙的叫喊声,便在龙巷上空响起: 各家各户起*啰——起*烧早饭噢—— 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用在阿根伙身上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喊”。细个子的阿根伙,嗓音甚是洪亮,极易让人想起夏*枝头的鸣蝉。说来奇怪,蝉儿那短小的身体,发出的声音真是响亮。眼下,刚开春,离听蝉鸣尚早。 香河,地处里下河苏北平原,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这早春时节,柳吐嫩绿,桃发新蕊,香河水流泛亮,村舍裹在薄纱般的**里,淡成一幅江南水墨。此时,行走在苏北平原上,可谓一麦碧千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碧绿的麦田,在春风里高低起伏着,碧波**着,让人有如置身于浪涛翻滚的大海。 香河一带,则稍有不同。此时的田野上,除了大片的绿,还有大片的黄。大片的绿,是碧绿的麦田;大片的黄,则是黄灿灿的油菜花,摇曳在春风里,甚是妖娆。不是说,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么?复苏的岂止是“物”,还有“人”。被**包裹着的香河的男男女女,亦随着春天的脚步,从隆冬里苏醒过来。 各家各户起*啰——起*烧早饭噢—— 随着阿根伙的叫喊,男人们这才窸窸窣窣地离开自己婆娘的热被头。这**中,搂在怀里的,果真都是自己的婆娘么?未必。 香河的**,从喊工开始。 各家各户起*啰——,起*烧早饭噢—— 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用对喊人起*、喊人起*烧早饭这样的事情,感到奇怪。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烧早饭。这,应属“大集体”年代之独创。 过不了多会子,各家各户的门,鸣着鸟语,吱吱呀呀地打开。阿根伙便忙着与“烂熟藕”一般熟识的村民们点头,打招呼,派工。他这时段的工作不再是“喊”,区别不同情形,有的需“登堂入室”,跟一家之主交代几句。也有的“登堂入室”之后,没了下文。 此时的巷子上,便有虚掩着怀,蓬松着发髻,挟着淘米箩,捏着牙刷、毛巾的大姑娘、小媳妇,三三两两往水桩码头去。 阿根伙见着,眼馋,手痒。眼馋,便肆无忌惮往女人脖颈子里钻。手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这个胸脯上抓一把,在那个脸蛋上捏一下。被追打,被唾骂,是他极乐意得到的回报。 垂柳掩映着的水桩码头上,那些女人,淘了米,漱了嘴,洗了脸,说了一会子家长里短的闲话,之后鸟雀一般叽叽喳喳地散开。 很快,各家各户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家前屋后,*鸣犬吠。沉寂了**的村庄,愈发热闹起来。 叫人家起*,叫人家起*烧早饭,有个正正规规的名称:喊工。 喊工,颇辛苦,得早起。一年四季,春秋天,气候宜人,早起就早起,尚不费难。寒冬腊月,炎炎夏*,气候不如春秋季温驯,鹅毛大雪说来就来,刮风下雨,亦无定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喊工,显然是要吃点辛苦的。 间或,也会有费口舌的事情发生。一般寻常人家,起*,烧早饭,吃早饭,按时上工,没问题。家中若有没断奶的婴儿,喂奶,则是年轻母亲上工前必须做的,自然会耽搁工夫。家中有新人的,那新婚的小两口,正是恋*的阶段,不被催得“屎急扒塘”,舍不得起*。想要小两口按时出门,难。 喊人起*,喊人起*烧早饭,只是喊工之前奏。隔不了多会子,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村头巷口响起来,只是喊的内容变了。听—— 上工啰——各家各户快上工啰—— 从喊人起*到催人上工,中间隔多长时间?一顿早饭的工夫。 喊村民们“上工”,才是喊工目的之所在。这样的工作,是有专人负责的,不是哪个想喊就能喊的。喊工,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与派工、计工,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 生产队长便是这一权力运行链条中的执行官。称生产队长为“执行官”,似有“五八”语风。照中国吏制,“七品”才有“芝麻官”之称谓。这农村大队中的生产队长,似只能称“芝麻粉”。然,县官不如现管。“芝麻粉”阿根伙们,还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看似辛苦的喊工上,慢慢生出些甜头来,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甜头。 细个子阿根伙,脚头快,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他的管辖区为龙巷东头的一队,即:**生产队。香河大队,共七个生产队,自然有七个生产队长。每个生产队长,只管自己生产队的几十户百十口子人。 阿根伙获得“芝麻粉”称谓时间不长,之前一队被称之为“芝麻粉”的,叫祥大少。那时的阿根伙,只是个“助喊”。真正行使“喊工”责权的,是一队之长祥大少。 祥大少喊工的做派,与阿根伙**两样。身高马大的祥大少,有一副大脚板,早*头走在空荡荡的龙巷上,啪哒啪哒,空声响,不知情的,还以为村子里进了怪兽,有点儿吓人。好在,紧跟着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祥大少的喊声便响起来了—— 各家各户起*啰——起*烧早饭噢—— 虽然,祥大少喊的,与阿根伙喊的,字面上并无差异。但,听起来相差就大了。前面介绍了,阿根伙的嗓子洪亮,准确点儿讲,“洪亮”一词用在阿根伙身上,不是并联,是偏正,主要是“亮”。这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不无关系。 不止于此,他能在那帮女人面前肆无忌惮地“眼馋”“手痒”,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亦不无关系。阿根伙的小淮调从哪儿学会的?没人去细究过。好在阿根伙不拿大,对妇女们可谓是有求必应。每回,他几乎都是从具有红色基因的“贫农、下中农”开唱,引出“带彩”的小僧尼之后,让自己的小淮调达到**。 与阿根伙的“亮”嗓不同,祥大少的嗓子,用得上一个词:粗犷。如若要细细追究的话,祥大少的嗓音特点重在“粗”字上。不止于此,听惯了祥大少喊工的,还能听出他与阿根伙语句间隙的差别。与阿根伙亮嗓一句完整地喊出口不同,祥大少在“各家各户”与“起*啰——”之间,似有停顿,而第二句“起*烧早饭噢——”则紧跟着,听上去命令的意味要浓些,强势、霸气。阿根伙,有时会学前任的喊法,终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喊声“霸气”的时候,少。 全村人都知道,“芝麻粉”祥大少有“三好”:玩牌、听戏、打老婆。 祥大少的老婆,在整个香河的婆娘当中,都够得上一个词:标致。白果子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会说话,撩人。匀称的身子,前挺后翘,让村上男人见了眼痒、手痒、心痒。尤其像蔡和尚、瘌扣伙这些光棍汉,当然也包括阿根伙,三十出头了,依然是光棍一条。他们这些男人,在如此标致的女人面前,口水早就不知淌出多少个三尺长了。只是吃惧祥大少,身高马大的,又是一队之长,惹不起。果真不识相,只能是找死。 于是乎,这帮光棍堂儿单身汉,手痒?自己往墙角上掼。心痒?只能夜里钻进被窝**。**能做的,也只有解解眼馋。这些男人,见着祥大少家哑巴婆娘,一个个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变成了带彩的狼,两只眼放着绿光,真恨不能眼光里长出手来。 就是这样一个令多少男人垂涎的婆娘,祥大少对她通常的礼遇却是一个字:打。 与村上其他男人打女人不同,祥大少很少将自己老婆关在家里打。祥大少打老婆颇具形式感,拽着他老婆长长的黑发,在龙巷上拖,一拖几个来回。只听到那婆娘哇哇哇叫,听不见回嘴。 如此标致的女人,是个哑巴,且不能生孩子,怪可惜的。这也让祥大少打老婆,变得十分理直气壮。 祥大少打老婆打累了,严谨说来,应该是拖累了,便会从怀里掏出那台随身带着的半旧不新的半导体,听戏。 祥大少所谓“听戏”,便是听革命现代京剧选段。什么《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什么《提篮小卖》之类。想听别的,门儿都没有。 有时候也听《浑身是胆雄赳赳》。过分了不是,一个如此标致的哑巴女人,被你个大男人折腾来折腾去,*后只能眼泪汪汪地回家,给你做饭。你还《浑身是胆雄赳赳》了?背地里,也有看不过去的,指着祥大少脊梁骨叽咕几句。 这样的叽咕,有如春天田野上的微风,给祥大少挠痒痒呢,没任何***,祥大少根本不会理睬。那几年,他正“红”在势头上,哪个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替哑巴女人鸣不平。尽管大伙儿都知道,这标致的哑巴,怪可怜的。 其实,后来祥大少常年听的,多为淮戏。香河一带,原本就有听淮戏的传统,只不过中间有几年大搞“破四旧”,阵势搞得蛮大的,老淮戏都给破掉了。上了年岁的,只能在自家灶台后面哼哼,不足为外人道也。要不然,像阿根伙,哪能唱得一口小淮调? 等到祥大少的半导体里有了什么《打金枝》,什么《牙痕记》,什么《铡美案》之类,已经是以后的事情。祥大少的运势反而差了。 听革命现代京剧的那会子,祥大少“芝麻粉”当得正带劲。在大队部开会时,面对香元支书,自己表态发言也好,接*香元指派的任务也罢,高门粗嗓,劲爆得很,从不拖泥带水,从不口出软语。 同样劲爆的,还有他裤裆里的小老二,雄赳赳气昂昂的,俨然一介武士。每天夜里,在哑巴婆娘身上,折腾来,折腾去,不到精疲力竭,不来个一泻千里,断不收兵。白天嘴上再劲爆,夜里躺在*上,总会想着自家的香火,如若在自己手上断了,自己*了后不谈,还要落顶“大不孝”的帽子,那不是要挨全村人耻笑?*对不起自家的列祖列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旧礼,老辈人传下来的,祥大少懂。 细皮嫩肉的哑巴婆娘,身上那地方,恨不能掐得出水来,可就是不争气,让祥大少的好雨总是落在荒祥大少再不死心,也没办法。心里头郁闷。 祥大少的郁闷,被阿根伙看在眼里,便撮哄他到谭驼子家玩牌。其时,在村民眼里,阿根伙就是祥大少的跟屁虫,*主要的工作便是“助喊”: 各家各户起*啰——起*烧早饭噢—— 阿根伙跟在祥大少后头,偶或也能过过“芝麻粉”的瘾,那感觉,蛮不错的。阿根伙打定主意跟定祥大少,自然想着法子讨好祥大少。 在谭驼子家玩牌的,原本是瘌扣伙、蔡和尚几个单身汉,私下悄悄玩的,属“小来来”的那种。虽说有点儿小赌资,但说不上赌。隔一阵子,几个男人嘴里淡出鸟来,想喝酒了,便约好到谭驼子家玩一下,弄瓶大麦烧,煮碗细鱼儿,便热嘈起来。有时也会到柳安然老先生家的豆*坊拾几方豆*,让香玉做个汪豆*,抑或麻辣豆*之类。这几个男人,实际就是借玩牌,吃个“碰头”。当然,也有赌运气的意思,毕竟是输牌的掏腰包。比起各人直接掏份子,有副牌在手上玩起来,还是多了些乐趣。 开春不比四夏大忙,农活不重,主要是田间管理。男人们也就是到田里,做些清沟理墒之类的农活,身子闲着呢。不是说闲则生非么?非分之想倒不是没有,有的想得到,有的想也白想。譬如祥大少家哑巴婆娘,祥大少不当回事,要是摆在瘌扣伙他们几个屋里,哪个不把哑巴婆娘当菩萨一样供着! 既然想也是白想,那就甭做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梦。几个光棍汉,从男人们惯常放在心头盘算的几个字中,挑了一个跟“赌”相近的,玩牌。“小来来”,之后吃“碰头”,喝点儿小酒。这就让原本清汤寡水的*子,生出些滋味来。 玩牌地点放在谭驼子家,主要是便利。谭驼子是个远近有名的“摸鱼鬼子”,家里几乎不脱鱼。当然,这鱼得花钱。钱,出在牌桌上。*为便利的,谭驼子家婆娘香玉,做得一手好菜。只要香玉往锅灶前一站,总能给你烧出几样菜来,蛮吊人胃口的。 其实,吊人胃口的,不只是香玉烧菜的厨艺。这几个男人,哪个不是吃腥的猫?吃惧祥大少,再标致的哑巴婆娘也不敢碰。在贪小的谭驼子那里却找到了缝隙。 在*常之中,他们几个,多多少少都从香玉身上得到过甜头:嘴头上快活快活,说些色彩偏黄的话;手上这块抓一把,那块捏一把,不在少数。香玉有个好处,一般婆娘比不了。香玉开得起玩笑,不怕你揩油。阿根伙就摸过香玉的**,香玉不仅没生气,还友情提醒,别让她家谭驼子知道。虽说隔着夹布褂子,但阿根伙摸上去,香玉的**子,肉乎乎,软绵绵,还是蛮有感觉的。 祥大少到谭驼子家玩牌,只玩“寸符儿”。一玩,就上了瘾。 “刘仁前笔下静静地流淌而出的,大抵是乡情。如梦如幻,如丝如缕。”——陈建功 香河, 蜿蜒流淌于苏北水乡的地理之河; 《香河纪事》, 满溢人性与风物之美的文字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