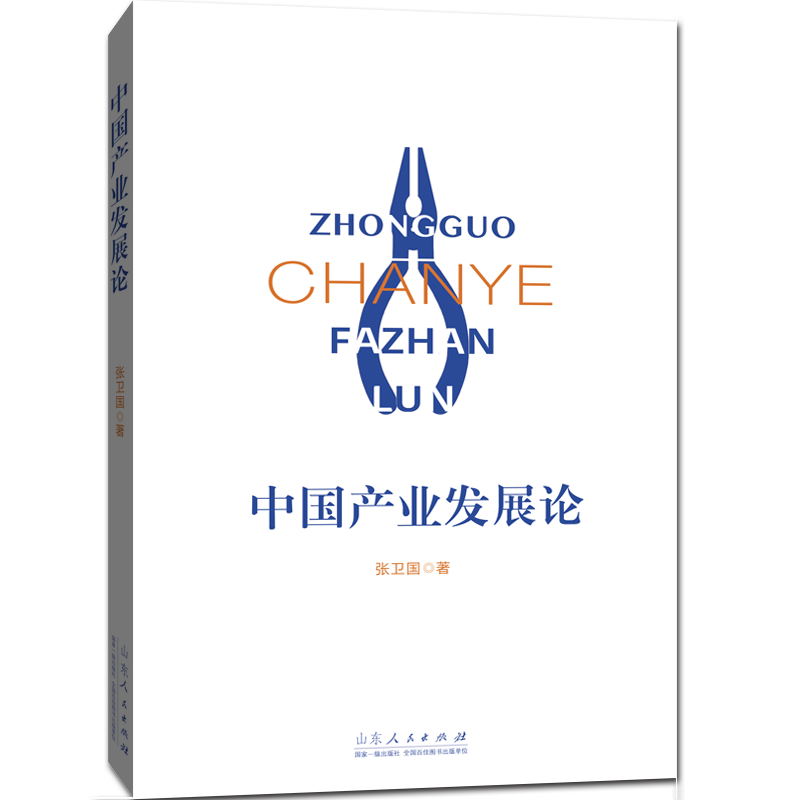
出版社: 山东人民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9.70
折扣购买: 中国产业发展论
ISBN: 9787209135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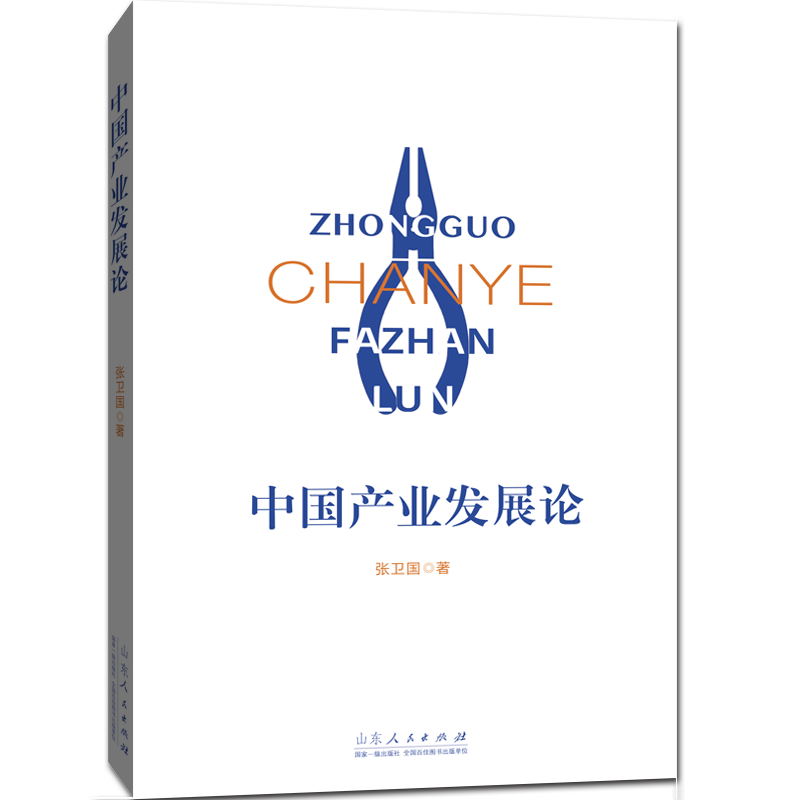
张卫国,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第一章 导 论 产业发展是包括产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空间集聚、产业组织创新、产业政策优化等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历史变化过程。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生产力并侧重生产关系或者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中阐释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而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上分析产业发展,具体又如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平衡发展的分析。古典经济学派集大成者亚当?斯密(Smith,Adam)、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Alfred)、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 A)、让?梯若尔(Tirol Jean)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分别从专业化分工与国民财富创造、垄断竞争与市场均衡、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与资源有效配置、博弈论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等角度,丰富了产业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实验经济学通过在受控环境中运用试验方法验证和发展理论,分别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进行了新的尝试。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理论经历了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作指导,借鉴苏联部门经济学理论,到引进学习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再到正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演进过程。 产业发展理论应当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产业发展政策应当构成经济治理的主要依据。反之,经济理论奠定了产业发展理论的基础,经济治理绩效决定了产业发展政策运用的绩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对产业发展理论的相关阐释建立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价值观之上,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但马克思本人当时没有专门研究产业发展理论,受时代所限也不可能对当代产业发展问题进行阐释。包括当代西方产业发展各种流派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受限于与现实很不相符合的建立在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的基本思路,其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越来越受到包括主流经济学一流学者本身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诟病。演化经济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理查德?R.纳尔逊(Nelson,Richard R.)和悉尼?G.温特(Winter,Sidney G.)在他们所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就指出:“完全拘泥于最大化和均衡分析,在为经济调整建立现实模型的道路上设置了主要障碍。” 这就是如斯蒂夫?吉恩(Keen,Steve)所说的“为什么世界上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是最后才意识到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正在迫近” 的原因。 非主流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 “面临的困难是,发明与演化一致的分析工具”,“现在仍处于婴儿时期” 。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各位知名宏观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来临,从一个方面说明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包括产业发展政策运用绩效在内的整个经济治理绩效的不良。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多次国际金融危机都可以从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在内的经济治理的缺陷中找到原因。 以下分析表明,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过度虚拟化和泡沫化成为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时期大萧条和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产业发展道路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道路之争,值得引起人们对中国以及世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道路作深入思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大衰退。时至今日,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依然处于缓慢复苏之中。全球经济“新平庸”(new mediocre),即全球经济处于长周期下行阶段,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由危机前两位数高速增长到持续下滑,并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过程。据统计,2006—2010年中国 历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2.7%、14.2%、9.7%、9.4%、10.6%,年均增长11.3%;2011—2015年中国历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9.5%、7.9%、7.8%、7.3%、6.9%,年均增长7.9%。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和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4.2%、9.7%,后者比前者降低了4.5个百分点;2011—2015年GDP年均增长速度比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3.4个百分点。危机导致的巨大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引致包括中国社会各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政界、产业界、学术界对世界各经济体产业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产业和经济发展道路作出深刻反思;世界各经济体内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产业界、学术界则对本经济体内产业和经济发展道路有更多思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Schwab,Klaus),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就“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的“未来之路”指出:“我相信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效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应对甚至化解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Deaton,Angus)在他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极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则指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与此同时,大逃亡也创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世界: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Piketty,Thomas)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抑制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 。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元老级人物乔根?兰德斯(Randers,Jorgen)在罗马俱乐部权威研究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过程中,当前的升温导致未来更高的升温,形成一个无法停止的因果反馈循环。”“这一事实应该强有力地促使我们采取比现有的更多的行动。” 华盛顿智囊团——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Atkinson,Robert D.)在其《美国供给侧模式启示录:经济政策的破解之道》一书中,针对包括供给经济学和需求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十分有限甚至无效的问题明确指出:“要促进21世纪的经济发展,保守派的供给经济学以及自由派的需求经济学都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都想从过去寻求指导方向。要采取有效的增长战略,需要基于21世纪全球化以及知识型导向这一经济现实。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增长经济学,因为该理论强调,通过创新带动生产力增长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 2010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选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Smil,V.)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一书中指出:“现代经济应该具有非物质性,以及制造业在后工业时代无足轻重的说法,纯属是对基本现实的误读。”“如果没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制造业浪潮,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同样,制造业的稳步发展也是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领导者的关键。”“美国人的奢华和政策正在不断侵蚀它曾经的巨大优势,也让它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在他的《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一书中指出:“工业化强健筋骨,金融化积累脂肪。中国应更多地倾听‘工业党’的建言呼声,约束金融利益集团的胡言乱语,更加鼓励工业资本,节制金融资本,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将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化坚持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在《中国制造2025》一书中指出:“如果不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将经济增长的期望过度寄托于服务业是不现实的,寄希望于虚拟经济的激烈扩张则更是充满风险。”“金融业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合理限度内是具有真实增长意义的,其提供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超过一定的限度,金融业自我扩展和衍生膨胀,并推动实体经济的产品和资产过度金融化,将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成为吸纳社会资源的引力‘黑洞’,终将危及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济创新发展理论是产业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依据。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是“创造性破坏”。他借用生物学术语“产业突变”说明这一经济结构内部的革命性变化,并明确指出:“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是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行业组织僵硬模式中的竞争,“在迥然不同于教科书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 。熊彼特认为经济人行为是有限理性的:“那种说行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类假说,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变得足够接近于现实,如果人们能有时间去被迫懂得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以内,人们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论。……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对现实的接近性。” 熊彼特式竞争是动态竞争,他强调创新就是不断打破均衡,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 熊彼特式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创新或组合创新:“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威廉?鲍莫尔(Baumol,William J.)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一书中指出:“可以这样说,18世纪以来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可以归功于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据统计,中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16—2019年年均增长2.0%。 与此同时,2016—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7%。 另据报道,“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5.3%提升到59.5%,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全球131个经济体创新能力排名中升至第十四位,创新正在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事实充分证明,创新发展是中国作为典型大国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探讨中国建构智能制造主导的高效生态产业体系,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兴起,其突出特征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人口、经济总量、国土空间大国,也是具有五千余年中华文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且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经济治理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经济发展正确道路,遵循产业发展基本规律,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立足中国产业发展国情,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今后应当建构智能制造为主导,具有能够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机结合的最典型生态经济特征的高效生态产业体系,而这对于全球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治理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章 导 论 产业发展是包括产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空间集聚、产业组织创新、产业政策优化等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历史变化过程。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生产力并侧重生产关系或者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中阐释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而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上分析产业发展,具体又如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平衡发展的分析。古典经济学派集大成者亚当?斯密(Smith,Adam)、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Alfred)、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 A)、让?梯若尔(Tirol Jean)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分别从专业化分工与国民财富创造、垄断竞争与市场均衡、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与资源有效配置、博弈论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等角度,丰富了产业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实验经济学通过在受控环境中运用试验方法验证和发展理论,分别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进行了新的尝试。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理论经历了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作指导,借鉴苏联部门经济学理论,到引进学习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再到正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演进过程。 产业发展理论应当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产业发展政策应当构成经济治理的主要依据。反之,经济理论奠定了产业发展理论的基础,经济治理绩效决定了产业发展政策运用的绩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对产业发展理论的相关阐释建立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价值观之上,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但马克思本人当时没有专门研究产业发展理论,受时代所限也不可能对当代产业发展问题进行阐释。包括当代西方产业发展各种流派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受限于与现实很不相符合的建立在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的基本思路,其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越来越受到包括主流经济学一流学者本身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诟病。演化经济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理查德?R.纳尔逊(Nelson,Richard R.)和悉尼?G.温特(Winter,Sidney G.)在他们所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就指出:“完全拘泥于最大化和均衡分析,在为经济调整建立现实模型的道路上设置了主要障碍。” 这就是如斯蒂夫?吉恩(Keen,Steve)所说的“为什么世界上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是最后才意识到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正在迫近” 的原因。 非主流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 “面临的困难是,发明与演化一致的分析工具”,“现在仍处于婴儿时期” 。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各位知名宏观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来临,从一个方面说明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包括产业发展政策运用绩效在内的整个经济治理绩效的不良。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多次国际金融危机都可以从包括产业发展理论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在内的经济治理的缺陷中找到原因。 以下分析表明,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过度虚拟化和泡沫化成为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时期大萧条和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产业发展道路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道路之争,值得引起人们对中国以及世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道路作深入思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大衰退。时至今日,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依然处于缓慢复苏之中。全球经济“新平庸”(new mediocre),即全球经济处于长周期下行阶段,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由危机前两位数高速增长到持续下滑,并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过程。据统计,2006—2010年中国 历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2.7%、14.2%、9.7%、9.4%、10.6%,年均增长11.3%;2011—2015年中国历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9.5%、7.9%、7.8%、7.3%、6.9%,年均增长7.9%。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和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4.2%、9.7%,后者比前者降低了4.5个百分点;2011—2015年GDP年均增长速度比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3.4个百分点。危机导致的巨大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引致包括中国社会各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政界、产业界、学术界对世界各经济体产业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产业和经济发展道路作出深刻反思;世界各经济体内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产业界、学术界则对本经济体内产业和经济发展道路有更多思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Schwab,Klaus),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就“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的“未来之路”指出:“我相信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效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应对甚至化解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Deaton,Angus)在他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极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则指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与此同时,大逃亡也创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世界: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Piketty,Thomas)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抑制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 。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元老级人物乔根?兰德斯(Randers,Jorgen)在罗马俱乐部权威研究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过程中,当前的升温导致未来更高的升温,形成一个无法停止的因果反馈循环。”“这一事实应该强有力地促使我们采取比现有的更多的行动。” 华盛顿智囊团——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Atkinson,Robert D.)在其《美国供给侧模式启示录:经济政策的破解之道》一书中,针对包括供给经济学和需求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十分有限甚至无效的问题明确指出:“要促进21世纪的经济发展,保守派的供给经济学以及自由派的需求经济学都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都想从过去寻求指导方向。要采取有效的增长战略,需要基于21世纪全球化以及知识型导向这一经济现实。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增长经济学,因为该理论强调,通过创新带动生产力增长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 2010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选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Smil,V.)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一书中指出:“现代经济应该具有非物质性,以及制造业在后工业时代无足轻重的说法,纯属是对基本现实的误读。”“如果没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制造业浪潮,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同样,制造业的稳步发展也是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领导者的关键。”“美国人的奢华和政策正在不断侵蚀它曾经的巨大优势,也让它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在他的《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一书中指出:“工业化强健筋骨,金融化积累脂肪。中国应更多地倾听‘工业党’的建言呼声,约束金融利益集团的胡言乱语,更加鼓励工业资本,节制金融资本,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将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化坚持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在《中国制造2025》一书中指出:“如果不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将经济增长的期望过度寄托于服务业是不现实的,寄希望于虚拟经济的激烈扩张则更是充满风险。”“金融业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合理限度内是具有真实增长意义的,其提供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超过一定的限度,金融业自我扩展和衍生膨胀,并推动实体经济的产品和资产过度金融化,将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成为吸纳社会资源的引力‘黑洞’,终将危及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济创新发展理论是产业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依据。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是“创造性破坏”。他借用生物学术语“产业突变”说明这一经济结构内部的革命性变化,并明确指出:“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是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行业组织僵硬模式中的价格竞争,“在迥然不同于教科书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 。熊彼特认为经济人行为是有限理性的:“那种说行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类假说,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变得足够接近于现实,如果人们能有时间去被迫懂得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以内,人们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论。……在个围以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对现实的接近性。” 熊彼特式竞争是动态竞争,他强调创新就是不断打破均衡,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 熊彼特式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创新或组合创新:“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威廉?鲍莫尔(Baumol,William J.)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一书中指出:“可以这样说,18世纪以来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可以归功于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据统计,中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16—2019年年均增长2.0%。 与此同时,2016—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7%。 另据报道,“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5.3%提升到59.5%,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全球131个经济体创新能力排名中升至第十四位,创新正在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事实充分证明,创新发展是中国作为典型大国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探讨中国建构智能制造主导的高效生态产业体系,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兴起,其突出特征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人口、经济总量、国土空间大国,也是具有五千余年中华文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且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经济治理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经济发展正确道路,遵循产业发展基本规律,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立足中国产业发展国情,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今后应当建构智能制造为主导,具有能够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机结合的最典型生态经济特征的高效生态产业体系,而这对于全球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治理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