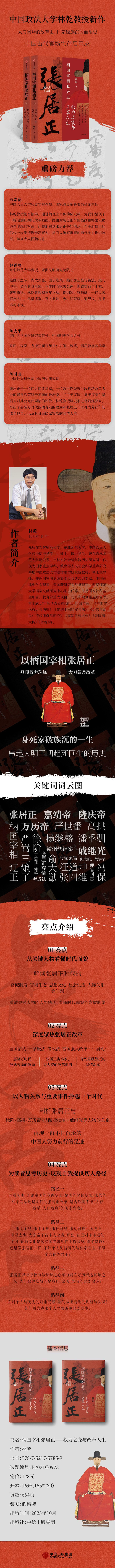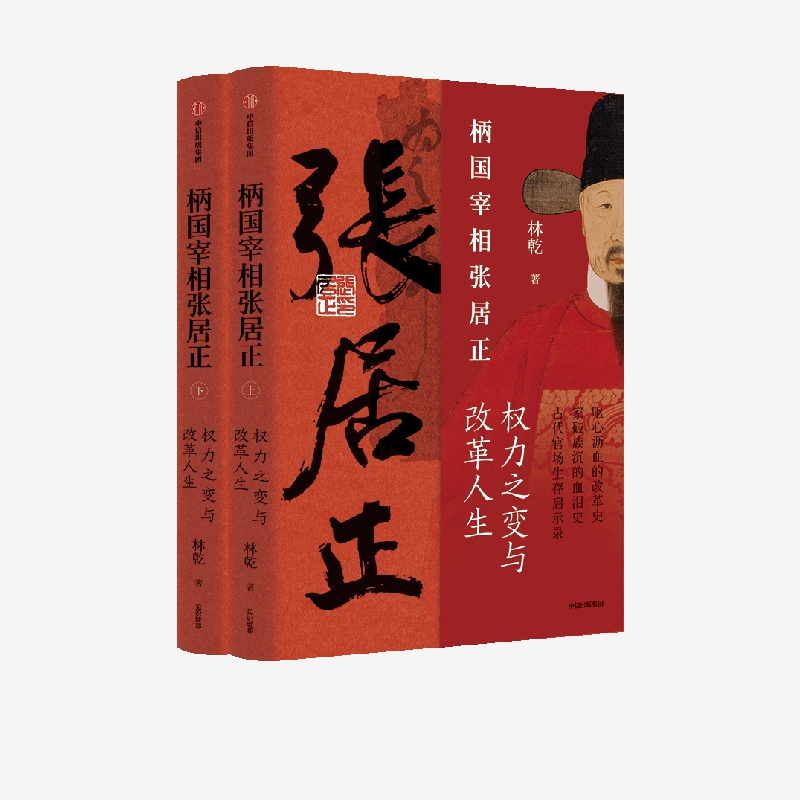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2.00
折扣购买: 柄国宰相张居正——权力之路与改革人生
ISBN: 9787521757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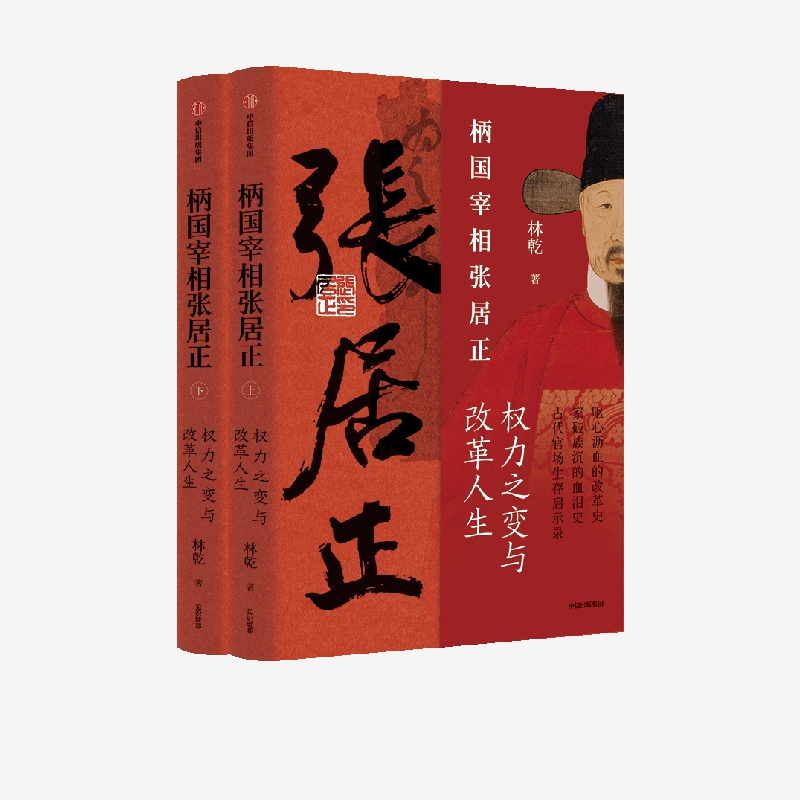
林乾,1959年生,先后在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华师范大学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曾于2017年任华为公司顾问,并在喜马拉雅讲述《雍正十三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北京市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权力与法律》《传统中国的权与法》《治官与治民:清代律例法研究》《嘉靖皇帝大传》《曾国藩大传》(合著)等。
第一章三位同年的人生抉择 一次特殊的临朝 传闻边马塞回中,候火甘泉极望同。 风雨雕戈秋入塞,云霄玉几昼还宫。 书生自抱终军愤,国士谁讥魏绛功。 北望苍然天一色,汉家高碣倚寒空。 匈奴万骑纵西山,天险谁当百二关。 今日安危任边将,异时恩泽满朝班。 乌边白骨那能辨,马首红妆若个还。 冗散书生空哽咽,截书谁为破愁颜。 这是时任刑部主事的王世贞,亲历庚戌之变后写下的两首纪事诗。 庚戌年是公元1550年,即明朝嘉靖二十九年,这是继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一百年后,大明王朝遇到的又一次大危机。对于嘉靖帝个人而言,是继八年前他被宫女谋害,死里逃生后,面临的又一次人生危机。 八月二十一日午刻,嘉靖帝在西苑便殿急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商议与俺答议和的事。此时俺答率军数万,列阵都城之外,其前锋兵马七百余骑,已于昨日进人安定门。俺答将日前虏获的太监杨增等人放回,让他们携带文书入城求贡,并向嘉靖帝下了“通牒”:如果当天得不到答复,就进兵攻城。 嘉靖帝因事态紧急,停止斋醮,立即命司礼监太监王利带上“通牒’召三大臣议事。这是京师戒严的第四天,号称七八十万的京营劲旅,点兵时仅有老弱病残四五万人,为了补充兵力,临时招募了四万居民在城门外各沟口抵御俺答,又命戚继光等各地应试武举的一千多人分守城门。李本休致后改复原来的吕姓,故又名吕本,他是泥塑木雕式的人物,全程一言未发。对话主要在嘉靖帝与徐阶之间展开。 不等三大臣行礼完毕,嘉靖急切问道:“现在形势如此,奈何?” 首辅严嵩似乎要先定调子:“这都是抢夺的贼寇,不足为患。’ 徐阶不等严阁老把话说完,就驳了回去:“在城下杀人放火,岂能说是抢夺之贼?!正须商议如何御敌之策方好。 嘉靖目视徐阶说:“卿言是对的。”又把目光转向严嵩、李本二人: “虏中求贡文书在何处?’ 严嵩从袖中取出。 嘉靖帝因先已知悉文书的内容,直接发问:“此事应当如何回应?’ 严嵩好像早已有了脱身之术,随口答道:“这是礼部管的事。’ 嘉靖转问徐阶:“卿说如何办? 徐阶反应极为机敏,答道:“此事重大,当请皇上主张。” 嘉靖闻言,顿时不悦,作色道:“正须大家一起商量,为何又转推 给朕!” 徐阶见严嵩默不作声,答道:“现在贼虏驻兵近郊,而我们是战是守,一无所备。如果不答应,恐怕会激怒他们来攻城;如果答应,又担心他们贪得无厌。不能答应为宜。” 嘉靖:“如果对社稷有利,皮币珠玉,朕不会吝惜。” 徐阶:“如果只是皮币珠玉,也就罢了。万一有皇上不能接受的, 如何是好?” 嘉靖略加思索,悚然道:“卿考虑得可谓长远。但现在应当如何应对?” 徐阶:“权且请用计策‘款之’。” 嘉靖:“何谓‘款’?” 徐阶:“今天派遣一个通事(翻译)到虏营,告诉他们说,‘你们来求贡的文书用的是汉文,皇上怀疑是假的,特派我来询问缘由,如果真是出于你处,就另外商议来报’。如此一来一往,便有两天时间,我们战守的物资人马也能准备好了。” 嘉靖:“如果他们是真的求贡,又该如何处理?” 徐阶:“如他们求贡是实,就再派通事前往,对他们说:‘早年你的祖父曾经入贡,现在你仍想要入贡,本来会准许的。但没有兵临城下来求贡的道理,况且又没有番文的信使,这也不是你祖父的旧规。你可以退出大同边外,派人携带番文前来,把求贡的文书交给大同守臣为你转奏朝廷,就可以施行了。’” 嘉靖:“如果这样,他们能听则可,如果不听,又将如何?” 徐阶:“如果不听的话,我们的战守已经准备完毕,四方征兵也汇集京师,他们也会退回的。” 嘉靖:“卿所言极是。此事还要与百官廷议。” 严嵩见嘉靖语气和缓了一些,便及时提出:“现在中外臣民,都希望皇上能出朝理政,并拨乱反正。” 嘉靖露出了略带不屑的微笑,想到自己多年不临朝,说:“现在还不至于乱。朕不难一出,但是否有些突然?” 徐阶:“百官众庶盼望此举已经很久了,现在皇上一出,如久旱逢雨,怎么能说突然呢。” 嘉靖于是允准第二天临朝,命严嵩等三人退下,由徐阶出面与百官商议求贡之事。 当天下午,徐阶在午门紧急召集百官,传达皇帝旨意,他拿出俺答求贡文书说:“俺答要求派三千人进京求贡,如果不答应就攻城,朝廷请各位发表高见。”群臣面面相觑,许久也无人发表言论。徐阶理解百官的苦衷:公开表态极易惹祸。他只好发放笔墨纸签,让各自写下意见。这时,国子监司业赵贞吉高声说:“此事不必问,如果问的话,那些奸邪大臣,一定会把求和的计策献于皇上。万一皇帝准许纳贡,俺答肯定就会入城。三千多人入城的话,恐怕乌蛮驿*都难以容纳。况且俺答兵已经肆意深入,一旦内外夹攻,将如何抵御?各位不担心会震惊宫阙吗?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驱逐贼虏,如果畏惧贼虏的恐吓,被逼迫而许贡,那与城下之盟有什么区别!” 检讨毛起不赞同地说道:“由于时事紧急,应该暂且允许纳贡,等俺答出塞后再拒绝他们。”此音刚落,赵贞吉立即大声叱责毛起。 当天晚上,火光烛天,德胜门、安定门北,人居皆毁。嘉靖惶恐不安中,秘密派往窥探会议的中使回报廷议内情。他为赵贞吉的话而气壮,立即宣召入左顺门,令赵贞吉手疏应对之策。赵贞吉奋笔疾书,提出派遣近侍同锦衣卫官前往诸将营中,赏军激励士气,无论军民人等,只要得一首级即赏银百两,逗留观望不战者诛无赦。嘉靖览奏,大为嘉许,当即升赵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给赏功银五万两,令其前往各处,宣谕将士。 赵贞吉兴冲冲地前往西苑直庐拜谒严嵩,守门者却不放行,赵贞吉怒斥门役。通政使赵文华闻声而出,劝道:“你还是暂缓一下吧,当今的重大事件应该慢慢商议。”赵贞吉怒气冲天道:“你是权贵门口的犬,怎么会知道当今的大事?” 严嵩等三位大臣虽然得到皇上明日临朝的许诺,但考虑到嘉靖已经十几年没有上朝,也不敢公开发布消息,只传令百官明早穿戴公服,齐聚奉天殿。因国有大事,皇帝才会登临奉天殿,百官也自然理解其中之意。 奉天殿是永乐十九年(1421)正旦建成,明朝迁都庆典就在这里举行,以此作为定都的标志。可惜此殿不到半年就因雷击被毁,留下瓦砾一片。其后永乐帝忙于北征,加上仁宗、宣宗二帝一直想把都城迁回南京,直到英宗正统五年(1440)才重新修建。 八月二十二日,天还没亮,百官们早早齐聚奉天殿前,但不好的消息纷纷传来:俺答军由巩华城进犯大明各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京畿直隶、保定震动。 直到傍晚时,嘉靖才驾临奉天殿。群臣行三叩五拜礼后,嘉靖一言未发,只是命礼部尚书徐阶奉敕谕至午门,随即还宫。 明制颁诏天下,通常在承天门,而午门通常是颁朔、命将、献俘、宣旨的地方。对于群臣,记忆之痛却是午门廷杖。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在此跪听鸿胪寺官宣读谕旨的百官,自大清早就滴水未进,身体早已饿得筛糠一样,加之唯恐灾难降临,个个心惊胆战,恐惧非常。 果然,嘉靖把责任全部推到臣子身上,语气充满杀气。大略说: 今虏酋听我背叛逆贼,入侵畿地,诸当事之臣全不委身 任事,曰:“上不视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 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 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胁我正朝大内, 恐吓朕躬,沽名市美,非党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误事大 小诸臣,便一一指名,着实参劾定罪。 1 这里所说的“背叛逆贼”是指逃往俺答统辖之地的汉人。全篇敕谕为嘉靖帝不上朝理政辩护,而令这位皇帝难以容忍的是胁迫他上朝。末了一句是要追究官员的责任。 果然,谕旨发布后,当即把到任不足数月的张居正的老师、户部尚书——李士翱等多人革职,同时派锦衣卫前往通州、蓟州等地抓捕文武大吏。至于张居正为他的老师“平反”,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等到百官从午门散去时,宫门已到上锁时间。 王世贞诗中“云霄玉几昼还宫”,说的就是嘉靖帝自西苑还大内的情景。 在嘉靖帝的允准下,太监杨增等人在护卫的陪同下,当即前往俺答驻地,代表明廷允诺通贡,并劝其退兵。在得到明廷的保证后,八月二十三日,俺答把焚毁的上万区庐舍留给了大明,带着数量惊人的战利品,包括杂畜数百万只,男妇六十万口(含死亡),以及其他无从计数的金银财物,旁若无人一般,从京城撤离。而京营、边防军、各地勤王军、招募的义勇等多达二十万人,却一箭未发。两天后,京师解除戒严。 大杀戮随即展开。兵部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以贻误军机等罪,拟秋后处决。因三法司的判决书过于冗长,誊写需要一定时间,嘉靖一再派太监催促,仍不见送达后,他龙颜大怒,命将审判官员廷杖、夺俸;又降旨将丁、杨二人押赴法场,立即行刑,言官对此群起抗争、救护,嘉靖毫不退让,命将言官廷杖、削籍。八月二十六日,丁、杨被处斩。丁汝夔还被枭首示众,不准收葬。赵贞吉以举动轻率的罪名,被廷杖五十,贬为广西荔浦县典史。 亲自参与处理庚戌之变的徐阶,后来回忆说:“当时幸亏祖宗神灵的保佑,才转危为安。”史家多认为,如果俺答决意攻城,嘉靖帝就会成为宋钦宗或明英宗那样的囚中之物。晚明史家谈迁说,幸亏俺答很快从京城撤兵,如果真的围困十天一个月,其结局很难预料,要么会像李世民即位之初,与突厥在渭桥签订城下之盟那样,要么会像北宋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那样,除此之外,真的想不出其他办法。而当年在京城考中进士,目睹这场大事变,后来写作《鸿猷录》的史家高岱说:我目睹了庚戌之变,当俺答已进入古北口时,京城的官僚士大夫仍在轻歌曼舞,作长夜之饮,一闻警报,大小臣工,惊慌失措,就朝廷的应对而言,真如同儿戏一般,它暴露出天下安定时间长了,国家缺乏折冲应变的能力了!震撼最大的是嘉靖帝,此后每当塞外传警,他都惶恐不安地说:“莫非庚戌之事又出现了吗?” 中国传统史学通常用朝代来表述时间。法国的年鉴学派把历史表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短时段又称为“事件的历史”。如果把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长时段来考虑,恐怕再没有比庚戌之变更重大的事件,能够作为前后期的时间分野了,它直接影响到明朝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建以及京城外城的建造等一系列变化。 大事件在改写历史走向的同时,也使许多人的命运裹挟其中。严嵩与徐阶之间长达十几年的争斗,由此拉开大幕。而三年前考中进士的三位同年——杨继盛、王世贞、张居正,被迫调整仕途的坐标,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个誓做“铁脊之鬼”,一个争做文坛领袖,一个擎起改革大旗。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归宿,透视出那个时代的官僚士大夫对国家肩负的不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