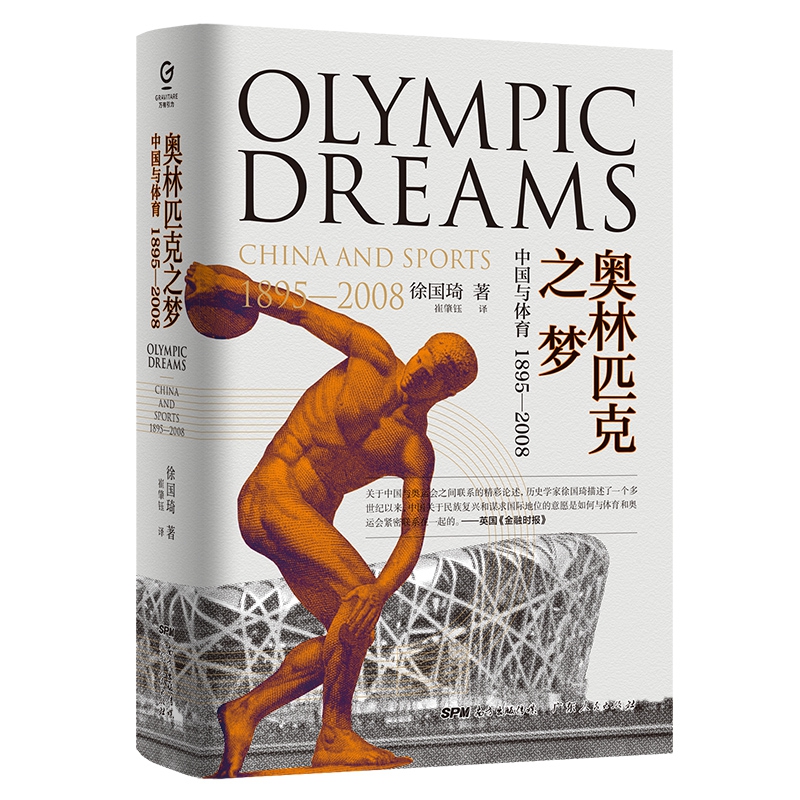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20
折扣购买: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奥运会间接证明着国家的实力,08年北京奥运让全
ISBN: 9787218135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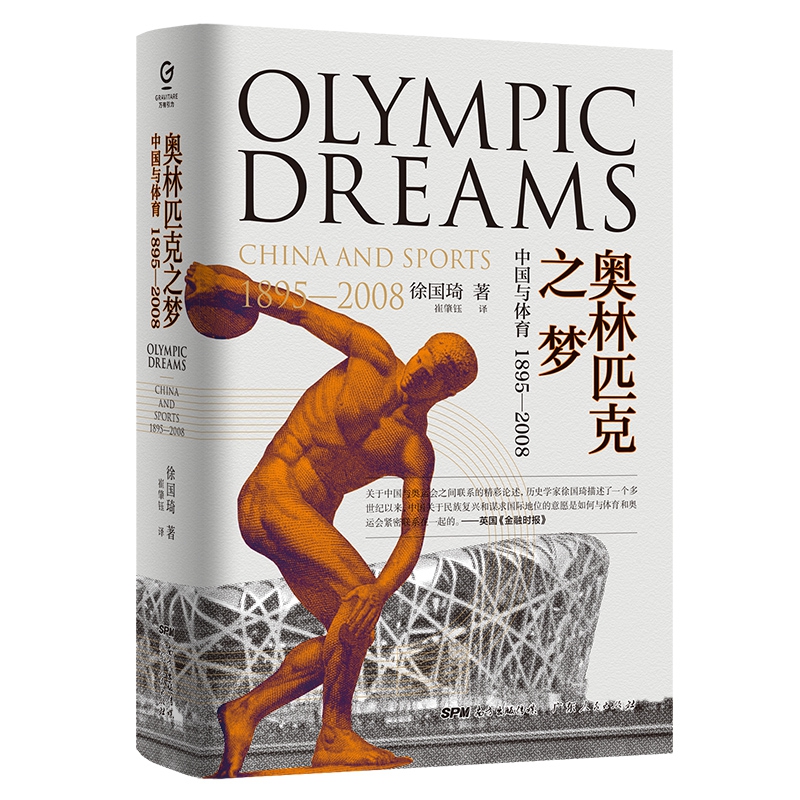
徐国琦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其在哈佛、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主要英文著作有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Great War (《西线战场陌生客》,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4)等。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 Idea of China 一书。中文著作包括其个人回忆录《边缘人偶记》《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难问西东集》《美国外交政策史》(合著)等。
第四章 “谁能代表中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13:3) 对皮埃尔?德?顾拜旦来说,现代奥运会是建立在“所有比赛,所有国家”的精神上的。当波希米亚和芬兰在出席1912年奥运会的问题上出现争端时,顾拜旦提醒双方有一种“体育地理”存在,它与“政治地理截然不同”。因此,他同意当时属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和俄国、芬兰作为独立个体参赛。但顾拜旦的乐观看法也许太天真了,各个政府在有关政治利益和合法性事务面前,通常不会理会他的这个崇高理想。虽然不是全部,但的确有些国家在处理奥运会及其相关问题时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例如当英国拒绝让爱尔兰以独立身份参加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时,爱尔兰运动员则拒绝在英国的旗帜下比赛。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奥委会依然声称只承认各奥委会,而不是民族国家。这样的话,原则上它可以认可任何领土上的国家奥委会。例如美国国土内就有三个奥委会:美国奥委会、波多黎各奥委会和关岛奥委会。英国统治范围内也设置有国际奥委会多重认证的奥委会,包括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国民党败走台湾,但仍不肯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国民党逃离大陆后,台湾通知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地址迁到了台湾,继续保留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国际奥委会面对“谁是代表中国”的问题,感到十分烦恼。 谁能代表中国?北京的立场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而国民党败退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看,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台湾只是一个省份,不属于、也不能属于各国际体育协会或者奥运大家庭。 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初对奥运会没有多少了解,不知道中国已经身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国多年,甚至还不清楚国际奥委会三位中国委员中的董守义选择在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另外两个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决定离开,前者在1949年后在香港生活,而后者则在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忙于巩固政权、建设国家,还有抗美援朝,没有留意到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举行。要不是苏联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要过很久才会考虑奥林匹克运动或者奥运会。在这件事情上,北京受惠于苏联,苏方促使北京及早加入其中(虽然它的代表团很晚才参加比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在北京连体育委员会都没有设立的时候,政府也已经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来组织体育活动。直到出席了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新政府才在北京设立一个单独的体育联合会。中国共青团的代表在从芬兰回国后,就中国出席赫尔辛基奥运会为刘少奇准备了一份报告,建议北京成立一个部级体育委员会,由副总理或其他高级领导人主持。这个建议获得接受,军事领导人贺龙后来领衔体委。 为什么苏联对北京加入奥林匹克感兴趣?因为国际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一改过去拒绝参加腐败的资本主义体育赛事的姿态,决定全面加入竞赛,以彰显苏联政治体系和社会所具有的优越性。1950年,苏联的官方体育组织被国际奥委会认可为国家奥委会,1952年赫尔辛基赛事成为了苏联首次出席的奥运会。 苏联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对体育和国际政治都有重要意义。1952—197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在他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人40年来第一次参赛——这庞大且组织良好的苏联代表团以其出色表现让世界震惊。”其运动员的表现在国内也颇受重视,1953年一份俄文报纸的社评表达了苏联人对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喜悦之情,声言:“苏联人民已经做好打开大门的准备……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运动员之间的铁幕将被掀开。”布伦戴奇也提到:“铁幕首先被掀开的地方应该在体育赛场上,这不是没有国际性意义的——也是对坚不可摧的奥林匹克理念的力量的一个伟大贡献。”布伦戴奇没有意识到,苏联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及其随之推动北京成为奥运大家庭成员的行动,会迫使国际奥委会在自己和北京本身的体育组织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处理“两个中国”问题。苏联完全有理由表示其与中国新生共产主义政权团结一致,并使之成为冷战思维下的一个亲密盟友。 苏联人似乎在1951年引发了北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注意。深受苏联政治和外交影响的195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赫尔辛基通知北京外交部,东道主芬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参加由它举办的奥运会。芬兰对北京参赛的热情使国际奥委会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J Sigfrid Edstroem)感到不安,他不想卷入复杂的中国事务中。 北京起初对世界体育不大熟悉,没把芬兰的邀请放在眼内。但苏联在第二年就此强烈敦促,使北京终于行动起来。1952年2月2日,苏联大使到北京紧急要求北京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1952年奥运会,以及新中国是否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并出席1952年2月15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苏联大使促请北京立刻答复。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会见苏联大使后,当天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参加1952年奥运会可行性的报告。这份最近才向学界公开的报告阐述了苏联人要求冯文彬就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态度知会苏联大使馆,说苏联有这样一个印象,北京不是奥运大家庭的成员,台湾才是。大使提醒北京参加奥林匹克是一次重要政治任务,甚至提出苏联政府愿意训练中国运动员,从而使苏联和中国运动员能够一起出战奥运会。 整个50年代,北京的官方政策大部分时候都是向苏联学习的,因此这个来自“老大哥”的要求和建议有着很重的分量。所以接到冯文彬的报告后,周恩来马上在2月4日接见他,一起商讨奥运会的事,随后在冯的报告上作出批语,当天递交刘少奇。周恩来告诉刘少奇,根据他和冯文彬的讨论,他认为北京应该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名义向国际奥委会发一封电报,声明台湾不能在奥运大家庭中代表中国。他建议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要求,允许北京参加2月举行的会议并出席奥运会。周恩来还告诉刘少奇,由于限期将到,这份电报已经发出。在没有了解中国过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历史的情况下,这份电报发到国际奥委会,声称北京刚刚组成了国家奥委会,并要求国际奥委会认可,以便北京能够参加1952年奥运会。周恩来进一步向刘少奇汇报说:“估计如[国际奥委会]二月会议拒绝我方参加,则七月比赛即可不去,免与蒋匪组织碰面; 如二月会议邀请我们而拒绝蒋匪组织参加,则政治对我有利,且比赛地点在赫尔辛基,可以参加。即使我比赛的几样成绩差,也不甚要紧。”刘很快就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这份详细陈述了北京最早对奥林匹克运动和1952年奥运会产生兴趣背后因由的报告,也就表明北京决定通过奥运大家庭和奥运会的成员资格来打响争取国际合法资格认可的第一场战役。 一旦做出决定,北京就行动起来,且迅速而果断。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1952年6月所写:“共产党中国的组织机构正想尽办法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驻芬兰大使耿飙亲自确认北京的电报在2月5日发送到国际奥委会。中国甚至派其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人员就北京的成员资格和1952年奥运会邀请的事,亲自探访埃德斯特隆。盛之白在2月13日国际奥委会的奥斯陆会议上向埃德斯特隆做了陈述,提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六亿人民,应被视作中国唯一适合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他进一步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开除王正廷和孔祥熙,因为他们不能代表中国,却有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他还要求取消对台北的认可。但是埃德斯特隆已经从北京外交人员那儿听了很多这样的话,于是打断了盛之白。他说:“亲爱的先生,您既没资格也没权力去给国际奥委会下命令和要求!” 但在这件事上,国际奥委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力介入带有体育政治化倾向。此外,中国政府对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及其原有身份没有重视,因而没有任用他去和国际奥委会沟通。后来,还是董守义主动和中国政府联系的。要是中国了解国际奥委会的规则和奥林匹克原则,直接让董守义去联系,它和国际奥委会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或许就少了许多风波。真那样,董守义就可以参加国际奥委会在那年2月份举行的第一轮会议——时间恰到好处,因为原国民党高官王正廷和孔祥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被击败之后感到没有面子去赫尔辛基参加会议。 芬兰的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艾力克?冯?弗伦克尔(Erik von Frenckell)通知其他委员,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联系了他,问为什么北京还没有接到参加1952年奥运会的邀请。弗伦克尔建议国际奥委会会议在6月1日参赛申请最后限期前就中国的事做出决定。即将在这年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布伦戴奇声明大会在做决定前必须先和三位中国委员取得联系,然而由于中国内战激烈,三位委员都在1948年后就与国际奥委会失去了联系。 情况逐渐明朗化。台湾方面有传言说唯一留在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已经身故。然而埃德斯特隆在与盛之白的会面中问及董守义时,却被盛告知他还健在。“他的位子在赫尔辛基这儿。” 由于国际奥委会规定运动员只有归属于一个国际体育组织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于是中国采取一个新策略:1952年4月,劝说国际游泳联合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成员,声言总会是之前的中国体育组织的延续,并愿意支付1949年以来的会费欠款。对中国之前有成员资格的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包括五项全能、体操、冰球、滑冰、排球和足球等组织,中国也采取同样办法。 如果北京做好准备工作,并首先派董守义出面,那么所谓“谁能代表中国”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当初中国政府对一些具体规则缺乏了解,使简单的体育事务变成了一件复杂的政治事件,以致使北京和国际奥委会关系变得紧张。埃德斯特隆在1952年6月17日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电报中说,北京的奥委会仍未得到认可,赫尔辛基之行“没有用处”。他在7月8日向中国体育官员荣高棠发了另一封电报,告诉他国际奥委会决定不让中国运动员“在问题解决之前参赛”,还让荣高棠告知董守义,“强烈希望”他到赫尔辛基来。 尽管埃德斯特隆态度强硬,中国还是下决心参加奥运会,并派董守义去参加该月月底的国际奥委会赫尔辛基会议。当董守义带着一名翻译出现在会议上时,埃德斯特隆让翻译离场,因为根据国际奥委会规定,翻译是不能参加其会议的。翻译说董守义只会说中文,拒绝离去。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的话,埃德斯特隆用他的手杖猛扣桌子,冷冰冰地说:“你在说谎。还在1948年,我和他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谈话!赶快离开会议室!”翻译于是带着董守义一起离开。但新当选的苏联委员康斯坦丁?安德亚诺夫(Konstantin Andrianov)在1951年国际奥委会维也纳会议上带翻译出席会议(因为他不像委员资格所要求的,会说英语或法语),却没有受到来自国际奥委会的抗议,这也是事实。直到1954年5月雅典会议召开时,国际奥委会才决定新当选委员一定要能说流利的法语或者英语。无论如何,这次董守义的出现对国际奥委会来说几乎没用,因为他没法参与解决关于中国参赛要求的种种问题。 在1952年7月的赫尔辛基会议上,埃德斯特隆提醒各委员说,中国的运动员正在列宁格勒等待邀请。面对要迅速作出决定的压力,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打算既不接受台湾,也不接受北京参加1952年奥运会。这显然是一个回避且意义不大的做法,正如艾力克?冯?弗伦克尔指出的,台湾的奥委会已经获得认可,因此不可能将台湾排除在奥运会之外。弗伦克尔提出建议,即让“北京和台北”的运动员都参赛。终于,国际奥委会先将北京的成员身份问题搁置起来,以29比22的票数通过让两队同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7月18日,即赫尔辛基奥运开幕的前一天,国际奥委会向北京和台湾同时发出了邀请。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快明白到奥运会对其政治合法地位的重要性,以让人惊异的速度作出行动。在国际奥委会最终亮起绿灯时,共和国的三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立刻批准了决定(虽然该决定直到7月23日北京得知台湾不会参赛时才公布)。7月24日深夜,周恩来与代表团领导人会谈并告诉他们:“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去迟了不是我们的责任。”代表团7月25日出发去芬兰,7月29日到达赫尔辛基,这时已是闭幕式的前一天。所有比赛都错过了,只有一名游泳选手参加了初级阶段的比赛,但没有成功进入第二轮。即便如此,北京还是参与了奥运会的一些文化项目。周恩来观看了将在赫尔辛基进行表演的中国杂技团的彩排,他告诉杂技团的演员,他们是中国的国宝,希望他们能为祖国增光。 北京对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兴趣所在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政治合法地位,在当时西方国家承认台湾当局的情况下,苏联人也充分认识到,赫尔辛基奥运会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只要到场,让五星红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飘扬,就是北京新政府的一次胜利。 再者,北京通过将一只脚踏入1952年奥运,又一次迫使国际奥委会着手处理“谁代表中国”问题。1952年8月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赫尔辛基当天,中国政府迅速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及秘书长荣高棠的名义给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奥托?迈耶发电报,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通过重组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认可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而成立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业余体育组织,并实施全国体育运动的管理。根据这些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认可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荣高棠对国际奥委会邀请台湾参加1952年奥运表示愤怒: 我不得不代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这种完全违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和特色的决定提出抗议。为了维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尊严和规章制度,我坚决要求对在台湾残余的国民党的体育组织和代表进行抵制……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相关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我同时要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所有国际奥林匹克机构和组织中被授予合法地位。 荣高棠在1954年4月9日以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名义发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一封信,再次要求国际奥委会在其即将于5月14日举行的雅典会议上,正式承认中国奥委会。1954年,国际奥委会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3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官方奥林匹克委员会。5月26日,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奥托?迈耶将这个决定通知北京。迈耶写道:“我们以最大的热情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奥运大家庭,并预先感谢你们在贵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配合。”北京再次从国际奥运会实现了自己的诉求。 中国或许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上打赢了“谁能代表中国”的第一场战役,但在1956年却出现了问题。1956年奥运会举行前,北京不但宣布参赛,而且敦促其运动员加紧准备。在《人民日报》9月2日头版发表题为《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去》的社论,号召中国运动员做好准备,并“在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祖国的荣誉而赢得胜利”。同版的另一篇文章声称中国政府欢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运动员加入中国奥运代表团。因为台湾仍然是奥运大家庭的成员,北京打算抢先到达澳大利亚,希望台湾当局会因为看到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已经在此而放弃参赛。但当北京代表团抵达时,台湾代表团已经入住了奥运村,它的旗帜正在飘扬。中国大陆向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于是决定撤离奥运会。 从1954年到1958年,台湾和北京都声称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代表“中国”。在阻止台湾参加1956年奥运会失败之后,北京逐渐得出结论:国际奥委会、尤其是它的主席——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对北京怀有恶意,并且支持台湾继续留在奥委会。于是北京在1957年通过董守义(以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作为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角色,而不是反过来)升级了对国际奥委会的批评。在12月下旬,董守义给布伦戴奇写信说国际奥委会“应该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奥林匹克委员会,(而)那应该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1958年4月23日写给布伦戴奇的另一封信上,董守义或以他的名义的官员表达了对布伦戴奇在谈论台湾时“许多不友好和歪曲评论”的“愤怒”。布伦戴奇将4月23日的信称为“侮辱性的”,并要求董守义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他写道:“你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却不顾自己的职责,企图利用一切机会提出政治问题,假如你继续违背我们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你辞职。” 就这样,北京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争论变得没有回头之路。根据权威消息来源,1958年6月28日,总理周恩来与贺龙、陈毅和其他外交部及全国体育管理部门的官员会谈,讨论体育和对外关系问题。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极其愤怒地”回复布伦戴奇,称他的态度“完全表明你是一个蓄意为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政治阴谋效劳的忠实走卒”,并且说:“像你这样玷污奥林匹克精神,破坏奥林匹克宪章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今天的国际奥委会操纵在像你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无遗。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所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 同一天,董守义宣布辞职,北京正式断绝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中国奥委会由秘书长张联华署名的、写给奥托?迈耶的短信说:“国际奥委会承认在台湾的、所谓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这一做法是非法的,我们提出严正的抗议”,并且北京将“不再承认国际奥委会”。这份声明再次谴责布伦戴奇的反华立场,并把他的态度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对立场联系起来。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下,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立即退出11个接受台湾为成员的国际体育组织。1958年8月15日,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常委会甚至修改了章程,删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字眼。这一动作清楚表明北京在8月19日正式给国际奥委会发信前,已经决定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国际奥委会意识到它要解释与中国之间所发生的事情。1958年9月5日,秘书长奥托?迈耶向所有委员、国家奥委会和媒体发了一封信,重申布伦戴奇的理由,声称北京“似乎不明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承认政府,而只承认体育组织(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已被认定国家的政府,只要其体育组织遵守奥林匹克规则),而各项规则的最重要关注点在于防止政治干预的必要性。很遗憾,这些原则在中国没有得到更好的理解。” 双方似乎都确信错在对方。然而,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是对国际奥委会声誉和奥林匹克理想的一个重大打击,导致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一场持续超过二十多年的隔绝。 谁代表中国?台北的立场 台湾之所以能成功留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与冷战国际政治有很大关系,这要远胜于它自己的政策的效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外交上都宁愿承认台北而不是北京,这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创造了优势。无论如何,台湾直到1971年都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 台北也有过几次行动,其中一个是声称其政治合法性直接扎根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并从1922年起就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此外,当国民党逃离大陆后,台北立刻通知国际奥委会说中国奥委会的地址迁到了台湾。这些策略帮助台北继续留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即使有种种优势,台湾当局在讨论其会员身份的时候也犯了好些错误,其中一个大错就是对1952年奥运会的处理。当时台湾当局打算派运动员参加这次奥运,从1951年就开始为比赛做准备,当年3月拨出38万新台币用于选拔和培训运动员。然而在1951年5月10日,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体育界元老郝更生建议台湾不要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他担心即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会借大会来对抗台湾。郝更生因消息闭塞而作出的建议在高层引起动摇。当台北得知北京获邀出席奥运会时,受“汉贼不两立”思想的影响,坚决不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得以强化。换句话说,“没有两个中国”的基本事实上已经潜藏在台北此时的思维方式中,(这比中国大陆采取这一立场并以此为由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二十多年要早得多)。 台北的奥委会1952年7月19日在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的正式信函中写道:“根据中国国家奥委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和被认可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权利和立场,作为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52年7月17日全体会议采纳方案的抗议,我恳切地通知您,我们已经决定退出参与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这封信先由郝更生签署,后来台湾地区奥委会主席也签了名。台湾的奥委会在其正式声明中对国际奥委会允许中国大陆参加1952年奥运会提出抗议,称之为“不合法,因其同意没有加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唯一合法的、且被承认多年的全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比赛选手参赛。”然而,台湾不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定让北京不受挑战地踏进国际体育界的大门,作出首次亮相。(正如此后将解释的,国际奥委会就参加1952年奥运会的问题给台湾发出的混乱信号,也影响到台湾作出不参加比赛的决定。 台北的另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就其在国际奥委会的两位代表孔祥熙和王正廷采取行动,以致他们长期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奥委会事务,面临被迫辞职的境地。孔祥熙从1939年起就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却从来没有出席过它的会议。因为委员在理论上由国际奥委会自行选出,并作为派到他们所在国的奥林匹克大使发挥作用,所以委员个人的言论会通过其国家奥委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台北如果在会议桌上多发声音,或许会在与北京的成员地位争斗中受益。明显偏向台湾的布伦戴奇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前就向郝更生提出过忠告:“现在台湾的要务在于在赫尔辛基有自己的代表,准备好为获得各个国际体育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认可而大斗一场。这个事态很严重。”然而,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就奥运大家庭成员资格的关键外交交锋中,孔祥熙的唯一贡献只是在1952年2月29日给奥托?迈耶写了一封信,抗议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因为这违反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申明的关于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必须隶属于国际奥委会的规则。”孔祥熙认为:“我相信,在台湾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仍然存在,而且在运转。” 布伦戴奇继续催促台湾行动。1954年4月22日,他发越洋电报给郝更生,直白地告诉他“最重要的是您要在雅典有人。王(正廷)和孔(祥熙)根据规章都属违纪,由于经常缺席而终将丧失(他们的)委员资格。”但这些警告和劝说都付诸东流。1955年,在国际奥委会的催促下,孔祥熙最后在6月24日向布伦戴奇递信请辞。王正廷虽然比孔祥熙更多地参与了国际奥委会的事务,但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之后也很少出席其会议和其他活动。他在1954年向布伦戴奇提交辞职信,之后又变卦,但还是在1957年最终辞职。换句话说,在这几个关键发展过程中,台湾并没有活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而中国大陆的董守义却积极地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益。 即使冷战政治——还有极其偏向台湾的布伦戴奇的鼓吹——帮助台湾在北京因1958年退出奥林匹克运动而使“谁能代表中国”问题成为世界新闻时留在奥运大家庭,国际奥委会还是要就台湾的成员资格采取行动。在1959年慕尼黑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要求在台湾的奥委会改名,理由是“这个国家奥委会不可能管理中国大陆的体育事务”。国际奥委会认为这个主张有道理,要台北着手取新名:“设在台北(台湾)的中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将会收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的通知,指出它不能继续以这个名称获得认可,因为它不能管理中国这个国家的体育事务,而这一名称将会从官方名单中除去。如果以别的名称获得认可的申请递交上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会予以考虑。” 然而,国际奥委会坚持要在台湾的奥委会改名的立场在美国受到了主流媒体、政客和大众的强烈批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就此话题发了好几篇社论,其中一篇写道:“通过将台湾驱逐出国际奥委会——并最终取消参加奥林匹克资格——这个委员会向最粗鲁的政治勒索屈服。”社论将国际奥委会的决定称为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懦弱、含糊、可耻……台湾‘不再代表中国整个国家的体育’的想法为一个直率的美国人所不齿。”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威廉?西奥多?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也为此感到沮丧,他给布伦戴奇写信说:“我同意《纽约时报》5月30日社论的观点……除非这个开除的决定被撤回,不然奥林匹克将不再代表任何有价值的体育运动,而美国人民应收回对它的支持。” 美国政府也受到压力而有所行动。在台湾将国际奥委会的做法称之为“背叛”时,美国国务院声称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是“一个明显的政治犯罪行为”。美国众议院一致投票通过,“如果任何自由国家被阻止参赛的话”,将收回拨给加州举行1960年冬季奥运会的40万美元专款。纽约州议员多尔恩(F.E.Dorn)呼吁,如果台湾被阻止参加奥运会的话,美国就退出奥林匹克运动。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谴责国际奥委会的政治举动,而美国民众发出的抗议信如潮水般涌来。 布伦戴奇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他自己草草写下:“人人都有行动。”后来又写道:“这个国家似乎掀起一种前所未有一边倒的狂热情绪。”他感到自己很孤独,“面对一亿七千五百万被消息误导的人民”。可怜的布伦戴奇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他的标准回答:“亲爱的先生或女士:显然,你们被消息误导了。”然后解释,台湾既没受到错误对待,也未被逐出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只是让台湾为自己挑一个更合理的名号。” 在这场文字战争中,政治有显著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篇社评指出:“现在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撤消对台湾的承认而激发的怒气稍有平息,这或许有助于看清奥林匹克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蹂躏,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国际奥委会就台湾的决定引起的热烈政治骂战中,美国以外的媒体似乎对情况有更透彻的理解。《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在1959年6月11日写道:“问:政治什么时候才是非政治性的?答:当它是你的政治的时候。质疑你组织的纯洁性的人总是派别鲜明的其他人。”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这正是当国际奥委会声明,因为台湾“不能管治整个中国的体育”,所以它的奥委会不再被认可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这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很明显”的事实,也是许多美国政客表示愤怒的原因。作者评论:“让美国之外的人颇为费解的是,忠于你的盟友而不是政治,但是承认一个在台湾岛上的、不可能从大陆派出任何运动员的委员会却是政治。” 虽然来自美国的强烈责骂让国际奥委会只有招架之功,它仍不得不为台湾的奥委会找个合适的名字。台湾应该在奥运大家庭中使用什么名称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1960年旧金山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委员乔治?瓦尔加斯(Jorge Vargas)提议:“为什么不把‘中国’和‘台湾’放到一起,就叫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可惜,国际奥委会用了19年时间才明白这一提议有多明智,用了20年才在蒙特维的奥采用这精确的名字去解开长期的僵局。 国际奥委会一如既往地能力不济,直到1960年罗马奥运会即将举行前才为台北的奥委会定出新名称。当时罗马组委会已经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将“中华民国”一名印入了所有文件和单张中,因此它对要改用“台湾”一名非常恼怒。组委会告知国际奥委会不可能重印所有文件,但是如果国际奥委会在会议记录中写清楚改名是如何在最后一刻实施的,它可以接受改名。更糟糕的是,当国际奥委会会议就新名称进行投票时,两次都陷入了25票对25票的僵局。国际奥委会这时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最终委员们同意台湾当局代表团在罗马奥运会中以“台湾”的名义参赛,但在将来可以按在台湾的奥委会请求,使用“中华民国奥委会”一名。 就这样,来自台湾当局的运动员以“台湾”这个地理名称参加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比赛和列队游行,尽管台北认为这称号带有歧视性和不公平。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决定让世界知道他们对这个决定的不满,台北代表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开幕式入场时队前打着“UNDER PROTEST(抗议中)”的字样。 这一行为惹怒了国际奥委会。布伦戴奇和奥托?迈耶联合致信参加1960年奥运会的台北代表团,写道:“我们认为你们的姿态不得体,具有政治化思维并且有损奥运会应有的尊严。我们觉得,你们在这样的行动中失去了世界运动员应有的凝聚力。我们不得不责备你们,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但这样做是出于一个希望,即你们将来能明白,你们必须以你们有管辖权的地区的名字参赛,且具备更好的体育精神。” 台湾和国际奥委会互相羞辱了一番,但名称问题依然未解决。郝更生在给国际奥委会的一封信中请求委员会在1963年巴登-巴登会议上考虑台湾将来出席奥运会的用名问题。他写道:“在105个获认可的奥委会中,只有‘中华民国’的委员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被迫使用一个……实质上不同于我们委员会所代表国家的名称。”台湾提议将它们正式名字的缩写“ROC”作为其称号。布伦戴奇在巴登-巴登会议上竭力让台北实现其愿望。印度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桑迪(G.D.Sondhi)1963年12月9日写给台湾地区奥委会主席杨森的一封信中谈到:“布伦戴奇先生以其独特而有力的方式帮助你们,你们应该感谢他。在按你们希望修改你们国家名称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困难。”最后,在1968年国际奥委会墨西哥城会议上,布伦戴奇成功地将在台湾的奥委会定名为“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进行“乒乓外交”以及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台湾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境况变差了。甚至香港也向国际奥委会抱怨台湾。在布伦戴奇1966年9月9日给台湾的奥委会的信中写到,国际奥委会收到来自香港业余体育联合会和奥委会的许多严厉的批评,“反对你们的国家联会通过各种方法为他们的运动队伍招募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其中一个香港投诉指出,台湾人口是香港的两倍,应该有能力自己组队。“如果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双脚自立,就要有勇气退出国际竞争。这种情况是最令人不满的……我想这种政策令国际奥委会及其规则为世人耻笑。”布伦戴奇同意该说法,警告这种做法同时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条文,并且说:“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立刻着手通过你们的立宪联邦防止这些对奥林匹克规则的侵犯。” 在第五章我们将详述的“乒乓外交”,是北京采取的外交攻势,促使许多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徐亨是1970年由布伦戴奇以迂回手法、没经过执委会同意就选出的国际奥委会台湾委员,他在1972年4月3日一份给台湾当局的绝密报告中写到,台湾1972年之后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极其险恶”,因为亲台的布伦戴奇主席即将离任,没有他的呼吁,许多欧洲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倾向于将票投给中国大陆。“应如何布置,以巩固我国在国际奥会之地位,实为当务之急……一旦容匪入会,则我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即受限制,甚至作友好访问比赛,亦难实现。其后果实不仅扼杀体育,甚且影响国民外交。”徐亨建议台湾当局快速果断行动,与韩国奥委会委员密切合作,并保证台湾当局在任何国际体育会议和集会中出现。在台湾的奥委会或许理解到徐亨所言之紧急,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高级别小组去处理国际体育事务。 但是潮流似乎向不利于台湾的方向转化,即使日本等以前与台湾友好的国家也开始质疑台湾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以代表中国的成员身份出现的合法性。作为回应,国际奥委会台湾委员徐亨指出:“有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支持者可能声称,中国只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必须在‘两个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现在处于两个政府管治下的分裂状态的事实而悲哀。但我们是以体育界领导人而不是政客的身份聚到这里的,所以我们没法改变这生活中的政治现实。” 台北的地位在70年代后期进一步恶化。1978年5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着手解决“谁能代表中国”问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和台北,目的在于劝说台湾在继续以独立被认可的成员身份留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情况下,取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名称。国主席“提醒委员们,如果台湾拒绝改名,国际奥委会将被迫执行中止机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僵局之后,新的国际形势发展促使双方通过妥协退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人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只有在外国迫使的情况下才着手真正有效地处理这一事务。 《奥林匹克之梦》利用最新的档案资料,从一个百年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体育,探索了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之交痴迷于西方体育,以及这与中国寻求国家和国际认同的关系。通过对乒乓外交和中国处理各种体育赛事的案例研究,本书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细节和对中国重大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寻常的见解——这些见解将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