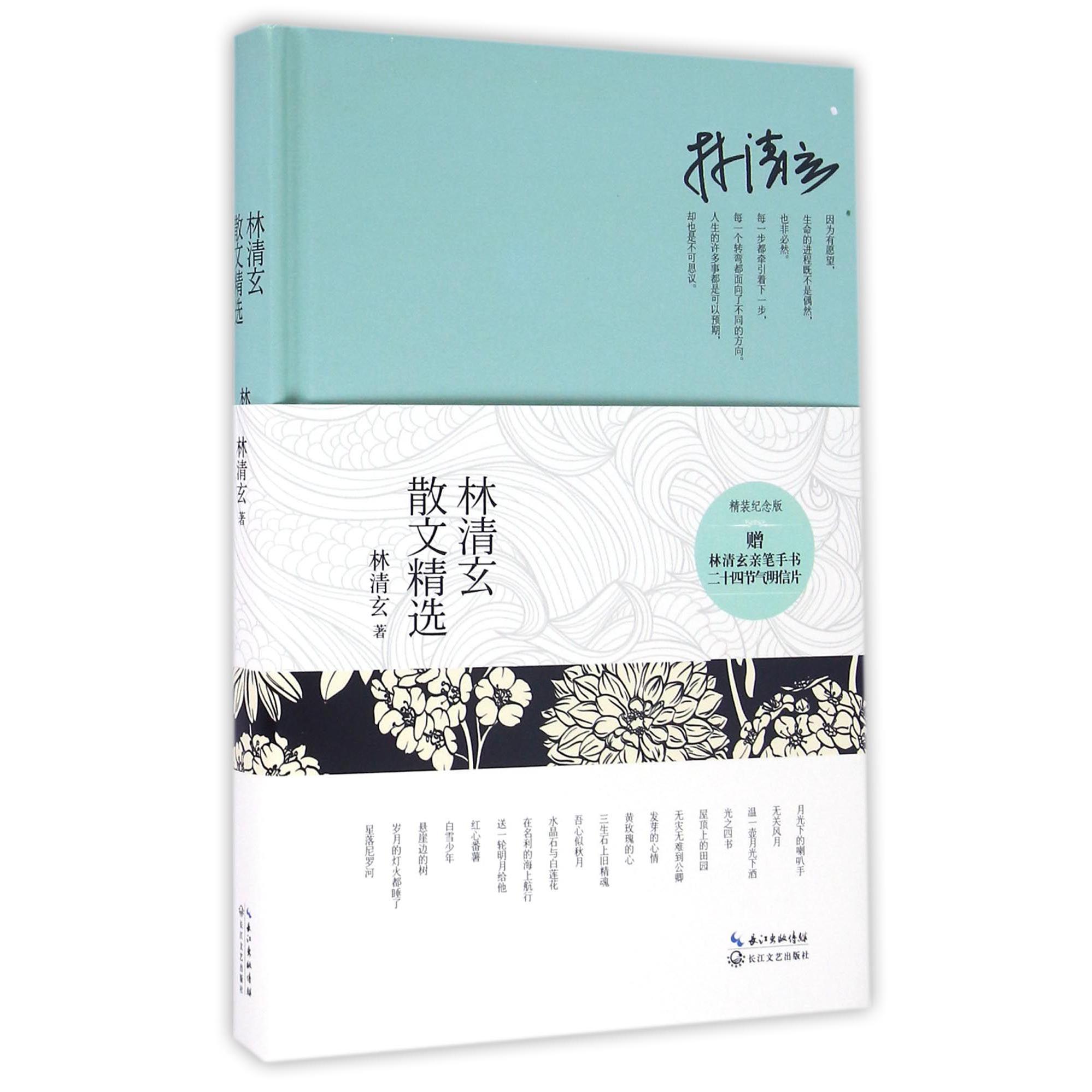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35.80
折扣价: 22.60
折扣购买: 林清玄散文精选(精装纪念版)(精)
ISBN: 9787535486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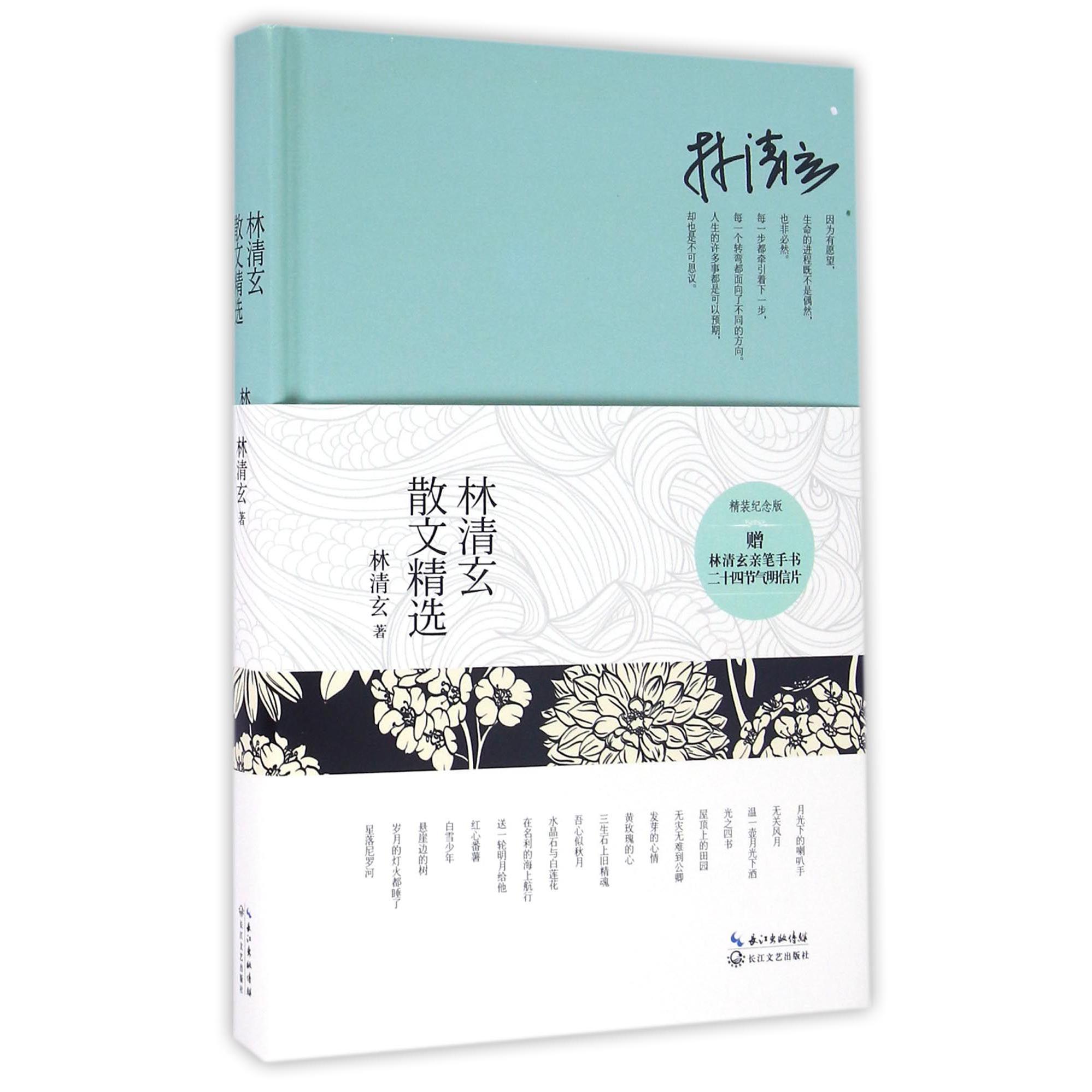
林清玄,**高雄人,散文大师,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二十岁出版散文集《莲花开落》,正式走上散文创作的道路;三十岁前揽尽**各项文学大奖;三十二岁时入山修行三载,出山后写成“身心安顿”系列,风靡整个**地区;四十岁出版“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 他在文学上悲智双运,情境兼容,不断创造推新,自成一家之言。三十多年来,他著书百余部,且本本畅销。他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教材,是**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
月光下的喇叭手 冬夜寒凉的街心,我遇见一位喇叭手。 那时月亮很明,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 他的影子诡异地往街边拉长出去。街很空旷,我自街 口走去,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我们原也会像路 人一般擦身而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大街竞被 他孤单落寞的影子紧紧塞满,容不得我们擦身。 霎时间,我觉得**神秘,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 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塞得街都满了,我惊奇地 不由自主地站定。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他的脚步零 乱颠簸,像是有点醉了,他手中提的好像是一瓶酒, 他一步一步逼近,在清冷的月光中我看清,他手中提 的原来是一把伸缩喇叭。 我触电般一惊,他手中的伸缩喇叭造型像极了一 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它的身躯盘卷扭曲,它充 满了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好像随时要吐出“咝咝 ”的声音。 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斑驳锈 黄色的音管因为有许多伤痕凹凹扭扭,缘着喇叭上去 握着喇叭的手血管纠结,缘着手上去我便明白地看见 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 成点点星光,穿着一袭宝蓝色滚白边的**,大盘帽 也缩皱地没贴在他的头上,帽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老 鹰——他真像一个打完仗的兵士,曳着一把流过许多 血的*刀。 突然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汽车从我的背后来, 强猛的光使老人不得不举起喇叭护着眼睛。他放下喇 叭时才看见站在路边的我,从干扁的唇边进出一丝善 意的笑。 在凌晨的夜的小街,我们便那样相逢。 老人吐着冲天的酒气告诉我,他**下午送完葬分到 两百元,忍不住跑到小摊去灌了几瓶老酒,他说:“ 几天没喝酒,骨头都软了。”他翻来翻去在裤口袋中 找到一张百元大钞,“再去喝两杯,老弟!”他的语 句中有一种神奇的口令似的魔力,我为了争取请那一 场酒费了很大的力气,*后,老人粗声地欣然地答应 :“就这么说定,俺陪你喝两杯,我吹首歌送你。” 我们走了很长的黑夜的道路,才找到隐没在街角 的小摊,他把喇叭倒盖起来,喇叭贴粘在油污的桌子 上,肥胖浑圆的店主人*一口广东口音,与老人的清 瘦形成很强烈的对比。老人豪气地说:“广东、山东 ,俺们是半个老乡哩!”店主惊奇笑问,老人说:“ 都有个东字哩!”我在六十烛光的灯泡下笔直地注视 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竞在他平整的双眉跳脱出来几 根特别灰白的长眉毛上,看出一点忧郁了。 十余年来,老人干上送葬的行列,用骊歌为永眠 的人铺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用的是同一把伸缩喇 叭,喇叭凹了、锈了,而在喇叭的凹锈中,不知道有 多少生命被吹送了出去。老人诉说着不同的种种送葬 仪式:他说到在披麻衣的人群里每个人竟会有**不 同的情绪时,不觉仰天笑了:“人到底免不了一死, 喇叭一响,英雄豪杰都一样。” 我告诉老人,在我们乡下,送葬的喇叭手人称“ 罗汉脚”,他们时常蹲聚在榕树下嗑牙,等待人死的 讯息。老人点点头:“能抓住罗汉的脚也不错。”然 后老人感喟地认为在中国,送葬是一式一样的,大部 分人一辈子没有听过音乐演奏,一直到死时才赢得一 生努力的荣光,听一场音乐会。“有**我也会死, 我可是听多了。” 借着几分酒意,我和老人谈起他 飘零的过去。 老人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家 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豆田,他年幼的时代便在大豆 田中放风筝、抓田鼠,看春风吹来时,田边奔放出嫩 油油的黄色小野花,天永远蓝得透明,风雪来时,他 们围在温暖的小火炉边取暖,听着戴毡帽的老祖父一 遍又一遍说着永无休止的故事。他的童年里有故事、 有风声、有雪色、有贴在门楣上等待新年的红纸,有 数不完的在三合屋围成的庭院中追逐的不尽的笑语… … “廿四岁那年,俺在田里工作回家,一部*用卡 车停在路边,两个中年汉子把我抓到车上,连锄头都 来不及放下,俺害怕地哭着,车子往不知名的路上开 走……他奶奶的!”老人在*车的小窗中看他的故乡 远去,远远地去了,那部车丢下他的童年、他的大豆 田,还有他老祖父终于休止的故事。他的眼泪落在车 板上,四周的人漠然地看着他,一直到他的眼泪流干 ;下了车,竟是一片大漠黄沙不复记忆。 他辗转地到了海岛,天仍是蓝的,稻子从绿油油 的茎中吐出他故乡嫩黄野花的金黄,他穿上戎装,荷 *东奔西走,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俺是想着故乡的 啦!”渐渐的,连故乡都不敢想了,有时梦里活蹦乱 跳地跳出故乡,他正在房间里要掀开新娘的盖头,锣 声响鼓声闹,‘俺以为这一回一定是真的,睁开眼睛 还是假的,常常流一身冷汗。”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