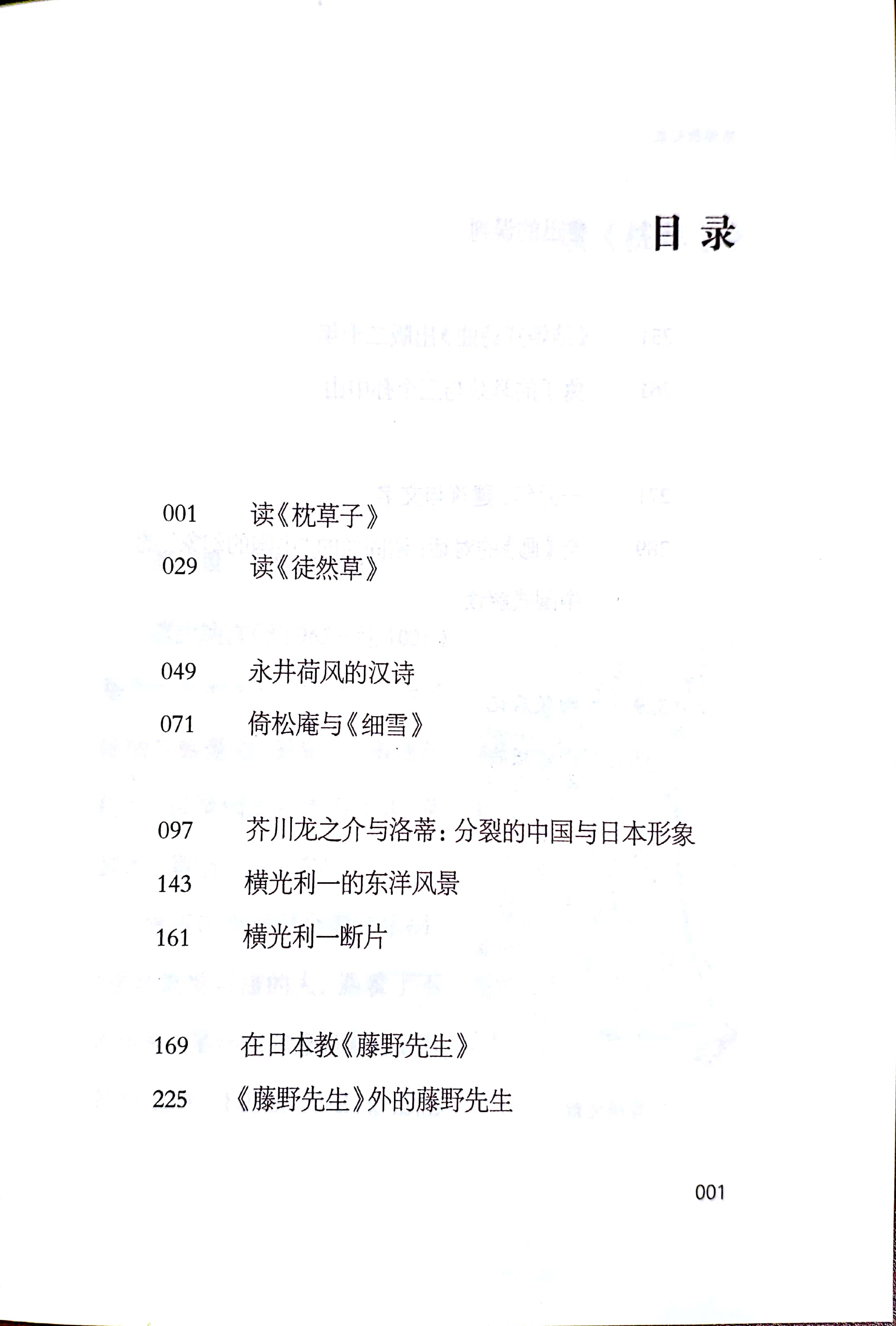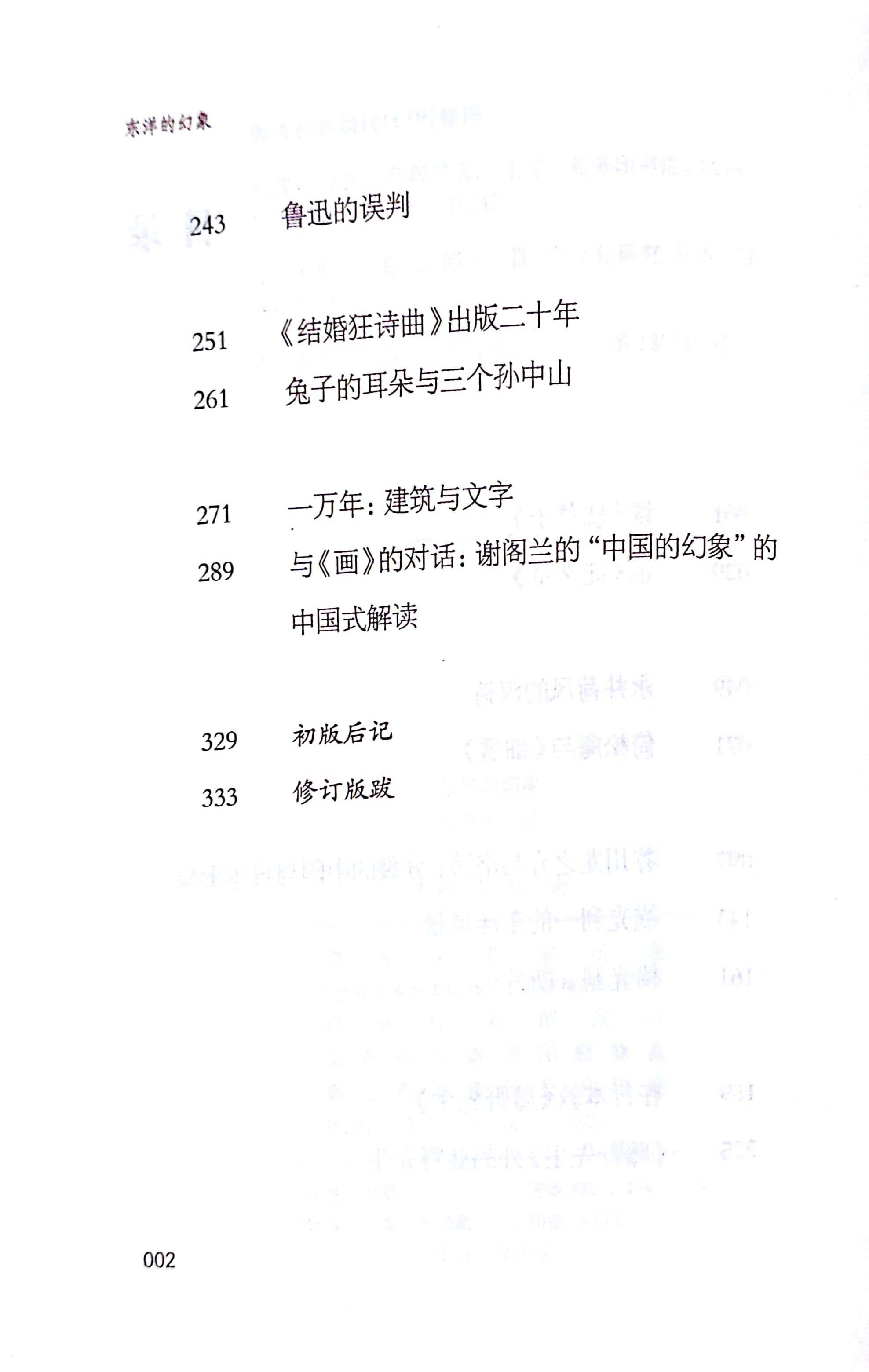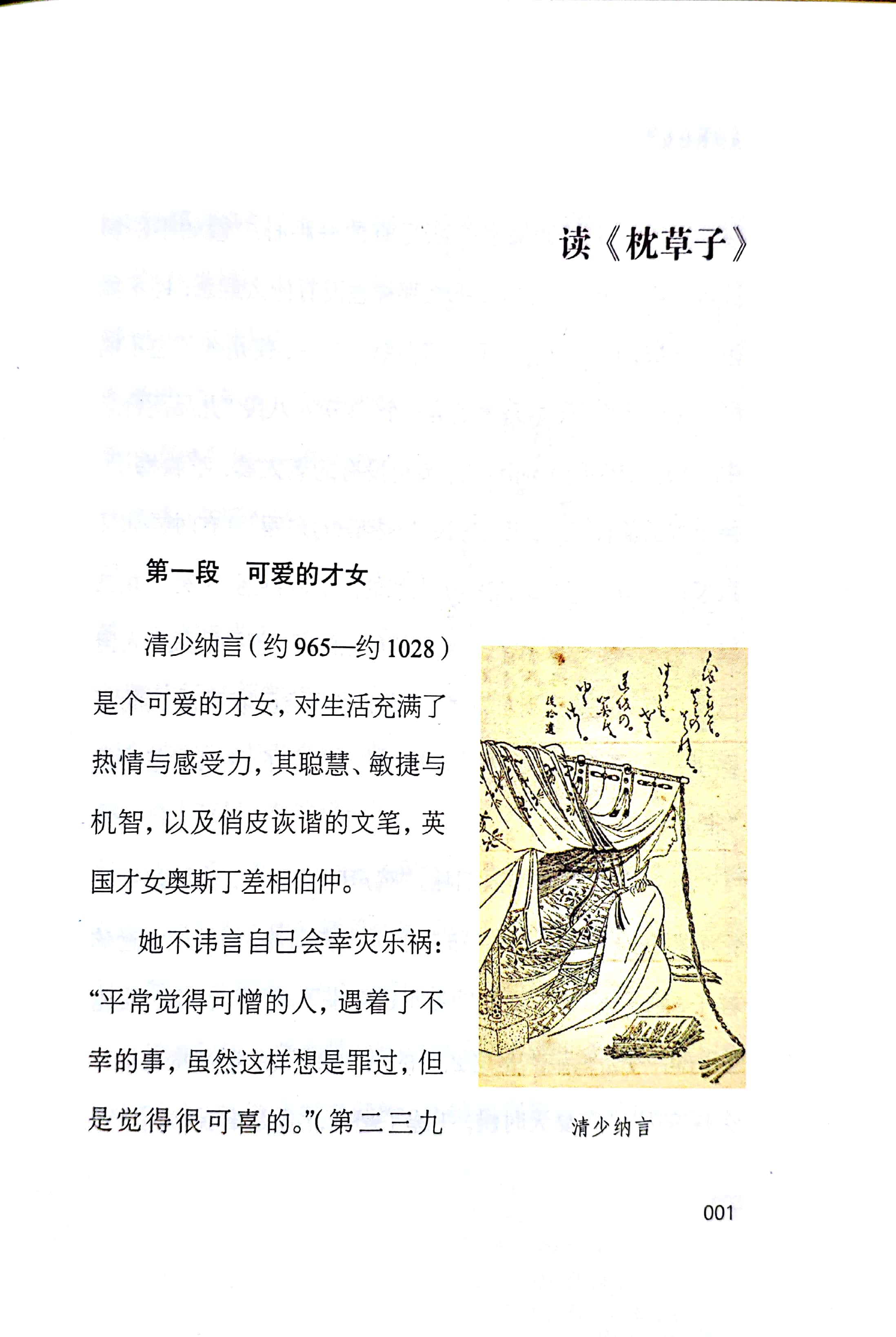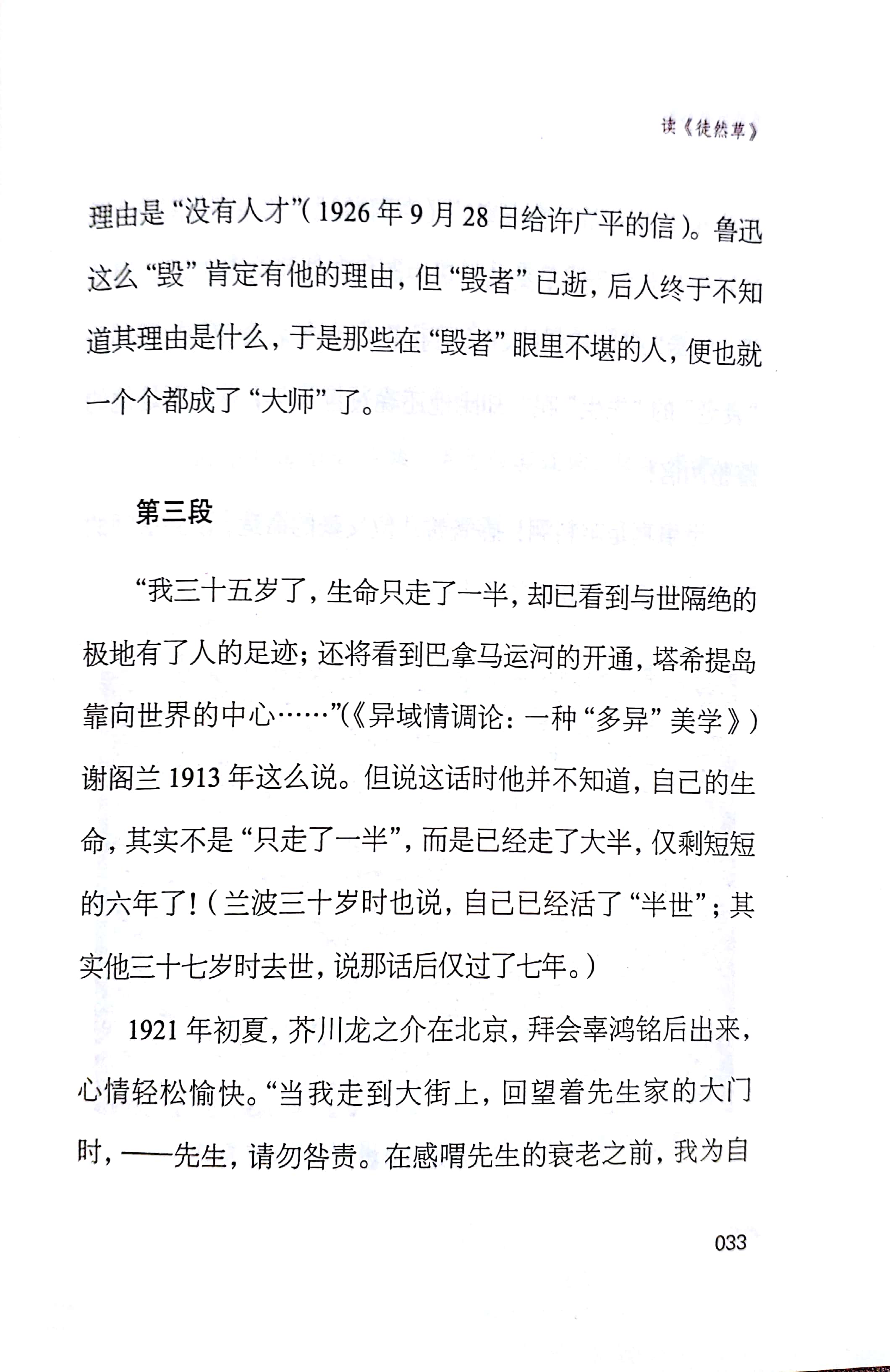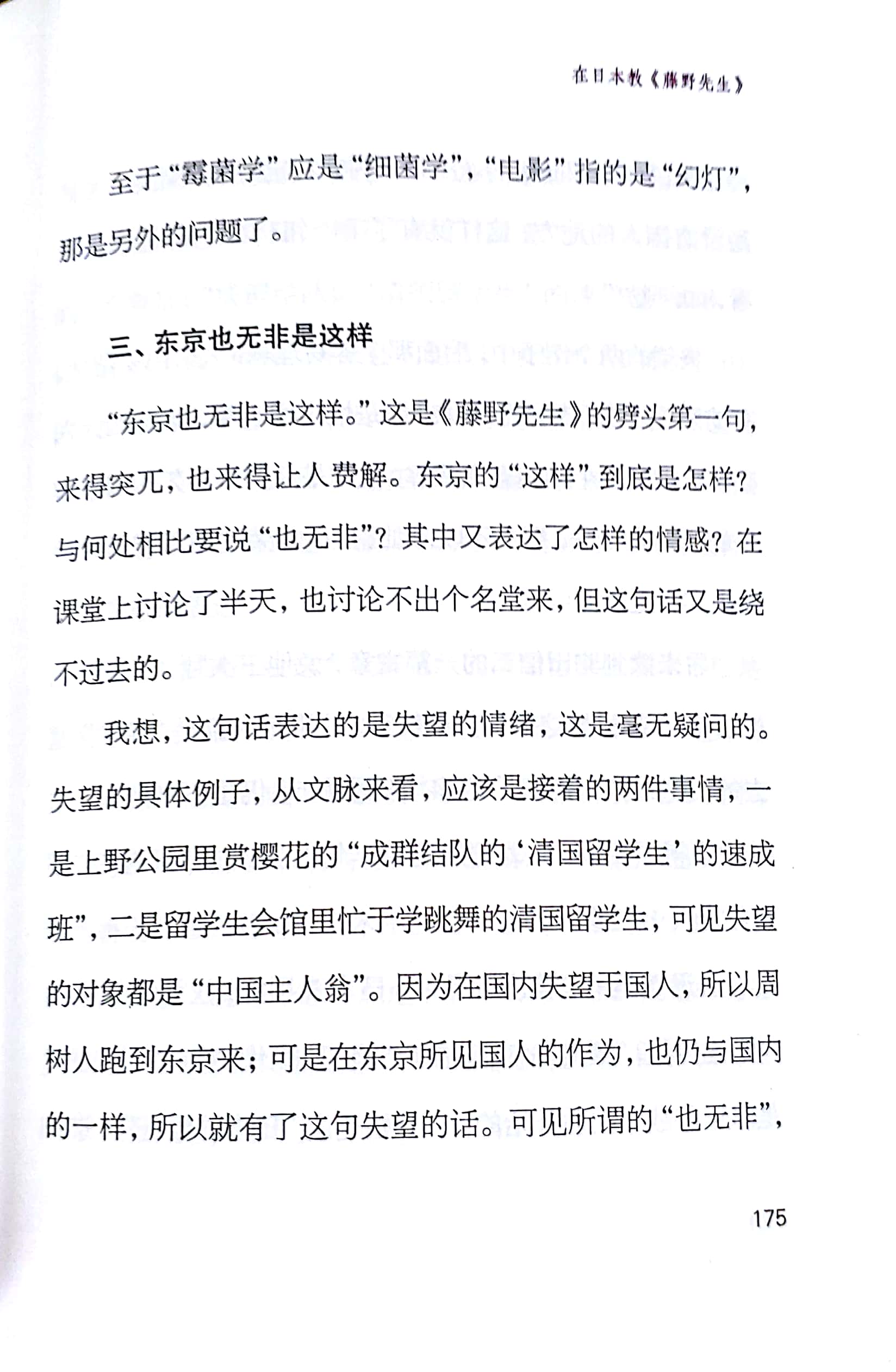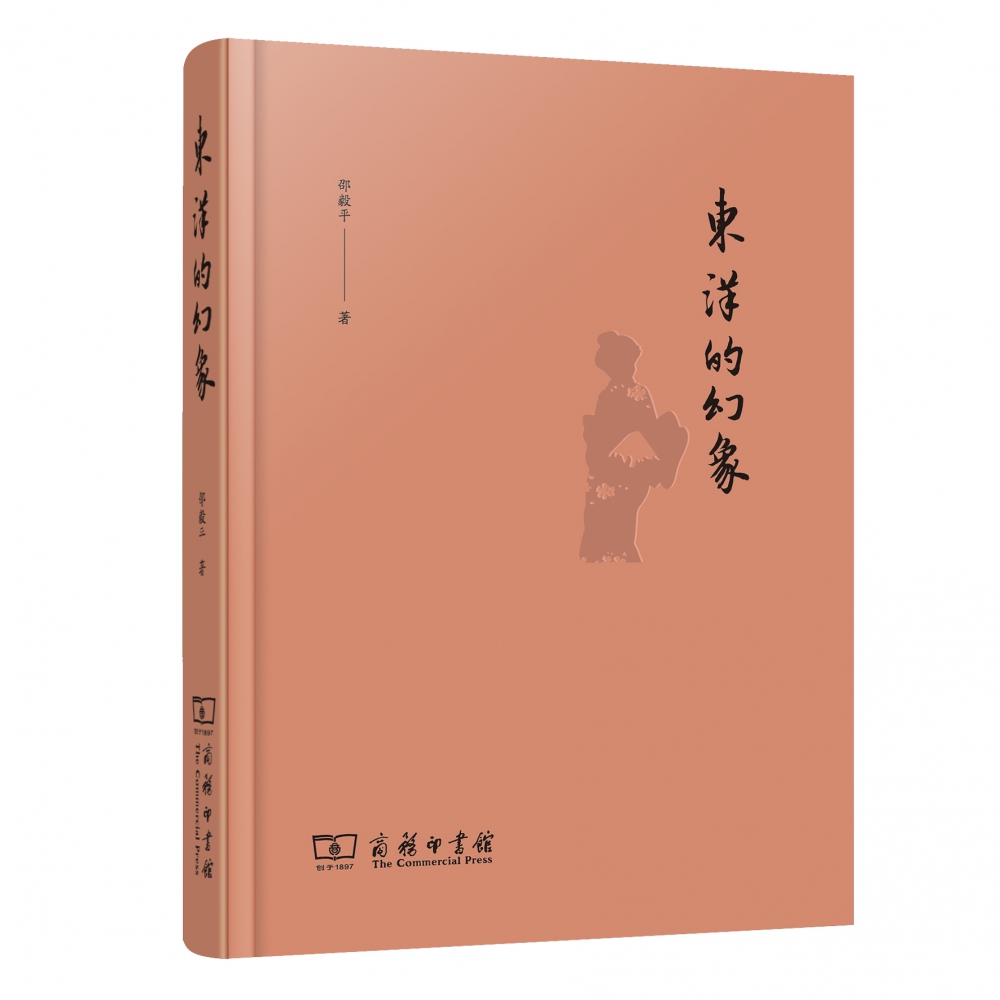
出版社: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东洋的幻象(精)
ISBN: 978710016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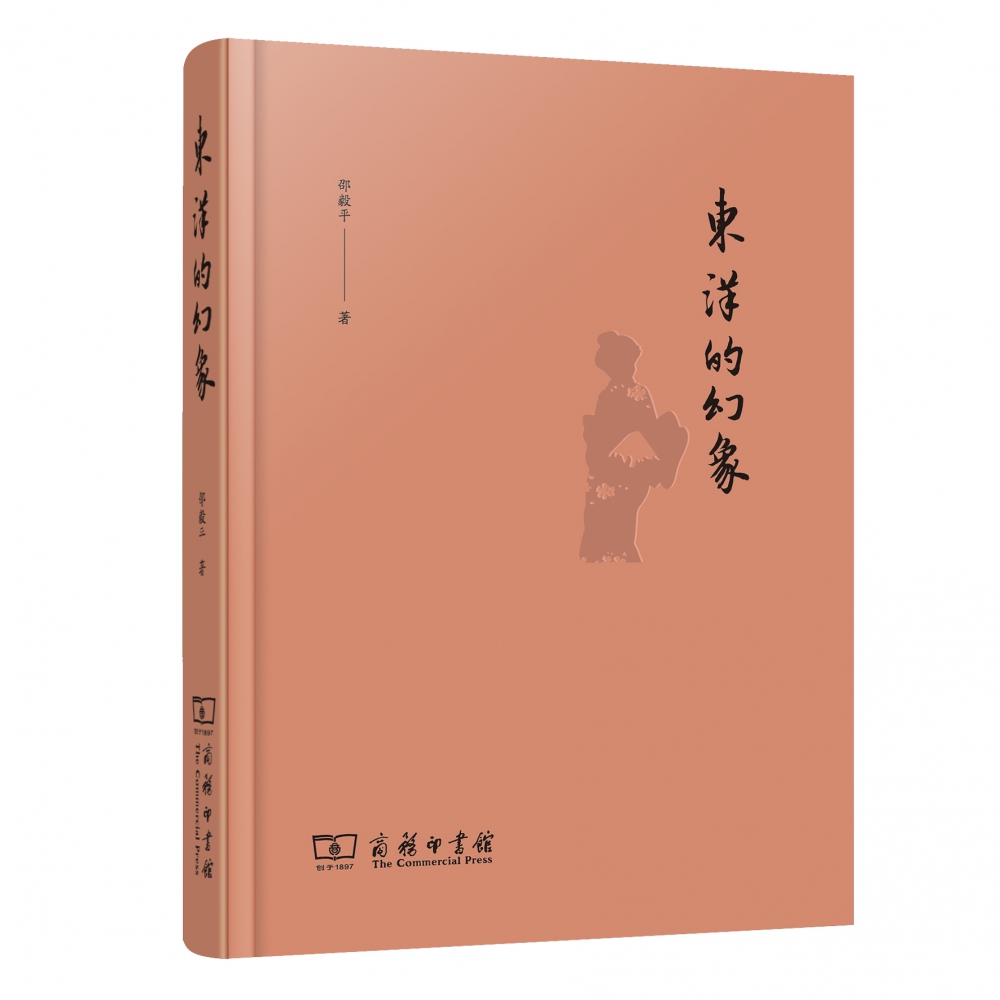
邵毅平,1957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东亚文学关系。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论衡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无穷花盛开的江山:韩国纪游》《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等。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当我们今天再来回顾谢阁兰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的那位乡前辈,同样因替法国海军服务而获得“异域”经验,写出了许多富于“异域情调”的文学作品,那就是曾在法国文坛风靡一时的洛蒂(PierreLoti,1850—1923)。 谢阁兰以“平视”的“他者”眼光看待中国,明确意识到自己所见并非真实的中国,而只是一种高度自我化的“中国的幻象”;洛蒂则以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眼光看待东方,以为自己所见就是真实的中国和日本,字里行间充满着猎奇与自恋,却基本上没有自我反省的意识。洛蒂的中国和日本题材的作品中,充溢着鲁迅所憎恶的那种心理:“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坟?灯下漫笔》)洛蒂的代表作《菊子夫人》(MadameChrysanthème,1887),虽然文笔优美,情节动人,但其中弥漫着的便正是这种心理,会让东方读者起鸡皮疙瘩的。 谢阁兰则正好相反,他决绝地宣布:“首先,清扫道路。把‘异域情调’所含的一切陈词滥调、油腻哈喇的东西统统扔掉,剥去它那身艳俗的旧衣裳:棕榈与骆驼,太阳帽,黑皮肤与黄太阳;这也就赶走了那些滥用此词的蠢家伙们……好家伙,真是场令人捂鼻的大扫除!”(第234页)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异域情调论:一种“多异”美学》中,谢阁兰为何要处处以洛蒂为对立面,将洛蒂作为“劣质异域情调论”的标本,一再加以冷嘲热讽,由此来展开自己的“异域情调论”: 什么?不就是些旅行“印象”吗?不然!这种玩意儿洛蒂已经制造得够多的了。(第226页) 其他人是假“异乡人”(洛蒂们,游客们,也都一样糟。我把这些人称作给异域情调“拉皮条”的人)。(第249页) 洛蒂之流则不然:对于他们的对象,他们充满了一种神秘主义的陶醉,没有清醒的意识,而是使自己与之缠绕;这些人互相之间也难分彼此,统统“为上帝沉醉”!(第257—258页) 而且,谢阁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劣质异域情调论”,与“殖民文学”息息相通,他在1909年1月13日写道: 扫地出门:殖民者,殖民官。 这些人根本算不上“异乡人”!前者出现是为了做当地生意,其目的再商业不过。对这种人来说,世界的“多异”只作为一种盈利手段存在。至于后者,那种中央行政的概念,以及适用于一切人、并且一切人也必须遵守的法律概念,从一开始就左右了他的判断,使他对世界的不合之音(或者说多音之和)充耳不闻。这两种人都无法声称自己对世界有审美的眼光。 因此,“殖民”文学与我们无关。(第258—259页) 写得真是痛快呵!对中国乃至东亚读者来说,洛蒂基于其“劣质异域情调论”所塑造的东方形象,仅仅反映了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令人生厌,并无什么启示意义;而相比之下,谢阁兰的“中国的幻象”,以其“异域情调论”为基础,却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仍给人以无穷的启示。 正因如此,在他们那个时代,洛蒂可谓红极一时,谢阁兰却还不为人所知;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者的地位已大大上升,前者的地位则相对下降;而到了今天,虽然在一般读者中洛蒂的知名度仍高于谢阁兰,但文学史给予谢阁兰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洛蒂。这一切,其实是在他们当初思考、动笔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时间则只不过把它显示了出来而已。媚俗者以媚俗取悦当世,却见弃于未来;特立独行者以反叛得罪当世,但将从未来得到补偿。 我知道“谢阁兰”这个名字,可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但真正开始读他的作品,却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我不敢说已经读懂了他的作品,但我知道自己着迷于他的“另类”,一如当年我倾倒于王充和鲁迅一样。试想一下,即使在“戏说”成风的现在,又有几个人敢公开赞美桀、纣呢?哪怕已过了一个世纪,谢阁兰还是那么“先锋”,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谢阁兰一再强调,他的“异域情调论”所要表现的,“是环境对旅人开口,是异域对异乡人开口。后者闯入了前者,惊扰它,唤醒它,令它不安”(第233页)。是的,我被他的“中国的幻象”惊扰和唤醒,它让我感觉到了不安;我现在对他们开口,说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不希望这些文字写出来如同石沉大海。哪怕只是一个手势,哪怕只是一个声音,只要它们能给人们带来什么,都会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第307页)那么现在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欣慰,因为他的作品所激起的回声已越来越大,甚至连我这么一个远在中国的门外汉,也加入到他的读者行列中来了。 而且,作为同样“天生喜爱云游四方,天生就是‘异乡人’”(第237页)的人,我也期盼着有朝一日造访谢阁兰的故乡,感受他当年在中国所感受过的一切,“给自己一个有别于真实自我的定义、感觉到‘多异’之存在时的陶然感觉”(第237页),并营造一个我自己的“法国的幻象”,回馈给这个营造了“中国的幻象”的智者,也继续完成我那自我救赎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