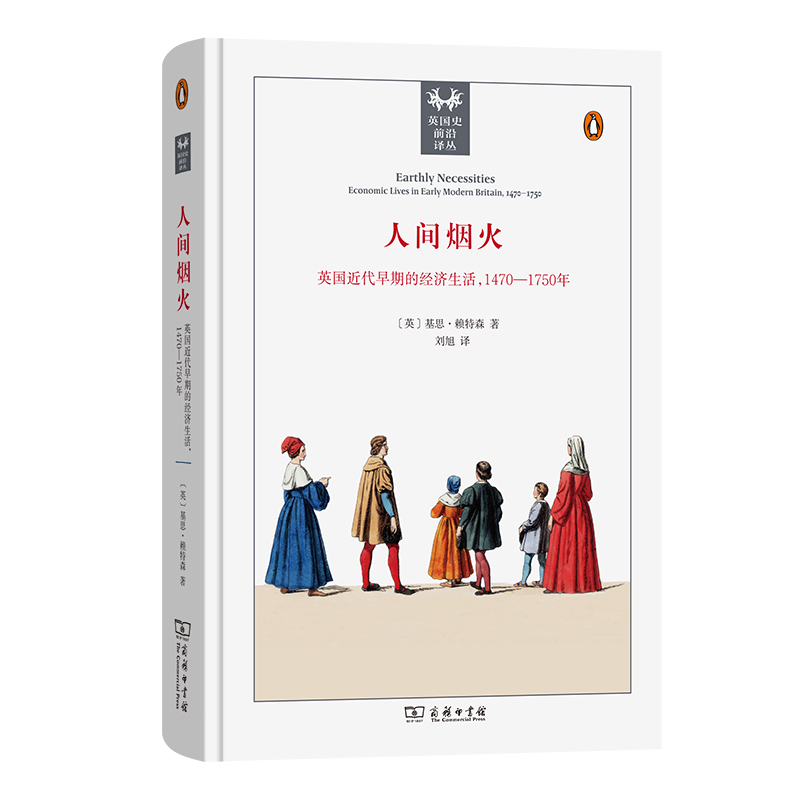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35.00
折扣价: 94.50
折扣购买: 人间烟火:英国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1470—1750年(精)/英国史前沿译丛
ISBN: 9787100228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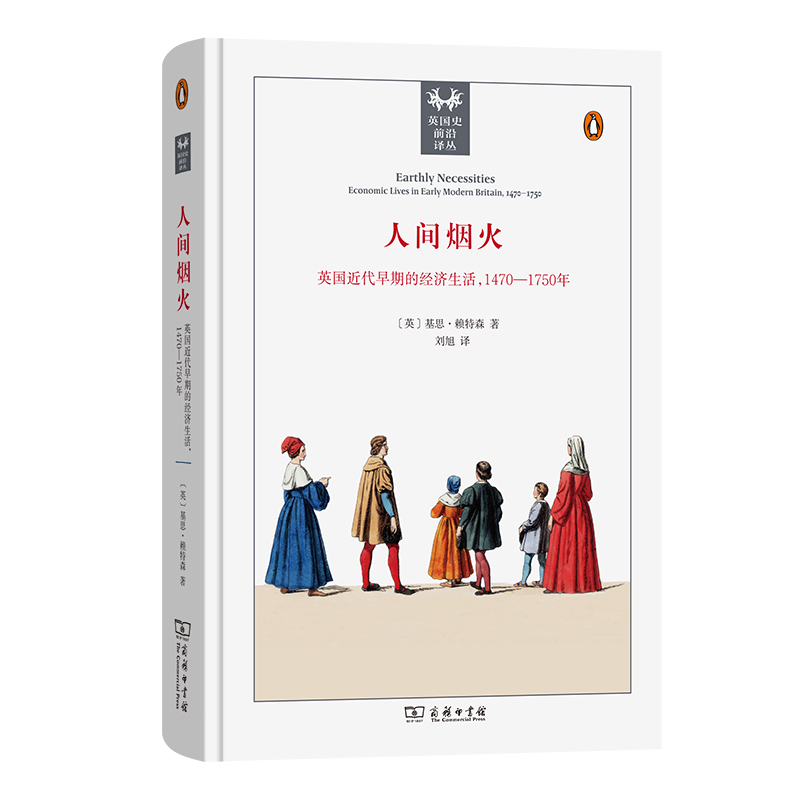
基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兰多夫·W.汤森德历史讲席教授,曾任北美英国研究协会的主席。他专攻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史研究,将在欧洲大陆已被广泛接受的“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英国社会史之中,除本书外,另著有《英国社会,1580—1680年》《拉尔夫·泰勒的夏天》等书,目前赖特森正在主编《剑桥英国社会史,1500—1750年》。 译者简介: 刘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人员。
富强之策 国内经济及与更大世界的关系变化,也暗含着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 16—17世纪,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维护人民的共同福祉,是普遍认可的政府权利与政府职责,这点在前文已有论述。基本看来,其时英格兰政府的公共政策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维护良好秩序与社会稳定,包括市场管理、经济扶持、扶贫济困、创造就业等等。其次对与国家军事力量以及安全、独立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比如农业、航运业和军火生产。最后是以对国家财富的保护和提升为导向,17世纪的英国强调贸易顺差的重要性,并因此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强化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增加或至少节约对保持货币流通至关重要的贵金属。 在此时期,英格兰政府工作的主要方向,均是围绕这几个目标开展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三大政策的相对重要性和政府工作的重心慢慢发生变化。而一旦涉及具体的经济问题,官方对于其公共政策的解读亦有所不同。 17世纪末至 18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更推动了这类变化,巩固和促进了在17世纪初已经萌发的经济文化中的革新。乔伊斯·阿普尔比曾评论称:“商业机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政府250 监管已经很难跟得上。”经济发展的实践,也逐渐与之前人们的预想发生抵触。1650年代建立的共和国自称为“共同体”(Commonwealth),但此时,用这个词汇表达更宏大的社会理想的做法已经让位于“公共善”的概念。 保罗·斯莱克也认为,“共同体”一词不再具有原来“含混不清的隐含意义”,它对于公共政策讨论中的财富问题更少表现出敌视,对于越来越具有力量的“改善”的观念更加友善,更加赞赏产量、生产率、盈利率的价值,并为世人区分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诉求提供了全新标准。 这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国内经济政策逐渐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时的英格兰政府,已经无意维护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农业秩序,有时甚至连表姿态的意思都没有。限制纺织产业发展的诸多法令已经名存实亡。公共市场常规框架外的交易活动的增长被以洋洋自得的心态加以对待。控制物价和工资水平的规章制度也逐渐被废除。而且在 1662年《住所法》(Act of Settlement)通过之后,享受教区济贫的权利基础得以确定,中央政府对于济贫法体制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少。这并非意味着都铎和斯图亚特早期的家长式作风在反威权干预的意识形态敌对浪潮中被扫除一空,而仅仅是中央政府忽略了一些从前关注的事务。乔安娜·英尼斯博士(Dr Innes)将这段时间称作英国行政管理的“无为期”。但它又和 19世纪崇尚自由市场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不完全一样,毕竟此时还有一系列法律条文和公共政策,旨在引领经济发展的方向,事实上这些政策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区别在于,当前的管理重心不同,政府不再那么执拗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希望借工商业的发展,全面提升国力。 后来,亚当·斯密将此类政策称为“重商体制”的结果,此后研究经济论著及这一时期贸易保护政策的历史学家将他的洞见发展成为一整套关于“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概念,一种成为 17世纪末18世纪初时代特征的经济体制。但事实上,“重商主义”在当时从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其源自于常见的设想,这些设想长久地影响着商业政策,并且在 17世纪早期复杂的经验中被固化。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信心不足,并且十分笃信“贸易平衡”的理论。人们相信,市场就像一个由所有竞争国家参与分食的蛋糕,其体量是固定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有限,因此整个世界的商品需求是有限的。技术革新也很难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从而让一国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聪明的做法是,要牢牢把握住现有的出口市场,开发、保护国内产业,疯狂夺取新的市场。而在进口国内紧缺的物资时,进口额一定不能超过出口额,因为贸易顺差有利于创造就业、有利于航运业发展、有利于开源节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强大。 暂且不论这些假设在 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是否符合时宜,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后来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克拉潘教授把建立在这种经济思维之上的政府立法和管理方式统称为“‘富强’之策”(policies of “Potency”),即“经济政策只具有次等经济意义”,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增强王国的实力,保证王国在经济上不依附于其他国家。这虽然听上去很有些经济民族主义的味道,但由这些目标提供依据的具体政策,却不必然包含一种建立咄咄逼人的商业体系的中央指令式计划。诚如约翰·布鲁尔所说,“这些政策构成一种松散而灵活的体系,内容还会一直调整” ——因此不断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试图拉拢政府,说只有自己的利益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总的来说,新时期的新特点慢慢催生出新的政府立法体系,在此体系内,市场发展似乎总是迎合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群。其假定了一个高强度的竞争环境,关于自由竞争的普遍优点的观念尚未形成,总体想法是通过创造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场所来追求经济优势,通过不正当手段为己谋利,争取胜利。 当时的这种经济思想带来的结果在政府的商业政策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商业是驱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各方围绕市场份额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简·德·福瑞斯(Jan de Vries)称“外贸看上去像是一个战场”。17世纪中期,长期奋战在海外的英国商人已经成功开辟出方兴未艾的殖民地市场,他们小心看护着这一块大蛋糕,当时的荷兰是国际航运的中坚力量,因此也成为英国人首要防范的目标。在 1664年某部法案的序言中,英格兰政府认为开拓种植园殖民地的目的是为英格兰带来“利益和优势”,“以使这一王国不仅成为种植园商品的贸易中心,也要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商品的贸易中心,向它们提供所需……其他国家的习惯是使它们的贸易归于自身”。 《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首先通过的是1651年法案,其时英国的殖民地贸易面临巨大危机,即将落于荷兰人之手。1651年法案在 1660年得到确认,并在后来不断修订、扩充,最终形成商业航海方面的系列法。1651年法案规定,从事亚洲、非洲、美洲商品进口的船只,必须是英国籍或殖民地籍。从事欧洲商品进口的船只,必须是英国籍或原产国国籍;英籍船只的船长和大部分船员必须为英国人;外国人同样不得参与英国国内的近海贸易及捕鱼。1660年法案则更进一步,对外籍货船运来的欧洲进口商品征收重税;并规定殖民地若要进口商品,必须由英籍船只或者殖民地籍船只负责运送;禁止殖民地商业中的一切外国因素,包括外国代理商;开列贸易清单,清单上的物品此后运往欧洲必须首先经过英国港口转运。显而易见,这些举措大多是针对荷兰的。法案起初并不容易执行,但英格兰政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为保卫其商业利益三次动用海军。1664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纽约),法案的执行状况从此大为改观。虽然《航海条例》以各单独领域的商业管制的旧有先例为基础,但它作为对未来意图的总体声明具 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给英国航运业和所有通过牢牢控制殖民地和再出口贸易利润而获益的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实际好处。 《航海条例》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在条例体系下,涉及特定商业利益集团的政府政策保持高度务实性。例如,特许商业公司一直希望压制“无证”的自由商业团体,维护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大公司的董事们不断强调行业“有效监管”的重要性,其中自然包括要求政府维持这些大商人的利润空间。不过在某些向来缺乏监管的经济领域(比如美洲殖民地的商业),经济增长更为迅猛,垄断集团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其他领域的自由商业势力借机游说政府,证明打破特许公司的垄断有利于降低物价、促进销量,进而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商业利润空间。 无论是垄断集团势力,还是自由商业势力,他们的诉求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政府则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在无关经济安全的特定商业领域,特许公司的监管职能逐渐弱化,它们的垄断也慢慢被突破,这一般是通过调整准入金额度、降低入行门槛来实现的,而不会直接取缔公司的特许经营权。通过这种方式,前往波罗的海的东地商业(Eastland trade)至 1670年代末已经实现市场开放,“商业冒险家协会”在1688年、莫斯科公司在1698年的准入金大幅下调后,垄断地位基本瓦解。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商业公司的特权被认为与国家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保护息息相关,此类公司的垄断特权不降反升。1661年,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均再次取得特许商业授权,其中黎凡特公司直至1753年一直控制着地中海地区的商船船队,垄断地位从未受到挑战。东印度公司更多地承载着世人的批评与攻击,却总能够从英格兰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特权,他们也总能够大方地以巨额贷款回馈政府。1698年经历了备受指责的十年之后,东印度公司眼看着商业对手向政府支付200万磅的政治献金,然后成立起“新”东印度公司。新老公司 分庭抗礼四年之久,后于1702年和解、 1708年合并,东印度的垄断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商业管理思路在这一时期有所转变,从前他们认为各行各业都应受到严格监管,而目前这种监管只存在于必要的领域。 乔安娜·英尼斯博士认为,自 17世纪末以来,政府决策发生了“中心转移”,这推动了前述的务实做法。专制复辟时期,在伊丽莎白时代和都铎早期均占据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枢密院逐渐退出该角色,中央政府的“多头政治”形态初现,财政部、内阁、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等一批坐拥实权的政府机关涌现。当然,权势增长最快的非议会莫属,特别是 1688年之后,议会会议每年都会召开。政府越来越少地参与总体经济战略的阐发,而仅仅作为对特定利益集团的主动行动做出反应的权力中枢存在。这些利益团体的活动并无新意,议会和枢密院都经常能够听到他们的请愿和抗诉,但是变化的体制给了它们额外的空间并且通过不断发展的新技巧,包括相互配合的院外游说、撰写小册子以及请愿,议会越来越为它们所用。由此,政府不断增添、修改原有的经济、社会法规。由当地或地方发起、得到议会私法案(private acts)支持的措施也越来越多,比如收费公路、航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些与圈地有关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商界人士希望能够自由经商,而不必受到政府法规的过分束缚,结果发现国家行政力量站在了他们一边,自然喜出望外。他们也经常借口帮助国家实现“贸易平衡”,要求政府特别是在海外贸易竞争中确保其竞争优势、对特定市场的占有以及免受其他竞争威胁。大卫·海伊教授(Professor Hey)的研究显示,谢菲尔德的刀剪行会为了维护行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一会儿要求自由贸易,一会儿又要求加强行业限制,看似无逻辑,其实全由自身利益出发。1660年,他们要求政府解禁西班牙的生铁进口,此举激怒了当地从事铁矿加工的人们。 1718年,同样在他们的推动下,政府通过相关法案,防止本国技术工人流失海外。这种形似矛盾的做法,其实颇具当年的时代特色。17世纪末,英国人钟情于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东印度公司从纺织成品的进口买卖中收益颇丰,但这却伤害到国内的毛纺和丝织行业,他们为接连丧失的市场份额焦躁不安,从 1690年代开始不断催促政府出台进口禁令。而与此同时,由于黎凡特公司长期为英国棉纺和丝织产业进口原材料,他们也更加希望看到稳定发展的国内纺织产业。出于个人倾向,抑或是特许公司锲而不舍的游说,议会议员一般分为两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他们终于在此时达成一致。 1701年,议会通过新法案,禁止穿着从亚洲进口的纺织成品,用于再出口的纺织品进口则不在其列。这一颇为实际的解决方案抚慰了丝织品院外集团并鼓励了国内棉纺织产业发展。 1721年英格兰停止从印度进口印花布之后,棉纺织行业这一初生的进口替代工业获得了更多的保护。 探寻大变局前夕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 约翰·本·斯诺奖获奖图书 。近代早期上承中世纪,下接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近代世界,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奠定了此后数世纪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与任何改革年代相似,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使社会经历了阵痛,很多因循守旧者从各种角度发出了自身对新时代的抨击。基思·赖特森曾将在欧洲大陆已被广泛接受的“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英国社会史之中,本书同样体现了赖特森的这一写作取径。阅罢本书,读者仿佛置身于英国近代早期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真切感受到这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对于各阶层群体所造成的真实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