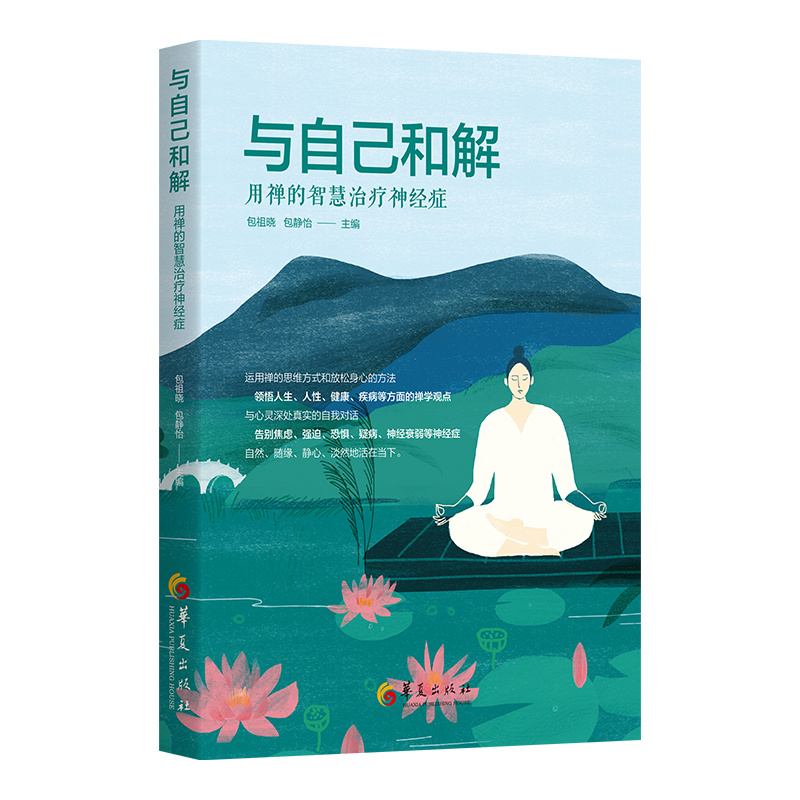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6.60
折扣购买: 与自己和解 : 用禅的智慧治疗神经症
ISBN: 9787522204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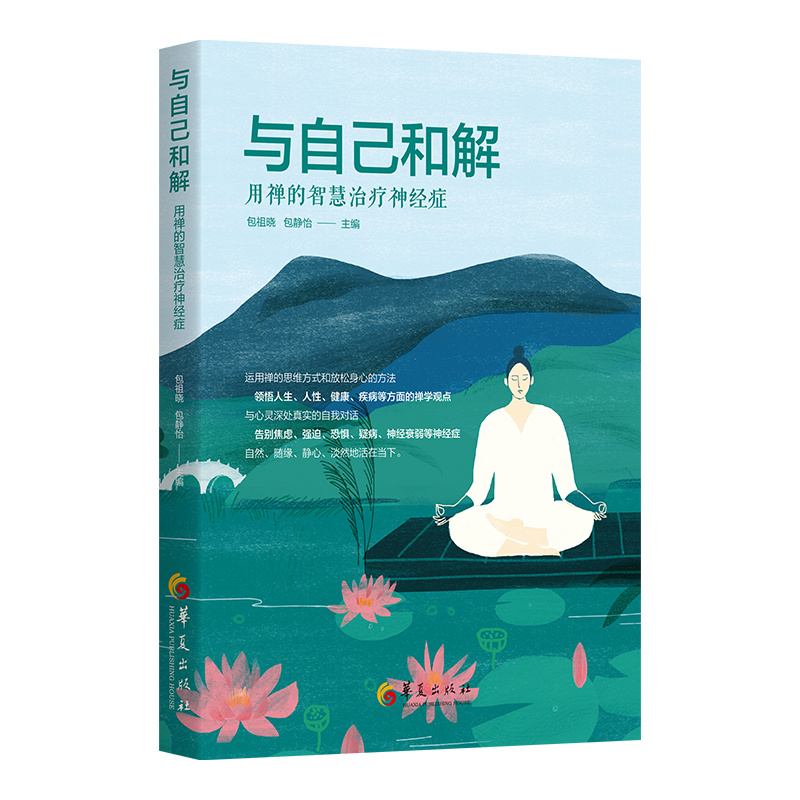
包祖晓,男,1974年8月出生,博士,现任浙江省台州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长期从事精神疾病和心身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擅长运用禅学理念和方法治疗各类心理障碍、心身疾病以及慢性躯体疾病,著有“解忧四部曲”——《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学习睡觉:心理治疗师教你摆脱失眠的折磨》《正念生活:心理医生教你摆脱焦虑的折磨》《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以及“禅疗四部曲”——《做自己的旁观者:用禅的智慧疗愈生命》《唤醒自愈力:用禅的智慧疗愈身心》《与自己和解:用禅的智慧治疗神经症》和《过禅意人生:存在主义治疗师眼中的幸福》。 微信公众号:心理科包博士,baozuxiao。包静怡: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悠游于医学、心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力创“全人”的健康理念。
人往往是自己吓自己 《百喻经》中有一则故事: 从前乾陀卫国有一班艺人,因为岁时饥馑就到别处去觅求生计。途经婆罗新山,而这山中素来多恶鬼,如吃人的罗刹鬼之类。当时这帮艺人一起在山中过夜,山中风寒,就燃火而卧。有一位艺人觉得冷,就起来披上演罗刹用的戏衣,向火而坐。伙伴中有人一觉醒来,猝然看见火边有一个罗刹鬼,竟不细察一下,爬起来就逃。于是惊动了其他伴侣,全都逃奔而去。这时,那个穿罗刹衣的人不明就里也立即跟了上去,奔驰绝走。众人见他在后面,以为要加害他们,倍增惶怖,就越山渡河,投沟赴壑,身体都伤破了,委顿跌踬,疲惫不堪。直至天明,方才知道不是鬼。 世上本没有鬼,鬼源自人们内心的恐惧。大部分神经症患者亦如此,他们多半胆小怕事,也多半怕别的东西,有人怕黑,有人怕高,有人怕水,有人怕狗……至于怕苦、怕累、怕挑战、怕失败、怕失去……虽说与“怕鬼”的跨度有些大,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是“死亡恐惧”。之所以会害怕,大部分时候是对这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够了解,是自己“妄心”所致。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我的生活充满可怕的厄运,可是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过。” 不仅鬼怪如此,人类社会的各种困难依然如此,往往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又如: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在德国一所大学里,一个18岁的青年学生吃完晚饭后,照例做导师每天布置给他的三道数学题。这个学生很有数学天赋,导师对他寄予了厚望,因此,在他完成固定作业之外,还会多给他布置几道较难的题。一般情况下,这个学生会在3个小时内把所有作业做完。 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不到3个小时,就把固定作业做完了。可是,在多布置的题中,最后一题写在一张小字条上,要求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画出正十七边形。 学生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埋头做题。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找不到解答方法。他想:也许是导师看到我每次做题都很顺利,就故意给我增加一些难度吧。越是困难,他越想把这道题攻克。他拿着圆规和直尺,一边画一边想着各种可能的思路,一直持续到天亮。最后,这道题终于被解开了。 学生拿着自己的作业,来到导师的办公室。他内疚地对导师说:“您给我布置的最后一道题,我做了整整一个通宵才解答出来。对不起,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导师接过他的作业一看,惊呆了,问道:“这是你昨天晚上做出来的?”“是啊。可是我很笨,竟然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导师让学生坐下,取出圆规和直尺,让他当面在纸上再画一个正十七边形。学生很快就画了出来。这时,导师激动地说:“你知道吗?你解开了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这道题,阿基米德没有做出,牛顿没有解出。你竟然在一个晚上就把它解答出来了!你真是个天才。我也在研究这道题目,昨天给你留题时,我一不小心把写这道题的小字条夹在了给你布置的作业里。” 很多年后,这个学生回忆那件事情时,总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那是一道两千年没有解开的题目。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把它解决。”这个学生就是数学王子高斯。 许多神经症患者由于“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作祟,处处觉得自己不行,世界充满恐惧。诗人臧克家的诗句:“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周边,等候着你一千次小心中一次的不检点。”可以视为这类患者心理冲突的一种刻画,他们时刻在为过去和未来担心:门窗关好了没有?煤气灶关好了没有?自来水龙头拧紧了没有?手洗干净了没有?被邻居家的狗碰了下小腿会否得狂犬病?……并导致反复地检查和回避,进一步增加“恐惧心理”。 如何治疗呢?下面利用泰国著名禅修大师阿姜查自我治疗的例子来说明: 夜幕低垂时,我没有其他的事了。若我试着跟自己讲道理,我知道自己一定不会去,因此抓着一位白衣就这么去了。 “该是瞧瞧你的恐惧的时候了,”我对自己说,“若我的死期已到,那就让我死吧!若我的心这么冥顽不灵,就让它死吧!”我如此暗想着。 事实上,我心里并非真的想去,但我强迫自己去。若要等到所有事情搞定才去,你将永远也去不成。因此,我义无反顾地去了。 …… 那位白衣希望能紧邻着我搭伞帐,但我拒绝了,让他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其实我心里是希望他能靠近一点,陪伴并支持我,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若它如此恐惧,那让它今晚就死了算了!”我挑战自己。虽然很害怕,但我也有勇气,反正人生难免一死。 天色逐渐变暗,我的机会来了。哈,我真幸运!村民正好带来一具尸体。我吓得连脚踩在地上的感觉都没了,恨不得立刻离开。他们希望我做一些葬礼的诵念,但我无法参与,于是就走开了。 过了几分钟,等他们离开后,我再走过去,发现他们将尸体葬在我的伞帐旁,并将抬尸体用的竹子做成床好让我睡。 现在我应该做什么呢?村子距离这里并不算近,至少有两公里远。 “好吧!若我会死,我就死。” 若你不敢去做,则永远不会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那真的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随着天色愈来愈暗,我不知在坟场可以往哪里跑。 “哦,让它死吧!人生到这世上来,总难免一死。” 太阳西沉,夜色告诉我应进入伞帐里,我完全不想行禅,只想待在伞帐里。每次我尝试走向坟场,似乎就有东西将我拉回,阻止我往前走,仿佛是我的恐惧正在与勇气拔河一样。但我还是得往前走,你必须这样训练自己。 …… 我坐在伞帐里,彻夜观察身体。我没有躺下或打瞌睡,只是静静地坐着。我是如此恐惧,即使想睡也无法入睡。是的,我害怕,不过还是尽力做。我彻夜打坐。 …… 然后,大约晚上10点左右,我背对着火打坐。我不知那是什么,但从背后的火堆传来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是棺材刚好垮下来吗?也许是野狗在咬尸体?但又不像,它听起来更像是一头水牛在缓缓地走动。 “啊!别管它……” 但它接着朝我走来,好像是一个人!他走近我的背后,步伐沉重,像头水牛,但又不是。在它向前移动时,树叶在它的脚下沙沙作响。好吧!我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我还能去哪里呢?但它并未真的走近我,只是转了一圈就往白衣的方向走去,然后一切重归寂静。我不知那是什么,但恐惧让我做了许多可能的猜想。 我想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那脚步声又开始从白衣的方向走过来。就像是人一样!这次它直冲向我,好像要将我转过去一样!我闭上眼睛,拒绝睁开。 “我要闭着眼睛死去。” 它愈来愈近,直到一动也不动地停在我的面前。我感觉他那烧焦的手似乎在我紧闭的双眼前来回挥动。啊!真的是它!所有的一切都被我抛到脑后,忘了颂持Buddho、Dhammo、Sangho(佛、法、僧),脑袋里一片空白,内心中满是恐惧,除了恐惧,没有其他。 打从我出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如此的恐惧。Buddho与Dhammo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只剩下恐惧充塞在胸膛,直到它仿佛像一张绷紧的鼓皮。 “算了,就随它去吧!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我仿佛凌空而坐,只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恐惧大到淹没了我,犹如装满水的瓶子。若你将水装满瓶子,然后想再多倒一些,水就会溢出瓶子。同样地,我的心已装满了恐惧,开始流溢出来。 “我究竟在害怕什么?”一个内在的声音问道。 “我怕死!”另一个声音回答。 “那么,‘死’这个东西在哪里呢?为何要如此惊慌?看看死亡的所在,死亡在哪里?” “哎呀!死亡就在我里面!” “若死亡在你里面,那么你还能逃去哪里呢?若逃走,你会死;若待在这里,也会死。无论到哪里,它都跟着你,因为死亡就在你里面,你根本无处可逃。无论你是否害怕,你都一样会死。面对死亡,你无处可逃。” 当我想到这点,我的观念似乎整个翻转过来。一切恐惧完全消失,简直是易如反掌,真是不可思议!那么深的恐惧,竟然能如此轻易地消失!无畏取代了恐惧。当时我的心愈升愈高,仿佛置身云端。 …… 阿姜查禅师这种治疗方式颇似现代心理治疗中的暴露疗法,确为治疗恐惧症经典而有效的方法。简单而言,就是不能逃避,怕什么就去干什么。 善于忙碌 有一个学僧到法堂请示禅师道:“禅师!我常常打坐,时时念经,早起早睡,心无杂念,自忖在您座下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用功了,为什么就是无法开悟?” 禅师拿了一个葫芦、一把粗盐,交给学僧说道:“你去将葫芦装满水,再把盐倒进去,使它立刻溶化,你就会开悟了!” 学僧依样葫芦,遵示照办,过了没多久,跑回来说道:“葫芦口太小,我把盐块装进去,它不化;伸进筷子,又搅不动,我还是无法开悟。” 禅师拿起葫芦倒掉了一些水,只摇几下,盐块就溶化了。禅师慈祥地说道:“一天到晚用功,不留一些平常心,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摇不动,搅不得,如何化盐,又如何开悟?” 学僧:“难道不用功可以开悟吗?” 禅师:“修行如弹琴,弦太紧会断,弦太松弹不出声音。保持平常心,不忘给自己留一点空隙,才能悟道。” 学僧终于有所领悟。 许多神经症患者就跟文中的学僧一样,当医生告诉他要“做点什么”时。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会跟医生说:我平时很忙的。的确,他们常用打麻将、旅游散心、逛街购物等多样化的娱乐使自己忙碌。但奇怪的是,白天忙的时候头脑里基本上“不会胡思乱想”,一到空闲下来和晚上,头脑里杂七杂八的念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这其实是一种瞎忙,这种忙碌用患者的话来说叫“转移注意力”,属心理学上的“中和思维”,对轻度的焦虑和强迫或许有暂时效果,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多样化的娱乐就像是麻醉剂,麻醉时间一过,空虚感又会来袭。换句话说,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对“念头”的压制、逃避或者以另一种刺激代替原来的刺激,是无效的。正如: 克契禅师个性随和,遇事尽可能不去麻烦别人,就连修行也是一个人默默地进行。一天,佛光禅师问他说:“你来我这儿也有12个年头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要不要坐下来聊聊啊?” 克契连忙回答:“禅师您已经很忙了,学僧怎好随便打扰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又是三个秋冬。 这天,佛光禅师在路上碰到克契,又有意点化他,主动问道:“克契啊!你在参禅修道上可曾遇到些什么问题?” 克契答道:“禅师您那么忙,学僧不好耽误您的时间!” 一年后,克契经过佛光禅师的禅房外,禅师再次对克契说道:“克契,你过来,今天我有空,不妨进禅室来谈谈禅道。” 克契赶忙合掌,不好意思地说:“禅师很忙,我怎能随便浪费您的时间呢?”佛光禅师知道克契过分谦虚,再怎样参禅,也是无法开悟的。于是等到佛光禅师再次遇到克契时,便对他说:“学道坐禅,要不断参究,你为何老是不来问我呢?” 克契仍然应道:“老禅师,您忙,学僧实在是不敢打扰!” 这时,佛光禅师大声喝道:“忙!忙!我究竟是为谁在忙呢?除了别人,我也可以为你忙呀!”佛光禅师这一句“我也可以为你忙”的话,顿时惊醒了克契:忙不过是逃避的借口,不知道自己哪里不明白,不在不明白处仔细探究是阻碍禅修精进的石头。 神经症患者就像克契一样,越逃避就越治不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忙碌的同时“给自己留一点空隙”,让自己有机会“观照”或“拥抱”头脑中的念头;另一方面要善于忙碌。 有人说,生活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躺着过日子,一类是站着干工作。躺着过日子的人,自感身体舒服,可宝贵的生命却在舒服之中失去了光泽,做人的精神却在舒服之中消磨了锐气。站着干工作的人,付出代价,而生命却在付出中换来了辉煌,精神却在付出中换来了不朽。就我们临床所见,这类躺着过日子的人容易患神经症。 曾经有人做了一个调查:“中了500万大奖,你会做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辞职”。有趣的是,如果追问他们辞职后想做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又会统统回到做自己喜欢的事上。从这个角度看,善于忙碌是做自己甘心忙碌的工作。有哲人提出:“工作如果是快乐的,那么人生就是乐园;工作如果是强制的,那么人生就是地狱。”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就是善于忙碌。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说:“一流的家庭主妇比二流的教授更接近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的人当然也就更少患神经症了。用我国神经症研究专家许又新教授的话说:“当您什么时候找到一件做起来比怀疑身体有病更有意义的事时,您的病就好了。”简单地说,专注地做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就是“善于忙碌”。 第84个烦恼 尽管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神经症禅学治疗的专著,但并不是教你追求特殊的开悟境界,不企图达成有别于当下的意识状态,不参公案或话头,更不主张透过专注禅定引发三昧之境。而是帮助修习者维持着感官的开放度,留意身心在每个当下的反应与变化,逐渐增强对身体的觉知力,愈来愈细微地去发现意识底层的焦虑感和紧缩倾向,学习如何对瞬息万变的思维活动进行标示,领悟人生、人性、健康、疾病等方面的禅学观点,以勘破那些在早期养成过程中所种下的错误信念和方法,突破这些根深蒂固的制约系统,学会“正念”地、“智慧”地活在“此时此地”之中。